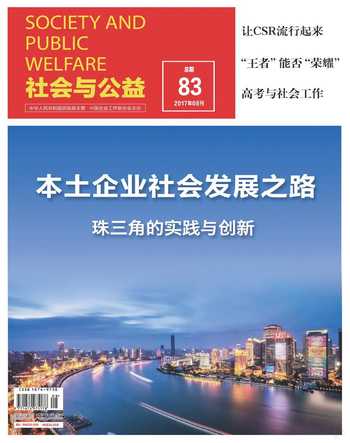“畫餅”何以“充饑” 高考志愿填報與社會工作專業
每到一年高考時,填報志愿問題就成為廣大考生,特別是家長們尤為關心的問題。其實,這其中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特別是一些新的專業表現地尤為明顯。一方面學生和家長在選擇專業時存在“過度實用主義”考量。即只以專業“有用無用”論好壞,這就導致一個結果,一些新的、富有活力的專業就成為“無用”或是“不好”專業的序列,因為不好找工作,沒有與之對應的職業、崗位。典型地如本文所說的社會工作專業。
事實上這里面存在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一是,有用無用,家長判定的標準就只是是不是很好找工作,收入是不是很高等。也就是說凡是那些畢業后很容易找到工作的,收入不菲的專業就成為填報志愿中的“熱門”專業,比如說經濟學、金融以及會計等。二是,認識上的不到位和“刻板印象”。一般來說,人們的“認識”是法學專業的學生畢業之后就是要到公檢法部門工作的,師范院校的畢業生以后是要去做老師的,而社會工作專業畢業之后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居委會的“阿姨、大媽”所從事的工作呢?如此以來,社會工作在選報志愿時不受待見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面,高校專業長期以來處于“學術象牙塔”進而與人們產生的“神圣距離感”。這一“距離”就造成了人們認識上的不足和理解上的“誤識”。一是高校專業宣傳與介紹上的“過于術語化”,即語言表達上的不接地氣;二是人才培養上的“社會性斷裂”。社會工作人才的靜態化培養與現實實踐的動態性變化不匹配,專業能力的養成與實務領域中的操作要求不疊合,導致僅有的用人單位對人才培養的不滿意以及政府對社會工作專業作為治理創新手段期望的邊際效應遞減。
由此,社會工作作為一個新興的專業在選報志愿的過程中就面臨著“多重尷尬”。第一,尷尬的第一志愿上線率。也就是說大一新生第一志愿選擇社會工作專業的比率極低,多數是由其他專業調劑過來的,通常都是被“陰差陽錯、糊里糊涂“地調劑到了社工專業。極低的第一志愿上線率就極大地影響了專業在學校發展中的地位,造成了邊緣,面臨被取消的命運。
第二,尷尬的專業介紹與宣傳。被調劑過來的學生就面臨著專業認同的建構問題,而專業定位以及職業化空間的不清晰、不通暢就造成了專業導入以及介紹中的空泛和乏力。因此,“畫餅”就成為通用的說辭。比如,“社會工作的春天說”、社會工作是一個很有前景的專業,同時將專業發展的不景氣都歸并到地區的不發達以及沿海大發展的“二元想象”中。再比如,林鄭月娥高票當選香港新任特首,我們的專業宣傳中就會說,她是港大社會學系畢業,曾讀社工一年;就連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也有社區工作者的從業經歷,似乎社會工作專業與做官(政治)具有了一定的關聯性。權且不論這種“關聯性。的顯著度如何?不可否認的則是,社會工作專業的知名度因為他們而有了明顯的提高,我們要反思這種提高中會不會將上述“關聯性”絕對化或是必然化,進而造成人們的新的“誤識”,這是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特別是當前的社會建設以及社會工作發展熱潮中,就更需要我們進行“冷”思考。第三,尷尬的就業空間和機會。一提到社會工作專業的就業去向,通常的“官方”表述就會是“本專業培養具有基本的社會工作理論和知識,較熟練的社會調查研究技能和社會工作能力,能在民政、勞動、杜會保障和衛生部門,及工會、青年、婦女等社會組織及其他社會福利、服務和公益團體等機構從事社會保障、社會政策研究、社會行政管理、社區發展與管理、社會服務、評估與操作等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在社會工作專業職業化程度不高的情境中,社會工作專業就被污名化為“萬金油”的專業,似乎做什么都可以,也似乎什么也都做不好。這樣沒有直接“對口”就業領域的專業就遭遇了尷尬,在高校中進一步被邊緣化。
上述的尷尬,造就了社會工作作為專業在高校的岌岌可危(中山大學撤銷社會工作本科招生,某種程度上就是例證),在社會中的污名以及在報考學生志愿填報中的消弭。因此,如何建構一個合理的關于“專業的想象”就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一“想象”要實現對社會工作專業尷尬的消解、不同主體認同與認識上的同一,以及對社會工作理論知識與實務操作的聯通,并且在這一“想象”要有助于建構積極的關于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社會的想象”,進而再此基礎上導向一種積極的職業觀和專業觀,增進改變。
侯利文,男,博士,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上海高校智庫“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美國休斯頓大學社會工作研究生院訪問學者(2015-2016)。主要研究領域為社區治理和社會工作學,先后主持和參與國家級、省部級以及橫向科研項目、委托課題20余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