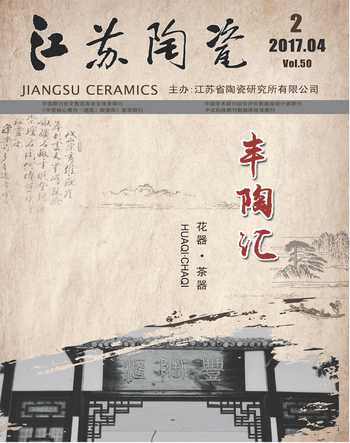壺生竹還是竹生壺
周躍鋒
紫砂壺藝是一門全手工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是通過藝人的雙手憑空塑造的一門技藝。它承載了深沉的歷史和文化,表露出每一個(gè)參與制作藝人的文化素養(yǎng),它是一種心靈之間彼此交流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紫砂壺的造型,尤其是紫砂花貨的造型,更加趨于隨心隨性,不受約束的自然塑造,需要?jiǎng)?chuàng)作者極盡巧思,將抽象或是具象的美感包容在一件小小的紫砂壺之中。
有人說,紫砂光貨是傳統(tǒng)壺藝的一面旗幟,而花貨則因?yàn)橥ǔ1憩F(xiàn)出趣味性而是對(duì)當(dāng)下的一種反饋。這種觀點(diǎn)正確與否見仁見智,但這種觀點(diǎn)背后反映出來的,卻是我們很多人對(duì)紫砂花貨塑造的一種潛在的認(rèn)識(shí)。物奇生趣,體現(xiàn)出韻味悠長、內(nèi)涵真切,是每一位制作紫砂花貨的陶藝人所追求的,但所謂的“趣”,不同的人卻又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古時(shí)文人有高雅之趣、追古之趣、問道之趣……而當(dāng)下更多的人則常常會(huì)追尋自然之趣、生活之趣。“趣”之所以不同,關(guān)鍵在于不同時(shí)代我們的需求各不相同。所以紫砂花貨塑造的關(guān)鍵也正在于此:創(chuàng)作者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趣”是否是別人需要的?是否會(huì)被欣賞?掌握住需求,自然也就明確了創(chuàng)作的方向;有了方向,目標(biāo)亦變得明確,創(chuàng)作起來自然得心應(yīng)手。筆者在制作眼前這件“竹趣壺”(見圖1)的時(shí)候,進(jìn)行了一點(diǎn)思考。
若拋去裝飾不談,“竹趣壺”的造型與傳統(tǒng)的紫砂壺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壺身氣韻飽滿、壺蓋覆于壺口,與壺身自然連續(xù),不突兀、不做作,弧線的走勢順暢,上下一體,遵循了紫砂造器一貫協(xié)調(diào)的美感。“竹趣壺”加上裝飾則將骨秀神清的竹融于壺中,運(yùn)用堆、貼、塑、雕等手法,將生動(dòng)的自然天趣和高貴的君子氣節(jié)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壺身為球形,飽滿圓潤,視覺上穩(wěn)重大方,壺嘴、壺鈕、壺把,均設(shè)計(jì)成竹節(jié)狀,遒勁有力,有剛正不阿的象征意義。一簇竹葉自壺流胥出,伸至壺身,幾片竹葉迎風(fēng)招展,瀟灑飄逸。造型至此,已盡顯竹趣,與其他以竹為題的作品不同的是,在這件作品上除了竹子以外,還多了一只精心設(shè)計(jì)翩翩起舞的蝴蝶,其靚麗的色彩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現(xiàn)實(shí)的場景,一個(gè)誤入竹林的小小生靈,色彩生動(dòng)、活靈活現(xiàn),與竹因風(fēng)而動(dòng),給整體虛靜的氛圍平添了一份生命活力。在定格住這一美麗瞬間的同時(shí),更抒發(fā)了一份心境,使得原本單調(diào)的竹味瞬間充滿了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多姿多彩,憑空生出許多趣味。
以竹為題材的紫砂類作品有很多,但經(jīng)過歷代藝人的創(chuàng)作,無論是從內(nèi)涵還是從造型上來說,單純從竹子本身去尋找的趣味幾乎被挖掘殆盡;簡單來說就是能想到的造型,大多已經(jīng)盡出于前人之手。因此傳承紫砂壺藝的過程,也就避免不了重復(fù)和類同。雖然這種現(xiàn)象無法避免,但從趣味的角度出發(fā),結(jié)合實(shí)際,營造出與以往不一樣感覺的作品,似乎能夠從一定程度上避免這種同質(zhì)同態(tài)的壺藝創(chuàng)作。
當(dāng)然并不是說原本題材之上,添加一處微小的變化或者裝飾就可以稱為新的創(chuàng)作,其前提仍然是要結(jié)合紫砂的實(shí)際情況,要擁有完整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邏輯。如“竹趣壺”中的蝴蝶,其顏色、形態(tài)構(gòu)成以及在茶壺上所處的位置都是需要精心梳理的,絕非胡亂搭配就能出彩。這種梳理一方面要考慮到茶壺本身的結(jié)構(gòu)、裝飾間的相互影響,還應(yīng)考慮到其裝飾邏輯與現(xiàn)實(shí)邏輯是否沖突,如我們踏春之時(shí)確能夠在竹林之中看見翻飛的蝴蝶,而絕不可能遇見一只仙鶴,這就是現(xiàn)實(shí)邏輯與裝飾邏輯的界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再回到文章標(biāo)題,即到底是茶壺生出了竹,還是竹子生出了茶壺?通過思考得出結(jié)論,實(shí)際中紫砂壺創(chuàng)作中通過不同的創(chuàng)作邏輯,這兩種情況可以分別產(chǎn)生,固然可以以茶壺形態(tài)為基礎(chǔ)配合竹子形態(tài)的裝飾;同樣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以竹子的形態(tài)做為基礎(chǔ),巧妙地體現(xiàn)出茶壺的功能。這其中并沒有矛盾的地方,其中的關(guān)鍵便在于要使創(chuàng)作邏輯和現(xiàn)實(shí)邏輯不悖。只要將邏輯理順,那么制作也就沒有困難了。長期以來,紫砂壺藝便是依靠著這一點(diǎn)不斷繼往開來,歷久彌新。其包容的藝術(shù)特點(diǎn)使得每一條創(chuàng)作之路都有著屬于自己的光明未來,關(guān)鍵在于創(chuàng)作者的努力與堅(jiān)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