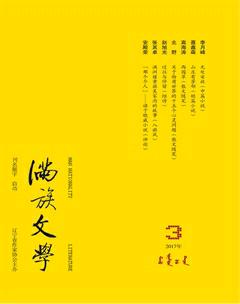“那個個人”
安殿榮
讀于曉威的小說,不禁讓人想到電影《阿甘正傳》里面那句經(jīng)典臺詞:“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遠(yuǎn)都不知道下一顆是什么滋味。”是的,于曉威的小說常在歷史與當(dāng)下,鄉(xiāng)村與城市,北方與南方間閃回,更是頻繁地在不同類型人物的內(nèi)心之間切換,難以用相對突出的主題和敘事風(fēng)格來概括他小說富于變化的特點,但是通過對于曉威小說的整體閱讀,還是找到了這種多變風(fēng)格背后恒定的內(nèi)核——于曉威關(guān)注的是身處不同時代與不同生活環(huán)境下的“那個個人”,擅以極端處境凸顯個體命運,以及個體在選擇過程中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yán)的追尋。
極端處境與自由選擇
談于曉威的小說,不能繞過丹麥作家克爾凱郭爾。于曉威寫過一篇克爾凱郭爾的同名小說《勾引家日記》,并在多篇作品中提到克爾凱郭爾,向他致敬。索倫·克爾凱郭爾(1813-1855)是現(xiàn)代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他醉心于探求現(xiàn)實中的人生問題,“那個個人”即是克爾凱郭爾的墓志銘。“是的,一足以成為無限,個人就是無限的起點。”克爾凱郭爾說。他還說,“作家正是那最典型的個人。”① 從于曉威創(chuàng)作的人本主義色彩上看,他深受克爾凱郭爾及其后形成的存在主義文學(xué)的影響。
存在主義作家們“常常在創(chuàng)作中把人物放置于某種極端化的處境之中,讓主人公面臨具有荒誕性的兩難化局面,最終突出他們的決斷和選擇。他們強調(diào)的是人類只有面對極端處境和危機(jī)關(guān)頭,生命的潛在的能量和可能性才會得到充分的挖掘,人的意志和尊嚴(yán)才能充分顯現(xiàn),人類所面臨的真正的生存現(xiàn)狀也才能得到深刻反思。因此,存在主義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身處逆境,遭遇荒誕的形象,他們所置身的往往是一些極端化的生存處境。” ②于曉威的小說即通常將主人公置于一種極端的處境之下,并致力于這種極端處境下,人物的心理變化和行為選擇,其中有偶然,有無奈,有轉(zhuǎn)折的大悲大喜,也有無法扭轉(zhuǎn)的一往無前。
于曉威的這系列小說可以歸為“處境小說”。《瀝青》是其中的代表作。《瀝青》中的張決蒙冤入獄,在辯白無望的情況下,他不惜一切代價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并使用一切手段(三次越獄)獲得自由之身。有意思的是,張決前兩次越獄成功后,又主動回到了監(jiān)獄,能逃而不逃,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但當(dāng)?shù)弥显V無門之后,張決實施了第三次越獄計劃,并徹底走上了逃亡之路。這就是張決在極端處境下的選擇,通過他的選擇,也讓讀者看到了這個時代的司法制度,看到了利益集團(tuán)之間以犧牲他者為代價的丑惡交易。當(dāng)張決在不能見光的逃避生活中看到自己沉冤得洗的消息時,竟是不敢相信的,他的個人命運從此陷落在逃亡之中,這是莫大的諷刺。《L形轉(zhuǎn)彎》講述了主人公杜堅人生道路的幾個轉(zhuǎn)折,他從一個居家好男人,轉(zhuǎn)為出軌的男人,再從出軌的男人轉(zhuǎn)成趁機(jī)謀殺的男人,當(dāng)杜堅受命去解救情人的丈夫時,在萬眾矚目的緊急時刻,他選擇了借歹徒之手,變相謀殺情人的丈夫。人物的命運就是在這樣一個接一個的轉(zhuǎn)折與選擇中被改寫了。《天氣很好》則著重于描寫有過案底、一心改過的何錦州被再次脅迫犯罪時的內(nèi)心波動與最終選擇,與之相對應(yīng)的是警察老劉在緊急情況下只身臥底,被識破并被陷害的故事。在清白與罪惡之間,選擇即意味著擔(dān)當(dāng)。在《房間》中,劉齊回家取資料時敲不開家門,以為是與妻子徐麗矛盾升級所致,情急之下,請好友陶小促幫助化解家庭矛盾,陶小促攀爬到劉齊家陽臺時,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劉齊的妻子徐麗是因為家中藏了一個男人而久久不肯開門,這種未曾意料的局面,使剛剛攀爬到陽臺外部的陶小促陷入了一種難言的尷尬,劉齊是陶小促昔日的好友,徐麗又是陶小促妻子的老板,兩難之中,他選擇了體力不支而墜樓。作者利用了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感性的方法來解消人物內(nèi)心的苦悶與荒謬。在這些極端處境下的選擇,無一不體現(xiàn)著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yán)的追尋。
關(guān)于歷史的另一種解讀
于曉威還有多篇歷史題材(戰(zhàn)爭題材)小說,也側(cè)重于個體命運在極端處境下的選擇,以及偶然性給人帶來的人生變故,藉此對歷史進(jìn)行重新觀照與審視。如《一曲兩闕》《抗聯(lián)壯士考》《一個好漢》《陶瓊小姐的1944年夏》等。
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曲兩闕》。小說開篇便由看守烈士陵園的老人提出 了一個悖論:“你是個好人,可你的敵人肯定要說你壞;當(dāng)你的敵人說你是好人時,你想你還是好人嗎?”老人年輕參加戰(zhàn)斗時,為了讓受傷的戰(zhàn)友免于落入敵手,在戰(zhàn)友的請求下,結(jié)束了他的生命;而面對同樣受傷的敵人(國民黨兵),面對同樣的請求,為了讓敵人備受傷痛折磨而死,老人拒絕了他。誰知,國民黨兵不但沒死,還活得好好的,還找到他,一心地要報答他。這深深地折磨著老兵。特殊情景下的不同選擇,使老兵的人生不經(jīng)意間就被擺渡到自己不愿踏上的另一條河岸。
另一篇典型的代表是《陶瓊小姐的1944年夏》。歷史題材作品多有生活原型可尋,而這篇一開端就告訴讀者,這完全是由裱糊在書上的一小截舊報紙引發(fā)的靈感。作者在尾聲中也再次聲明:“以上情節(jié)的發(fā)生,差不多都是在我的想象中完成的。”“粘貼在楊衒之《洛陽伽藍(lán)記》第四篇文末的殘斷的舊報紙,只有一小截,上面只記載了這么幾句話:“本報訊……彈藥庫遭全創(chuàng)……事后據(jù)某旁觀人士回憶,事發(fā)前曾有一年輕之陌生女子入內(nèi),該女子胸峰高挺,風(fēng)姿綽約,然輕裝薄服,無持寸鐵……此事蹊蹺,云云。”作者根據(jù)有限的這幾句話展開了想象,塑造了一個美好的、為愛而堅定的陶瓊小姐的形象。盡管是虛構(gòu)的歷史故事,而陶瓊小姐患乳癌的遭遇和為愛人挺身而出的抉擇,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實。
《一個好漢》則提供了另外一個看待歷史的角度。這像是一個揭秘故事,使人對這個好漢的定義進(jìn)行重新考量。并不堅定的地下通信員、典當(dāng)行老板胡成軒,在準(zhǔn)備自首前夕,因為誤讀了一張字條,真的成了一個好漢。“盡一切可能伺機(jī)越獄。我們已沒法營救你。”胡成軒在慌忙間把“沒法”看成了“設(shè)法”,于是,在希望面前,在好漢與漢奸之間,他選擇了前者。在越獄等待救援的過程中,他犧牲了,成為史冊中記載的一個好漢。《抗聯(lián)壯士考》寫了李老槍、楚雙子、趙四眼三個抗聯(lián)英雄的小傳。他們在戰(zhàn)斗中的選擇以及后來的命運,透視了偶然因素與命運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尤其是《楚雙子》這篇,記錄了特殊年代特殊情景下的一次非人道性的抉擇。楚雙子是一對雙胞胎的名字,大的叫楚大雙,小的叫楚二雙。兩人為了躲高利貸,一南一北分開逃跑,二雙加入了抗聯(lián),大雙卻加入了偽軍。為了拿到一份叛變者的供詞,二雙偷襲并擊斃了大雙。不同信仰追求下,手足間的自相殘殺讓人唏噓。
難以勘測的情感世界
于曉威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寫難以勘測的情感世界。比如《勾引家日記》《L形轉(zhuǎn)彎》《眩暈》《在淮海路怎樣橫穿街道》《讓你猜猜我是誰》《北宮山紀(jì)舊》《隱秘的角度》等等。這些作品一個比較鮮明的特點是對愛情的懷疑和猜忌,對婚姻的各種試探,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個人情感世界的震動,并于一個轉(zhuǎn)彎處(極端處境或是情感的困境)戛然而止,留給讀者的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回味空間。
可能發(fā)生的轉(zhuǎn)折都有哪些呢?比如在《勾引家日記》中,主人公以陌生的身份試探和勾引自己的妻子。這是在無聊生活中一次臨時起意的游戲,然而荒唐的游戲背后,隱藏的是在這個通信發(fā)達(dá)的時代愛情之脆弱,以及對愛情和婚姻的不信任,眼見著妻子對神秘人從一塊堅冰到心動如水,主人公滿是懊惱。然而作者結(jié)尾的轉(zhuǎn)折——妻子沒有赴神秘人之約,選擇像往常的周末一樣,和丈夫一起出去吃飯,這雖是結(jié)尾,卻僅僅是故事的一個逗號,留給讀者對他們今后婚姻生活的遐想是無限的。主人公在自己的日記中援引了克爾凱郭爾的一段話:“你必須做點什么!既然你有限的能力無法使事物變得更容易,你必須以相同的人道主義熱忱,努力著使事物弄得困難一些……我把在每一處地方制造困難看作自己的任務(wù)。”于曉威確實像克爾凱郭爾所言的那樣,他在努力制造困難,設(shè)置極端的處境以窺探和暴露人性弱點,而那些無端生出的困難,使生活像斜逸出來的枝條,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路徑,有了別樣的豐富。《眩暈》設(shè)置的困境是個體的孤獨,即便是相愛的人,也很難設(shè)身處地去了解愛人的真實心理處境;《讓你猜猜我是誰》闡述的是一種關(guān)于愛情與婚姻的悖論。這個故事雖然與《眩暈》完全相異,但兩篇小說留給人思考的內(nèi)核卻是非常接近的,橫亙其中的困境同樣是永遠(yuǎn)無法真正抵達(dá)他者——即便是最親密的人,所以,如題記所引:“結(jié)婚,你將為之后悔。不結(jié)婚,你也將為之后悔。無論你結(jié)婚還是不結(jié)婚,你都將為之后悔。”《在淮海路怎樣橫穿街道》寫的則是關(guān)于情感的出軌與回歸,寫破壞秩序的沖動,以及秩序破壞后,是否重歸秩序與理性的思考。《隱秘的角度》雖不能簡單歸為情感故事,因為故事的主角之間并沒有發(fā)生實質(zhì)性的交集,而僅僅是憑借窗口的觀望建立了某種想象。但美好事物帶給人的反應(yīng)卻是不一樣的,有人欣賞,有人受到了折磨,而這正印證了每個人所經(jīng)歷過的復(fù)雜的情感世界。
有態(tài)度的寫作
有態(tài)度的寫作是讓人敬佩的。閱讀于曉威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位很有擔(dān)當(dāng)?shù)淖骷遥宰约邯毺氐囊暯怯涗浐兔枘∩睿宰约旱乃伎紒泶蛄亢蛯徱暽睿鎸ι钪谐霈F(xiàn)的諸多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于曉威在他的作品中,一邊拆解一邊重組,看似犀利,實則讓人窺到了他內(nèi)心的那塊柔軟之地。
于曉威的作品比較注重對生命狀態(tài)的呈現(xiàn),對國民性格的思考。比如《九月玉米地》《喪事》《關(guān)于狗的抒情方式》《今晚好戲》《在深圳大街上行走》等等,包括《圓形精靈》和《游戲的季節(jié)》。《九月玉米地》呈現(xiàn)的就是普通農(nóng)戶人家遭遇病痛和高額醫(yī)療費用時的生存狀態(tài)。因為無錢醫(yī)治,小病而拖成了大病,大病則帶走了人的生命。村姑和林子身上有著他們那代人的樸素和堅韌,他們沒有去想生活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只是默默地接受這一切變故。作品表面上寫的是村姑一個人的命運,實則關(guān)切的是所有浸泡在苦難中的人和他們的命運。于曉威在結(jié)尾寫道:“只有眼前的玉米地還在活潑潑地生長著”,可見作者對現(xiàn)實生活那種既無奈又無力改變的傷感情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篇作品還讓人看到了普通人在病痛下的堅韌和尊嚴(yán),林子與村姑之間那種相濡以沫的愛情,也是那么地真實、質(zhì)樸、感人。《喪事》更是一種直接的白描式的呈現(xiàn),縱是一個片段,卻更接近鄉(xiāng)村生活的本質(zhì)。揭示國民性格的作品如《關(guān)于狗的抒情方式》和《今晚好戲》等等。前者寫小機(jī)關(guān)里的大乾坤,諷刺意味十足;后者則是對“圍觀”心態(tài)的一種呈現(xiàn),不禁讓人想到魯迅先生筆下圍觀的中國人。《圓形精靈》和《游戲的季節(jié)》這兩篇小說,將生活中有意味的片段用一條主線串聯(lián)了起來,讓我們在回望不同時代的生活時,不免發(fā)出一聲悠長的嘆息。
作為一位有態(tài)度有擔(dān)當(dāng)?shù)淖骷遥跁酝淖髌犯嗟伢w現(xiàn)在對心靈的撫慰、滋養(yǎng)和引領(lǐng)上。這一類作品多集中于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作家認(rèn)知生活的全新視角,讓人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多種可能。這類作品通常有很強的戲劇性,帶給人的震撼和沖擊也是非常強烈的。在《孩子,快跑》中,主人公端午涯本沒有考上重點高中,但因為平日里都是跑步上學(xué),體育百米跑了全校第一,按特殊人才被重點高中招錄了。端午涯的故事頗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意味,意外獲得的收獲,也讓我們思索應(yīng)該如何對待困頓的并不如意的生活。作家為讀者呈現(xiàn)的生活既是殘酷的又是溫情的。《厚墻》當(dāng)屬這類作品中的代表作。小說開頭的詩意與結(jié)尾的殘酷形成了鮮明對比。是什么讓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比厚墻還要難砸?是什么讓有著善良本性的男子在生活中變得如此慳吝?又是什么樣的境地,會令一個少年因為五十塊錢對雇主舉起大錘?作品開頭展現(xiàn)的是人們心懷美好的本來面貌,這相當(dāng)于故事的“前傳”,是重新看待生活的視角,也使砸倒“厚墻”的聲音變得如此強烈。還有《午夜落》,也是一個非常小的生活橫截面,作家沒有細(xì)述主人公遭遇事件的因果,只寫了他對老板的不滿,以及在這個小小咖啡廳里,只點了一杯咖啡的可憐女人。他甚至產(chǎn)生了幫那女人買單的想法,及至咖啡廳打烊時,才知道那女人原是這里的老板。這對主人公帶有莫大的諷刺意味,但同時也讓我們體味到作家的用心,不同的觀察角度會帶來不同的判斷結(jié)果。對人生的認(rèn)知和判斷也是如此。在《沿途》中,主人公從絕望到重燃希望,也是因為獲得了重新認(rèn)識生活的視角而豁然開朗。一次赴死之旅,讓主人公改變了想法,向死而生。這些作品都可以看到作家的擔(dān)當(dāng)意識,這些重新打量生活的角度是別致的,也是可貴的。
節(jié)制又豐沛的敘事
縱覽于曉威小說,在敘事上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就是既節(jié)制又豐沛。
節(jié)制主要體現(xiàn)在對語言的“慳吝”上。于曉威短篇小說居多,語言以簡潔干脆見長,基本上都是直接切入“那個個人”,不做與主體故事不相關(guān)的無意義的纏斗。除了有效的敘事,節(jié)制也是為了留白,使作品在有限篇幅內(nèi)蔓延出無限的回味空間。這點還比較突出地體現(xiàn)在作者疏離的敘事態(tài)度上。雖然有很多作品使用的是全知視角,但作者還是“慳吝”地只講述十分有限有效的部分,比如《眩暈》的開篇:“杜默和陳紅是居住在深圳羅湖區(qū)的一對青年夫妻。一年半前的一個傍晚,正在散步的某公司職員杜默在火車即將進(jìn)站時,發(fā)現(xiàn)了橫臥在鐵軌上的陳紅。”這個開頭,可以說絲毫無彈性可言,就是簡單的介紹和鋪墊。但這樣的開頭也恰恰說明了作家的自信,對接下來要講述的故事的自信,也是對自己敘事能力的極度自信。在這個故事中,再也沒有交代杜默究竟是在什么公司工作(那于作品而言是毫無意義的),也沒有交代陳紅為什么臥軌,而這個缺失的交代,恰恰是為陳紅之后的病態(tài)表現(xiàn)打下伏筆,也為陳紅與杜默離婚后的生活擔(dān)憂,為每個個體的孤獨哀傷。
豐沛主要體現(xiàn)在對“那個個人”豐盈的心理關(guān)照,體現(xiàn)在通過故事闡述的意義豐富的哲學(xué)思辨,以及有意味的結(jié)尾上。于曉威的小說對主人公的內(nèi)心給予了高度的關(guān)照和尤為細(xì)膩的描摹。也可以說,于曉威小說重于刻畫的就是人物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勾引家日記》中對男主人公內(nèi)心活動的刻畫,甚至采用了與日記相結(jié)合的方式進(jìn)行講述。哲學(xué)思辨幾乎貫穿在于曉威的所有作品之中,對生活、對個體命運、對愛情、對時間等等的思考,在作品中都多有體現(xiàn),有的則直接將哲學(xué)大師的話援引進(jìn)來,《勾引家日記》中寫道:“社會心理學(xué)認(rèn)為,人的最初求偶本能并不是源于占有的情感,而是源于嫉妒的情感”;《在淮海路怎樣橫穿街道》中說:“正像羅蘭·巴特說的,愛上了愛情而不是那個人。雖然據(jù)我考證,同樣的話更早是一個半世紀(jì)以前的克爾凱郭爾說的。”;在《沿途》中,“他想起蒙田說過的一句話:世上可怕的往往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們對事物的看法……”后又引用了卡夫卡說過的一句話:“虛幻往往更是一種真實,而常人眼中的現(xiàn)實往往是不真實的……”;《讓你猜猜我是誰》引用了瑞士心理學(xué)家榮格的話:“惱怒是意味著你還沒有看到在它后面是什么東西”等等,可見作家有著非常豐厚的哲學(xué)素養(yǎng)。《北宮山紀(jì)舊》本身便是一個禪意十足的故事。而像《厚墻》《沿途》《午夜落》這些作品都彌漫著強烈的哲學(xué)思辨,作家提供的是打量生活的多維視角。我們看世界的角度不同,所站的立場不同,自然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衍生出不同的想法。這些哲學(xué)思辨,便使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無限豐沛起來。
于曉威短篇小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采用補記或人物檔案的形式結(jié)尾,結(jié)尾與前面的故事或是有意味的補充,或是形成巨大的反差,帶給人思想上的震動。比如《房間》的結(jié)尾就是采用了補遺的形式,使故事結(jié)局走向完滿的同時,依舊留下懸而未決的東西,使作品更加豐富起來。在《抗聯(lián)壯士考》這系列短篇小說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這系列作品都以簡短的人物歷史資料結(jié)束,與前面的故事形成反差,也提出嚴(yán)正的思考。比如在《楚雙子》中,雙胞胎因為跟隨的隊伍不同,使得手足兄弟相殘。在楚二雙的歷史資料中這樣記載,楚二雙在去一所大學(xué)做報告時,被問道:“您當(dāng)時對親手足的舉動是否違背人性”的問題時,“年近八十的楚二雙望著滿臉幼稚卻又自詡學(xué)識淵博的大學(xué)生們,愣怔半晌,啞口無言,疑為耳朵幻聽。最終憤而離去,不復(fù)與外界有觸。”這樣的補記是讓人非常震動的,作品沒有給出答案,故事的主人公也沒有給出答案。也許每個讀者也都不會給出堅定的答案。這也就是作品的豐沛所在。
于曉威的小說較多關(guān)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時代背景下的“那個個人”,寫極端處境下那些個人豐富的心理路徑和行為選擇,這使他的作品品類豐富,形式多樣,涉及的領(lǐng)域也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回避的一點是,為了突出表現(xiàn)人的處境以及表達(dá)作家對生活的思考,作品的一些情節(jié)還是難免能夠看出精心設(shè)計的痕跡。總之,于曉威是位非常有擔(dān)當(dāng)?shù)淖骷遥麑ι硖幧詈榱鞯摹澳莻€個人”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注,也在對個體的關(guān)注中,讓我們看到了與之相關(guān)的比較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提出了犀利的問題,也提供了別樣的柔軟的視角和可以探索的方向。期待他在保持豐富的創(chuàng)作的同時,有更多的開拓。
注釋:
①《“那個個人”——中譯本序》,《勾引家日記》,【丹麥】克爾凱郭爾著,江辛夷譯,作家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P2。
② 《20世紀(jì)外國文學(xué)專題》,吳曉東主編,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11月第2版,P47。
〔責(zé)任編輯 宋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