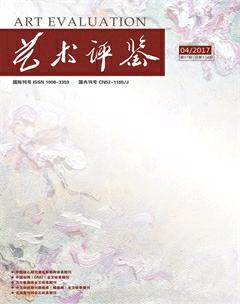讓·魯什“真實電影”美學(xué)風(fēng)格初探
鮑曼華
摘要: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大師讓·魯什是20世紀(jì)法國四大人類學(xué)國家級博士之一,1917年出生于一個法國中產(chǎn)階級家庭。二戰(zhàn)時期,他來到尼日爾架橋修路,并以記錄的形式來做人類學(xué)研究。1958年,他拍攝了電影《我,一個黑人》,之后紀(jì)錄片變成了讓·魯什一生表達自己對于大自然和人類學(xué)訴求的主要方式,而他作為紀(jì)錄片導(dǎo)演的新身份也漸漸的被人們所認(rèn)同。縱觀整個紀(jì)錄片發(fā)展史,法國的讓·魯什導(dǎo)演以“真實電影”電影風(fēng)格與同時期美國柯利克“直接電影”一同形成紀(jì)錄片中的兩大主要的紀(jì)錄電影的形勢與風(fēng)格,也對當(dāng)時的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本文將要探尋讓·魯什紀(jì)錄片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并分析這樣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形成背后的原理與原因。
關(guān)鍵詞:讓·魯什 真實電影 分享型人類學(xué) 美學(xué)風(fēng)格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7-0139-04
一、影像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分享”與“反饋”的靈感源頭
讓·魯什認(rèn)為:“作為一名人類學(xué)家,觀察和田間調(diào)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他早期的電影中,他拍攝紀(jì)錄片的目的在于搜集人種志的資料,獲得當(dāng)?shù)厝说男湃危玫疆?dāng)時、當(dāng)?shù)亍?dāng)事之人的本土文化認(rèn)同。他毅然扛起他的小型攝影機,奔走于尼日爾河畔的各個角落,開始了他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的生涯。”①
1954年,魯什回到索柯漁村放映他的電影《獵河馬》給漁民們看,這種“分享”與“反饋”的研究方式也使得他在人類學(xué)的研究上提出了:共同參與人類學(xué)原理,使得社會人類學(xué)的研究在本土文化認(rèn)同上不再依靠一種“顯象”和“觀察結(jié)論”去揣測當(dāng)?shù)氐谋就廖幕欢峭ㄟ^“分享”“反饋”直接獲得一種本土的文化認(rèn)同。②可見,魯什當(dāng)時對于人種的要求并非只停留在了觀察和調(diào)查的層面上,他似乎對于還原“被遮蔽”的“真實”,發(fā)掘“生活中的‘真實”有著更濃厚的興趣。他將生活中的“真實”置于“真實生活”之上的層面。在讓·魯什紀(jì)錄片中,戲劇化結(jié)構(gòu)和敘事策略(如《美洲豹》《瘋狂的靈媒》等片)使得這些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與一般意義上的“人種志”電影有所不同。
1960年,魯什在法國拍攝了《夏日紀(jì)事》這部電影,它成為了魯什“真實電影”的經(jīng)典之作,也是魯什電影生涯的重大轉(zhuǎn)折,至此之后,他將記錄的重心從“人種志”電影中研究人類的自然屬性轉(zhuǎn)移到了去關(guān)心人們內(nèi)心的想法與情感,魯什從這種轉(zhuǎn)變中試圖去發(fā)掘一種被“遮蔽”的真實,將“真實”做的徹底。
作為一名紀(jì)錄片導(dǎo)演,魯什的電影中運用了“在場性思維”的方式來拍攝,并以“介入”與“搬演”為表達,使得屏幕內(nèi)外共同在場參與互動,讓觀眾對于“真實”(v'erit'e)又有了全新理解。
讓·魯什在他的有生之年為了非洲電影做了一些貢獻,在他80歲的時候,他又重新回到了非洲這片熱土上支持非洲文化的發(fā)展,他在當(dāng)?shù)亻_辦“電影學(xué)校”“文化遺產(chǎn)保護中心”,2004年2月18日,讓·魯什在尼日爾的一次車禍中意外死亡,享年86歲。然而,讓·魯什這個來自法國的“尼日爾守護神”,將以另一種方式繼續(xù)守護著這條東流入海的河流,并傳達給人們一個信息——這是沒有結(jié)局的,電影的歷史沒有結(jié)局。③
讓·魯什的“分享人類學(xué)”逐漸成為一種流行的紀(jì)錄片流派,“分享”與“反饋”正在改變著人們觀影的方式。
二、“介入”“干預(yù)”“角色搬演”——讓·魯什電影的紀(jì)錄策略
“真實電影”是一種反對虛構(gòu)的電影。在對于界定“非虛構(gòu)電影”的概念在(non-fiction film,港臺翻譯為“非劇情片”)后格里爾遜時代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紀(jì)錄電影定義,并且被人們普遍接受。當(dāng)代影視創(chuàng)作中,無論是在故事片中采取“紀(jì)錄”手段,還是在紀(jì)錄片中運用“虛構(gòu)”修辭,都表明當(dāng)代電影中自我反省意識和作者的策略在不斷增強。④
早在1922年,弗拉哈迪的《北方納努克》中,搬演手段成就了當(dāng)時紀(jì)錄電影一種“還原真實”的虛構(gòu)手段,而在魯什后期的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中,這一手法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繼承,并且在此基礎(chǔ)上開創(chuàng)了“真實電影”的先河。
我們能夠看到的“真實電影”的最早作品,是魯什在1958年拍攝的《我,一個黑人》。這部影片拍攝了一些到象牙海岸打工的尼日爾黑人青年的生活,這些人都是他找來的業(yè)余演員——他們一方面需要在象牙海岸打工掙錢以解決生計,一方面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拍攝電影,其中一個青年還因為觸犯了當(dāng)?shù)胤杀魂P(guān)押了三個月。魯什并沒有安排這些黑人青年具體做什么,而只是跟拍,因此這部電影也被稱為“即興電影”。而巴爾諾曾評價這部電影為“使人感覺不到導(dǎo)演的存在而又非常有感染力”,是一種“不可阻擋再現(xiàn)真實的印象”。⑤
在形式上,這部電影體現(xiàn)了攝影機或者說攝制主體的“在場”。這種“在場”的方式,不論在當(dāng)時的劇情片還是紀(jì)錄片中都讓人耳目一新。
在魯什的紀(jì)錄電影中,表達問題盡可能接近于所認(rèn)知的真實,對聲音與畫面進行忠實紀(jì)錄的這種手段在他早期的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中得到充分運用。基于此,同他的客體/采訪對象進行交流分享,但這種共同參與分享式的拍攝手法形成了與“觀察法電影”對立的一種美學(xué)風(fēng)格——即“在場的美學(xué)。⑥
此后,魯什紀(jì)錄電影的風(fēng)格開始轉(zhuǎn)向“虛構(gòu)”,從敘事上來說,講一個故事是為了防止觀眾完全沉浸其中,而這種游走于“真實”與“虛構(gòu)”之間的電影美學(xué)風(fēng)格,在20世紀(jì)60年代的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中掀起了“真實電影”之風(fēng),挑戰(zhàn)了人們傳統(tǒng)的觀看電影模式,拉近了屏幕與觀眾之間的心理距離。“真實電影”除了分享參與的觀影模式打破了傳統(tǒng)觀念以外,魯什在電影中開始有意識的搬演,對人物進行有意識的刻畫。他的演員中多半是非職業(yè)演員,同時時時刻刻和魯什生活在一起(例如達雷姆,拉姆等),導(dǎo)演對于“演員”的性格愛好、生活作息是十分熟悉的,因此魯什也在前期的設(shè)定中將演員的生活與故事一同囊括在他的電影里,而“戲”里的達雷姆同時也是“戲”外的達雷姆,演員們在魯什的電影中不僅僅是搬演一個角色,更是搬演了他們自己真實有趣的生活。在真實生活中的情感事件,起承轉(zhuǎn)合非常自然,演員們明白了他們的“角色”之后,更是在鏡頭前有意識地搬演,有意識地介入和發(fā)表自己真實的看法,這種介入通常同樣是自然且不加以設(shè)定的,演員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演戲,還是真情吐露(例如《夏日紀(jì)事》中瑪瑟琳在協(xié)和廣場上喃喃自語,事后瑪瑟琳說自己是在演戲,而魯什卻堅持當(dāng)時她是在真情吐露)。
“我認(rèn)為可以通過刺激某種偶然性、激發(fā)某種遭遇,來創(chuàng)造戲劇性,我們需要拍攝經(jīng)過干涉之后的生活,而不是記錄本來的生活。”⑦魯什在2002年接受北京師范大學(xué)張同道教授的采訪時說到,在他眼中的“生活中的‘真實”是高于“真實生活”的。
他用“激發(fā)”一詞,說明他認(rèn)為生活中的火花是需要主觀的去介入和干預(yù)的。將戲劇點轉(zhuǎn)移到導(dǎo)演所想表達的主題上中,以介入和干預(yù)的方法,使得一些被遮蔽的真實得到還原。筆者認(rèn)為這就是他的電影中的“真實”所高于“生活真實”之處。
其一,這種“介入”“干預(yù)”“在場”頗有誠意的向觀眾展示了影片攝制的方方面面,將電影中所遮蔽的關(guān)于影片攝制這部分的畫面光明正大的展現(xiàn)給大家。
其二,這種“在場式”的電影手法收了起所有凌駕于電影本身,觀影者之上的“上帝視角”,以一種平等的視角將觀眾和電影本身帶到了同一觀影視角,像是導(dǎo)演坐在了觀眾席中一起觀影,一起期待劇情。
其三,“真實電影”的“在場性”美學(xué)風(fēng)格使觀者陷入一層又一層的電影世界之中,仿佛是在看一場“電影中的電影”,而這也正如柏拉圖所說“生活的真諦要透過層層的藝術(shù)才能見到”。
三、“電影魯什”的“攝像機”視閾
與巴贊的紀(jì)實主義美學(xué)風(fēng)格所推崇的長鏡頭理論不同,從魯什的鏡頭中往往可以看到不同于巴贊所提出的“影像與現(xiàn)實”的“實際同一性”。
在魯什的鏡頭中,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實對于影像的反饋,而這些影像中又埋藏著種種“虛構(gòu)”的修辭。
魯什的影像在“真實”與“虛構(gòu)”中游弋;在他電影中的“在場”是根植一種對于觀者而言的“在場”。這使得當(dāng)我們作為觀者觀看他的電影時,常常可以看見他既在“真實”中,又在“真實”之外。⑧
當(dāng)魯什在非洲拍攝當(dāng)?shù)赝林苑窒矸答伒姆绞剑缭綌z影機的觀察,求得當(dāng)?shù)厝藢τ谏钭顪?zhǔn)確的理解。在這樣的拍攝過程中,拍攝者本人不再是一個冷眼旁觀的觀察者,魯什坦言:“我以一種間隙瞄準(zhǔn)的方式拍攝我的電影,我這樣看著我的電影。看看鏡頭里面和鏡頭外面的事物有什么不同,發(fā)生什么不同的事件。那個時候我借用維爾托夫的話‘電影眼睛,這樣的術(shù)語,我覺得我不再是讓·魯什,而是‘電影魯什”。
在魯什的這番解說中我們能夠想象出這種分享反饋的“參與式”拍攝手法使得被拍攝者同時在“真實的自己”與“電影中的自己”兩者間時而疏離,時而貼近。作為觀眾的我們,也仿佛是置身于現(xiàn)實的時空中和“電影魯什”一起經(jīng)歷拍攝,在魯什的電影中的主人公通過影像,與鏡頭外的觀眾進行交流。
“電影魯什”的“機械眼睛”是指魯什自己參與的真實電影中,所使用的攝像機視閾。這種“攝像機視閾”的說法通常是一種擬人的手法。而真正的“電影里的神甫”還是魯什自己,他以全知的視角,又同時參與了自己的電影,這使得他的電影鏡頭時而冷靜的旁觀,時而又深度的參與。
四、《夏日紀(jì)事》——“電影魯什”的影像社會調(diào)查
1954年,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民舉行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武裝起義。1958年,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宣布成立,這象征著武裝斗爭獲得了初步勝利。
《夏日紀(jì)事》拍攝于1960年,法國人類學(xué)家讓·魯什和埃德加·莫蘭記錄了這期間的一個夏日,巴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他們對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的所思所想。
影片始終圍繞著人們的生活與情感,不予否認(rèn),它是一部“真實電影”,也是一部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甚至是一次影像實踐的社會調(diào)查。
在這場關(guān)于人們情感與生活的影像實踐的社會調(diào)查中,最先進入我們視野的是瑪瑟琳,而且兩位導(dǎo)演讓·魯什、埃德加·莫蘭與被采訪者瑪瑟琳同時出現(xiàn)在一個空間里。
他們向瑪瑟琳表達了他們實驗的意圖:“我和魯什想拍攝的是一部關(guān)于反映生活狀態(tài)的主題的影片:你怎樣生活?其實意思就是在生活里你如何應(yīng)對自如?”⑨問題從瑪瑟琳開始,再問其他人。瑪瑟琳不僅是第一出現(xiàn)和主要的被拍攝者,同時還是一個參與者,她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yè)的人提出了同一個問題:“你幸福嗎?”對陌生人而言,這種提問顯然是有些唐突的,有些讓人猝不及防。作為“女主角”之一的瑪瑟琳,在影片伊始的街訪部分中,既是導(dǎo)演意圖的實施者,同時也是創(chuàng)作者一員的她還是《夏日紀(jì)事》的錄音師。而后,他們采訪了瑪瑟琳和女助手,訪問了雷諾汽車修理廠的一些工人,畫家納蒂娜和亨利夫婦,工人安吉羅,在法國讀大學(xué)的黑人朗德,在巴黎打工的西蒙娜夫婦,一個在巴黎生活的年輕的意大利女人瑪麗羅,接著是大學(xué)生讓·皮埃爾,他曾是瑪瑟琳的情人,此后魯什和莫蘭又將前面采訪過的納蒂娜、亨利、瑪瑟琳、皮埃爾等人聚到一起,討論阿爾及利亞事件和大學(xué)生的問題。年輕人談了戰(zhàn)爭與青春,談到了他們對戰(zhàn)爭的反對。接下來是瑪瑟琳獨自走在空曠的巴黎協(xié)和廣場的長鏡頭,她在喃喃自語,是一段和死去的父親的獨白,回憶起過去在家鄉(xiāng)時,由于納粹對猶太人進行追捕而造成她和家人分離的那些日子。
至此在影片的海量采訪段落中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些變化,這種影像調(diào)查從一開始的街訪中籠統(tǒng)的廣義上的“你幸福嗎?”細(xì)化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每一個人對于生活的看法,以及每一個人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不同的生活經(jīng)歷,再到一群不同的人對于生活中的具體的一個問題做了討論(如阿爾及利亞事件)。影片前半段大家都在討論自己——比較個人,影片的后半段大家開始討論攝像機的視閾——開始轉(zhuǎn)向公共場所,多人討論,家庭聚會,較前半段更為開放。
在最后導(dǎo)演魯什和莫蘭又將大家齊聚在法國人類學(xué)電影資料館中放映這部分影像,大家對于影片的真實性提出了各自的意見。這在《夏日紀(jì)事》中是一個反饋的環(huán)節(jié)。魯什將這種分享式的人類學(xué)片拍攝手法,運用到紀(jì)錄片的制作中來,讓參與其中的人(包括魯什和莫蘭)都有一種“在場”的感受。
“電影具有揭示我們所有人的虛構(gòu)部分(to reveal a fictional part of all of us)的能力,盡管很多人對此表示懷疑,但對我而言這正是一個人的最真實的部分。”⑩
在魯什看來,《夏日紀(jì)事》不止是一部紀(jì)錄片,因為在影片中人們的真實生活被激發(fā)出了虛構(gòu)的樣貌;同時,它也不止是一部故事片,因為它所展現(xiàn)的虛構(gòu)部分都是真實的。
“我們面對的是一系列媒介,而且是騙人的媒介(lying intermediaries)。我們一會兒將時間壓縮,一會兒將時間伸長,我們選擇鏡頭角度,使拍攝對象變形,使事物的速度加快,并且在一個運動后面緊跟上另一個運動。因此,整個工作就是欺騙。但是,對我和莫蘭來說,我們在拍攝這部影片時,這種欺騙遠比真事真實(this lie was more real than the truth)。”
魯什承認(rèn)在創(chuàng)作《夏日紀(jì)事》過程中也確實造成了現(xiàn)實的變化,如果他們不拍此片,現(xiàn)實將是另一種樣子。這正是真實電影的最重要的特點:不是被動地等待事情的發(fā)生,而是去干預(yù)、去激發(fā),最終都是為了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的本質(zhì)。
從《夏日紀(jì)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影片中展現(xiàn)出的導(dǎo)演和演員之間的人際關(guān)系保持著一種適宜輕松的距離。他們在訪問被采訪者時,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去沉默、去回憶、去反應(yīng)。
在《夏日紀(jì)事》的結(jié)尾之前的過渡場面,表現(xiàn)被拍攝者看完自己的影像后展開討論的過程——這個“分享人類學(xué)”的段落正是對電影通過“虛構(gòu)”來展現(xiàn)真實的一個實踐宣言。
這個段落其實又給了所有被拍攝者一次展現(xiàn)內(nèi)心世界的機會,使片中的人物之間又一次產(chǎn)生碰撞。影片的張力又就此呈現(xiàn)——正是讓·魯什在做人類學(xué)影片時所體味到的“分享”的快樂。
拍電影永遠是一項聯(lián)合行動,因而“參與”是打開魯什作品中的主要線索,也是他電影中最核心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五、結(jié)語
“這是沒有結(jié)局的,電影的歷史是沒有結(jié)局的”——在《貝約爾·敘魯格與帕特里克·勒布特談話》中貝約爾這樣認(rèn)為。因此,筆者認(rèn)為讓?魯什主義的美學(xué)風(fēng)格也是未完待續(xù)的。理由如下:
首先,魯什的電影美學(xué)風(fēng)格是從他創(chuàng)作人類學(xué)紀(jì)錄片開始就始終保持著一種“在場”與“分享”的態(tài)度,這種美學(xué)風(fēng)格是有出處的,概括的來說可以是他在弗拉哈迪身上繼承了“分享”,在維爾托夫身上繼承了“在場”,兩者結(jié)合奠定了魯什電影美學(xué)風(fēng)格的基石。
其次,魯什控制攝像機的“在場”視閾,拉進了他和觀眾之間的距離,演員與導(dǎo)演在魯什的電影中以一種共同生活,共同成長的立場。在魯什的導(dǎo)演下,演員呈現(xiàn)在攝像機前,以“表演”的方式站在了觀眾的立場上。當(dāng)我們細(xì)細(xì)品讀《夏日紀(jì)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不僅僅是一部電影 ,更是一種“主動干預(yù)介入”的“巴黎城市調(diào)查”。
綜上,筆者認(rèn)為“在場”與“參與”是讓魯什紀(jì)錄片主要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注釋:
①[法]讓·魯什.《讓·魯什與皮埃爾·安德烈·布當(dāng)格的對話》,1980。
②詹先玲:《關(guān)于真實的冒險——讓·魯什紀(jì)錄電影研究》,碩士學(xué)位論文,北京師范大學(xué),2008年。
③[法]《貝約爾·敘魯格與帕特里克·勒布特談話》,1980.
④林少雄,諾埃爾·卡羅爾:《非虛構(gòu)電影與后現(xiàn)代主義懷疑論.多元化視閾中的紀(jì)實影片》,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320頁。
⑤邵露虹:《從人類學(xué)記錄片到真實電影》,碩士學(xué)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xué),2008年,第6-10頁。
⑥[法]保羅·霍金斯編,大衛(wèi)·麥克道格:《跨越觀察法電影.影視人類學(xué)原理》,昆明: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頁。
⑦張同道:《冒險是我的職業(yè)——讓魯什訪談》,《電影藝術(shù)》,2007第1期。
⑧聶欣如:《“在場”與原始思維.紀(jì)錄片研究》,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113頁。
⑨[法]讓·魯什:《夏日紀(jì)事》,1960.
⑩[法]保羅·霍金斯編,讓·魯什:《攝影機與人.影視人類學(xué)原理》,昆明: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75-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