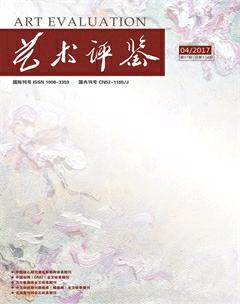詞之婉約與豪放辨析
薛寒冬
摘要:關于婉約與豪放的說法早已見諸詞論,廣為人知。詞作為文學體裁的抒情特質,古今一體,從未改變,對于抒情作品易于感悟而難于分類研究。與此同時,作家的深層感悟又因時移世易而變化萬千,故而以豪放婉約來劃分詞人必然會存在不準確之處。
關鍵詞:豪放 婉約 詞 抒情
中圖分類號:J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7-0169-03
一、詞的起源與抒情特質
關于詞的起源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 有人認為詞作為文體最早起源于宮體詩,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宋代的王灼,他在自己的詞學理論著作《碧雞漫志》卷一論述了詞的起源,將詞的源頭追溯到上古時期,而將詞作為文體的起源追溯至隋代宮廷,他指出:“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宋代張炎在《詞源》之中也持同樣的觀點:“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為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在郭茂倩所編纂的《樂府詩集》中的《近代曲辭》部分舉出隋煬帝所作《紀遼東》二首,其中第二首如下:“遼東海北翦長鯨,風云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鎬京。”
“前歌后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可以看到這首作品在句式結構、字聲和用韻方面與后世詞的形式一般無二。《隋書·音樂志》中有記載稱隋文帝雅號音樂并且制定新樂,而他的繼任者隋煬帝更是親命樂工作《斗百草》《泛龍舟》等曲。有人認為詞最早起于民間。《敦煌曲子詞集》收錄有一百六十多首詞作,其中僅有五篇作品已考知為溫庭筠、歐陽炯、李杰等人所作,其余絕大多數的作品來自民間,出于無名氏之手。敦煌曲子詞以充分,堅實的證據證明民間創作是詞的最早來源。
雖然關于詞的起源說法不一,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自詞產生以來,一直從未脫離抒情文體這一藩籬。早在初、盛唐時已有文人詞作傳世,如李白有《菩薩蠻》《憶秦娥》傳世,韓翃有《章臺柳》,張志和作《漁歌》,戴叔倫作《轉應曲》,韋應物作《調笑》等等。到了中唐,白居易、劉禹錫“依曲拍為句”有《憶江南》等作品。晚唐五代時期,社會的變遷動蕩卻反而促成了詞的體制進一步得到確立,出現了專作詞的詞人以及收錄詞作的專集。五代時期,溫庭筠被尊為“花間鼻祖”,《花間集》收錄其詞六十六首,但是其詞作藝術成就遠在花間眾人之上。在溫庭筠之后,寫詞的文人越來越多,詞人隊伍日漸龐大。五代十國時期,倚聲填詞更是尉為成風。五代時期,若論作詞當首推西蜀、南唐二地。西蜀地處四川盆地,號稱天府之國,而南唐更是“比年豐稔,兵食有余”,兩地經濟文化甚為發達,于是進一步成為詞人匯集的兩大基地。西蜀詞人的詞作大多數都收錄在《花間集》中。西蜀花間詞人中,成就最高可與溫庭筠并稱的是韋莊;而南唐詞人則以李璟、李煜父子二人,以及其臣子馮延巳最為出色。人稱李后主變伶工詞而為士大夫詞,自此,詞作為一種文體而獨立出來,與詩并道而行。入宋,詞壇名家輩出,佳作紛呈,進入了空前絕后的繁榮時期,出現了柳永、張先、秦觀、蘇軾、李清照、周邦彥等一大批優秀的詞人詞作。最終,宋詞得與唐詩并稱,被后人尊為一代文學之勝。不過可惜的是與此同時,民間詞也逐漸被忽略、被邊緣化,并且最終甚至被埋沒了。詞于宋代達到巔峰之后,在元明時代衰落了三百多年,而后在清代重新進入新的發展狀態,出現了一批代表性的詞人詞作,清初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中期以張惠言為代表的常州詞派等。自隋初至清末一千多年間詞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經歷了多次的發展與變革,但是抒情性這一基本特質從未改變過。
二、抒情作品的宗旨在于理解
詞作為一種文學作品其首要任務是感情傳達的載體。理論研究是我說了你記住,而文學作品是我傳情你感受。情是千變萬化的,所以以作品風格而劃分作品流派甚至是作家流派是有失允妥的。時移事異,作者的感懷不一,這是文學史上常見的現象,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李清照。以南渡為界,李清照的前后詞風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她作為一個柔弱女子親歷社會動蕩、家國淪亡,生活巨變使得她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種變化相應的是,其前后期詞作在內容、情調乃至色彩、音響,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明麗清新變為低徊惆悵、深哀入骨。即使是同樣的物象,比如大雁,前期是《一剪梅》中“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是滿懷期待的思念,是不乏樂觀成分與積極態度的;但是到了后期《聲聲慢》“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是充滿傷感色彩的低訴。時事變遷使得作者風格發生了明顯變化的還有蘇軾,在發生“烏臺詩案”之前,蘇軾歷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可謂政績卓著。其詞作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充斥著儒家進取思想。而在“烏臺詩案”發生之后,其詞作再難見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平淡曠達之情日漸顯露。可見,一個作家在作品中的感情是隨之人生際遇而千變萬化的。
三、詞的豪放與婉約
詞在唐代已小露鋒芒,到宋代達到頂峰。著名的詞人有李煜、柳永、晏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李清照、蘇軾、辛棄疾等。印象中,豪放派代表人物是蘇辛,婉約派代表人物是柳永、李清照。但筆者要提的一點是,不能因為某位詞人的某類型作品出名就把他歸為某類詞人,豪放派與婉約派的區別只在于詞而非詞人。
以“豪放”“婉約”論詞的說法最早見于明人張綖的《詩余圖譜》:“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醞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秦觀)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蘇軾)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婉約詞一直處于正統地位,即使到了南宋,王朝風雨飄搖的政治局面、民族興亡的關鍵時刻,一部分進步的詞人感到豪放詞有利于抒發愛國之情,抗敵之心,豪放詞有了長足的發展,但這并未改變詞壇上詞風以綺靡濃麗、柔婉含蓄為主的局面。《吹劍錄》有云:“東坡在玉堂曰,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這里把蘇東坡與柳三變的詞進行比較,一個壯如東北大漢,一個嬌如江南女子。
說到豪放詞派,歷代評論者首推蘇辛。提到蘇軾,不得不提的應該就是《念奴嬌·赤壁懷古》這首詞是豪放詞的代表。但是,在蘇軾的詞作之中也有大量的婉約詞,比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每每讀到這首他悼念亡妻的作品時,都會感慨他的用情至深。再說辛棄疾,他的豪放作品《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之類自不必說,但是不要忘記他還有很多婉約作品,比如,《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上片寫春意闌珊,而下片寫美人遭妒,全詞借用女子口吻寫得哀婉凄惻,柔中寓剛。可謂不折不扣的婉約詞。
再說婉約,被十七八妖童媛女手執紅牙板而歌的柳七郎,為世人廣為傳頌的是他《雨霖鈴》中:“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但是他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抒發了作者羈旅行役之苦,以及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上片首先描繪了一幅雨后清秋圖,而后進一步描寫物華漸休的凄涼之景;下片抒寫詞人久羈他鄉急切盼歸之情。全詞語淺而情深,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寫出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典型感受,從而成為傳誦千古的名篇。這是柳永不可多得的豪放詞佳作。
說婉約必不可繞開而行的是李清照。不管是“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還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都讓人對這位弱柳扶風的女子心生憐愛。而她的《漁家傲》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豪放的李清照。在大鵬高舉的時刻,詞人大喝一聲:“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可謂是豪氣沖天,一往無前,確實不愧為豪放詞。難怪前人黃寥園云:“此似不甚經意之作,卻渾成大雅,無一毫釵粉氣,自是北宋風格。”梁啟超也在《藝蘅館詞選》中說其“絕似蘇辛派”。一個封建官宦家庭出身的柔弱女子能有此不凡的志向和抱負,真是“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須眉”。
四、結語
不管是豪放還是婉約,都是作者感情的表達,都沒有違背詞作為一種文體“抒情”的基本特性。在眾多詩詞類型中,豪放與婉約可以說是對立的,但是它們又是統一的。作者的情感,在表達之時,就已奠定作品的感情基調。但不管是何種感情,都是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入,因而豪放與婉約又是統一的。
王國維《人間詞話》云:“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筆者認為,這里的優美、宏壯就是婉約與豪放。雖然靜安先生是以此來說明境界,但境界未嘗不是一種風格的體現。因婉約而成的“無我之境”,豪放而成的“有我之境”,都是詩人自身情感的傾注,沒有優劣之別,只有喜歡與否。
豪放與婉約的多樣與統一,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它們有不同的圖案,卻統一于同一個物體。所以,對于豪放與婉約而言,沒有好壞,只有喜惡。蔣勛有一個說法,他認為男性文化與女性文化其實是相互滲透互為補充的,太過陽剛會變成粗魯,而相反的太過女性會變成低靡,所以說并不存在豪放與婉約的明確界限,也不可以一概全地說哪個作家屬于豪放派哪個屬于婉約派。通過以上的示例我們可以看到,所謂豪放派也不乏柔美纏綿之作,而所謂的婉約代表人物亦可見曠達壯懷之氣。所以我們可以具體到某一首以豪放婉約論詞,但以豪放婉約論詞人就顯得不夠嚴謹,也有悖詞表情達意的主要特性。
參考文獻:
[1]唐圭璋.詞學論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編.詞學論稿[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3]宛敏灝.詞學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陳弘治.詞學今論[M].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5]施蟄存詞學名.詞釋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8.
[6]馬興榮.詞學綜論[M].濟南:齊魯書社,1989.
[7]梁榮基.詞學理論綜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8]繆危鉞,葉嘉瑩.詞學古今談[M].長沙:岳麓書社,1993.
[9]龍榆生.詞學十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0]吳梅.詞學通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