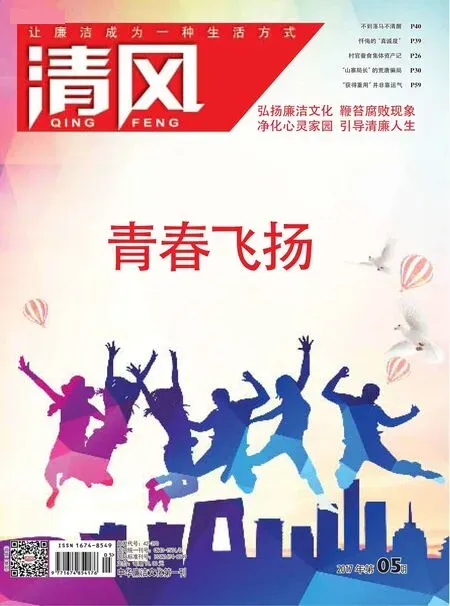梁啟超家教的奧秘
文__劉緒義(湖南長沙)
梁啟超家教的奧秘
文__劉緒義(湖南長沙)

梁啟超紀念館(化定興 攝)
一個人同時擔負起九個子女的教育任務,這在面臨生不生二胎時還優柔寡斷的現代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民國時期就有一個既要活躍于學術貢獻于社會,又要花大量精力教育遠在天邊的子女的人,他就是梁啟超。
早年熱衷于政治的梁啟超,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中,成為卓有影響的啟蒙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當他看透了當時政治的腐敗,飽受了精神上的失望和疲憊,無奈退回書齋,走上了學術救國的道路后,又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術泰斗。但是,他并沒有因此耽誤對子女的教育,進而演繹了一幕滿門俊秀的家教傳奇。
“個性加氣象”教育
“寶貝,你們好嗎?”在梁啟超給子女們寫下的數以百計的家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父親滿紙的愛。
但是,梁啟超對子女的愛并非表現在給他們最好的物質生活上,而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當孩子們小時,他愿意花時間與他們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點滴樂趣,像個老頑童一樣和孩子們一起玩耍:夏日,他與孩子們一起去北戴河度假,游泳,出海抓魚。游玩的同時,他還很注意欣賞孩子,用幽默的語言記下了發生在孩子們身上的很多趣事。
孩子們長大后相繼離開外出求學,他對他們的關愛則通過書信表達,最淋漓盡致的莫過于在稱呼上,諸如“大寶貝思順”“小寶貝莊莊”“老BEBY”“達達”“忠忠”等,毫不掩飾對子女的愛,讓每一個子女都覺得自己最受寵。有一次他給梁思莊寫信,信中說:“小寶貝莊莊: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這得意之作裱成這玲瓏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給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會搶你的,你卻要提防你那兩位淘氣的哥哥,他們會氣不忿呢,萬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吳淞半江水’的手段來卻糟了,小乖乖,你趕緊收好吧。”
九個子女中,梁啟超花在長子梁思成身上的心力尤多。有一次,梁啟超給梁思順寫信:“我們家幾個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絕無問題了。思成呢?我就怕因為徽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牽動,憂傷憔悴是容易消磨人的志氣的(最怕的是慢慢地磨)。我所憂慮者還不在物質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因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狹的人,一定抵不住憂傷憔悴,影響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毀了。你看不至如此吧!關于這一點,你要常常幫助這思成預防。總要常常保持著元氣淋漓的氣象,才有前途事業之可言。”
梁思成成長之路并不順利,再加上他與林徽因的愛情問題,讓梁啟超多了幾分擔憂:“我這兩年對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異兆的感覺,怕他漸漸地會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來見我時,還我一個三四年前活潑有春氣的孩子,我就心滿意足了。”“保持元氣淋漓的氣象”,是他家教的支柱理念之一。梁啟超家教之法深受他崇拜的曾國藩的影響,曾氏“盛衰在氣象”的教育理念在梁氏這里進化成“元氣淋漓的氣象”。
具體說來,就是注重子女的個性教育。個性是人格的表征,備有人格,方才享有人權。“個性不發展,則所謂世界大同、人類平等之諸理想皆未有實現。”可見梁啟超對尊重每個人的個性發展的重視,將它與人類平等理想實現聯系起來。因此,梁氏家教極為尊重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尊重子女依據他們的性情選擇專業。
有個性,方才不會輕易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方能獨立思想和自由判斷。有個性,方才有創新能力。因此,梁啟超對孩子們總是扮演著好朋友的角色,只給建議,不求照辦,做無代溝的老爸。次女思莊留學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大一讀完基礎課,選專業時,梁啟超考慮到現代生物學在中國是個空白,希望她學這個。思莊從了。但課程很乏味,思莊提不起興趣,向大哥思成訴苦。梁啟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寫信讓她選擇喜歡的專業,改學圖書館學,后思莊終成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梁啟超不主張兒女們做官,針對每個孩子的個性和特長,建議他們選擇一條更適合的道路。因此,他的九個子女無一人從政。
“趣味加擔當”教育
梁啟超一生于思想啟蒙、社會活動和學術研究上用功之勤,于厚厚的《飲冰室合集》即可看出,然而,繁重的社會活動和學術研究并沒有使他成為無趣的學究。
1922年梁啟超在《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的演講中,開宗明義:“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什么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
在子女教育上,梁氏更是強調趣味,“人的一生要有趣味,無趣味則無意義”,強調生活情趣和人生樂趣,鼓勵子女培養情趣,“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么生命便成為沙漠,要來何用?”希望子女們不要讀死書、死讀書,不求出人頭地,順其自然,率性發展,找到自己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樂趣。他給思成的信中這么寫道:“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他告誡思成:“我以為,一個人什么病都可醫,惟有‘悲觀病’最不可醫,悲觀是腐蝕人心的最大的毒菌。”他擔心思成留學歸國后很難馬上找到合適的工作而失望沮喪,幵導思成說:“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最可怖之敵,我們須終身不許它侵入。”
在梁氏看來,喚起趣味的目的是要防止“悲觀病”,擔負起社會責任。1919年12月2日,梁啟超給思順信中說:“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人生在世,常要思報社會之恩,因自己的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1927年1月27日梁啟超又對孩子們說:“中國病太深了,癥候天天變,每變一癥,病深一度,將來能否在我們手上救活轉來,真不敢說。但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見,都不必管。”這種永不悲觀、盡我之責、不求其效的態度正是他極為認同的曾國藩“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理念的升華。
后來,他的九個子女都為中國的科學與文化教育事業貢獻出巨大的智慧和力量,應該說就是拜這種“趣味加擔當”教育所賜。
“堅韌加吃苦”教育
看上去,梁啟超可謂“史上最寬的爹”,但他并不溺愛,他對孩子們說,“你們諒來都知道,爹爹雖然是摯愛你們,卻從不肯姑息溺愛,常常盼望你們在困苦危險中把人格能磨練出來。”“一個人在物質上的享用,只要能維持著生命便夠了,至于快樂與否,全不是物質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樂,才真是會打算盤哩。”
梁啟超認為吃得苦才能有擔當,他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在這方面,梁氏重視言傳身教,以身作則,“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們姊妹弟兄的模范。”以自己作典范來塑造子女完整人格。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梁啟超希望孩子們以勞作為樂趣:“各人選擇趣味最濃的事項做職業,自然一切勞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勞作越有趣。” 他教育孩子們正視生活中的苦難,形成正確的苦樂觀:“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覺苦,不致為苦所窘耳”。
他對思順說:“你們比你們的父母,已經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許要比現在加多少倍,拿現在當作一種學校,慢慢磨練自己,真是再好不過的事,你們該感謝上帝。”“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對于生活的憂患,梁啟超告誡孩子們千萬不要抱怨,要把它當成考驗和磨礪自己的機會,打起精神與困苦作斗爭,在一次次的磨練中,讓自己更加強大。
在這種教育熏陶下,孩子們真的都能往吃苦路上走。思成留學歸來后,毅然選擇留在東北大學任教,雖然條件比較惡劣,但仍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績。在抗戰期間,他和林徽因都身患疾病,在四川過著艱苦的生活。他拒絕了美國一些大學發出的聘請:“我的祖國正在危難之中,我不能離開她,哪怕僅僅是暫時的。”為了祖國,他毫無怨言地承受著生活的苦。思永走在考古的路上,長年于野外風餐露宿,體力衰弱的他吃盡了苦頭,但是從不抱怨,為中國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思禮留學美國期間,靠勤工儉學自己養活自己,在飯館端過盤子,洗過碗,在游泳池當過救生員,在罐頭廠裝過罐頭。梁思莊早年喪夫,獨自一人撫養幼女。孤兒寡母歷經千辛萬苦到成都燕京大學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一直為祖國的圖書館事業奮斗,直到臥病不起。梁思達和夫人俞雪績抗戰時在四川中國銀行工作,在矮小的草屋里領略當年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真實情境,堅持到抗戰勝利。
(作者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