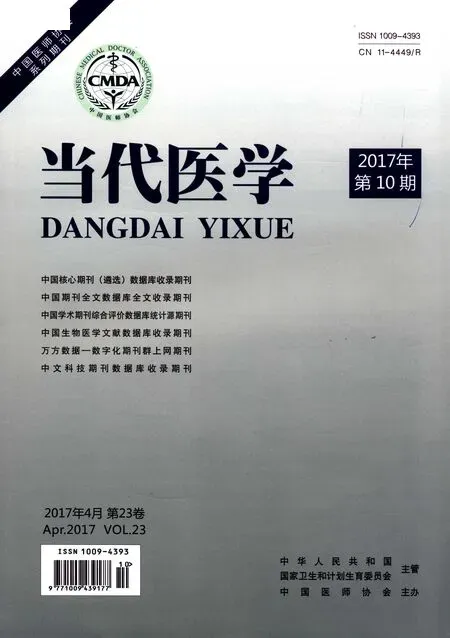難治性癲癇的預測因素
王芳,王愛文,成亞東(1.山西醫科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1;.長治市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山西 長治 046000)
難治性癲癇的預測因素
王芳1,2,王愛文2,成亞東2
(1.山西醫科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1;2.長治市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山西 長治 046000)
目的 探討難治性癲癇的預測因素。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例癲癇患者的臨床資料,按照藥物治療效果分為觀察組100例(藥物難治性癲癇DNR-EP)和對照組100例(藥物有效性癲癇DR-EP)。觀察2組患者的年齡、初次發病年齡、高熱驚厥史、既往腦損傷史、圍產期高危因素、陽性家族史、神經功能缺損癥狀及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有效、部分性發作、多種發作類型、影像學異常、智能障礙、精神心理異常、治療后腦電圖癲癇波異常等因素。結果 觀察組和對照組患者在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有效、部分性發作、多種發作類型、影像學異常、智能障礙、精神心理異常、治療后腦電圖癲癇波異常方面比較:55例(55.0%)比85例(85.0%),73例(73.0%)比55例(55.0%),78例(78.0%)比51例(51.0%),72例(72.0%)比49例(49.0%),78例(78.0%)比58例(58.0%),75例(75.0%)比55例(55.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部分性發作、多種發作類型、影像學異常改變、智能障礙、精神心理異常、治療后腦電圖癲癇波異常為難治性癲癇的預測因素。
難治性癲癇;預測因素
癲癇(epilepsy)是一種由多種原因引起的中樞神經元高度同步化異常放電的臨床綜合征,根據異常放電起源腦內部位可分為運動、感覺、語言、自主神經、情緒等發作或兼而有之,是僅次于腦血管病的第二位高發神經系統疾病。全世界有超過5千萬人為其所累,我國約有900萬的癲癇患者[1],每天有16~30/50萬新發癲癇患者,其中25%~30%為難治性癲癇(intractable epilepsy,IE)。難治性癲癇又稱頑固性癲癇,是指頻繁的癲癇發作,至少每月4次以上,應用適當的第一線抗癲癇藥物正規治療且藥物血濃度在有效范圍內,至少觀察2年,仍不能控制發作且影響日常生活;無進行性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或占位性病變[2]。目前,難治性癲癇臨床研究資料很少,國外研究[3]證實難治性癲癇的危險因素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發病早;腦電圖背景異常;單純部分性、強直和肌陣攣發作;癲癇持續狀態病史;發育異常;影像學異常改變。本課題回顧性分析200例癲癇患者的臨床特點,尋找難治性癲癇的預測因素,為難治性癲癇患者的規范化治療提供依據,積極提高難治性癲癇的控制率和治愈率。我們研究了一些相關因素,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2010年10月~2015年10月于長治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神經外科、重癥醫學科、兒科住院的癲癇患者200例。癲癇診斷符合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的診斷標準,發作至少間隔24 h連續3次以上,且腦電圖符合癲癇樣放電;癲癇發作類型及癲癇綜合征類型診斷同樣符合1989年國際抗癲癇聯盟的診斷標準。(1)部分性發作:包括單純部分性發作、復雜部分性發作;(2)全面性發作:包括強直-陣攣性發作、強直性發作、陣攣性發作、肌陣攣發作、失神發作、失張力發作;(3)部分性發作繼發全面性發作。參考國際抗癲癇聯盟初次單藥治療癲癇指南,給予合理抗癲癇藥物治療。根據藥物治療有效情況,分為難治性癲癇組和藥物治療有效組。癲癇患者對藥物治療反應性的定義參照既往國際研究的常用標準。(1)藥物難治性癲癇(drug non-responsive epilepsy,DNR-EP):應用適當的第一線抗癲癇藥物正規治療且藥物血濃度在有效范圍內,至少觀察2年,仍不能控制發作且影響日常生活的頻繁的癲癇發作,至少每月4次以上,無進行性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或占位性病變;(2)藥物有效性癲癇(drug-responsive epilepsy,DR-EP):應用適當的第一線抗癲癇藥物正規治療,至少觀察2年無發作者。收集的病例依據抗癲癇藥物治療效果進行分組,觀察組100例患者為藥物難治性癲癇組,對照組100例患者為藥物有效性癲癇組,全部病例行頭顱CT或MRI檢查。對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構成等基本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保證兩組之間的可比性。觀察組男52例,女48例,平均(32.6±13.24)歲,對照組男48例,女52例,平均(31.6±14.46)歲,兩組年齡、性別匹配,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 測定方法 記錄所有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初次發病年齡、高熱驚厥史、既往腦損傷史、圍產期高危因素、陽性家族史、神經功能缺損癥狀及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有效、部分性發作、多種發作類型、影像學異常、智能障礙、精神心理異常、治療后腦電圖癲癇波異常等因素。觀察組病情變化時復查頭顱CT或MRI。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采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n,%”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單因素分析 經比較兩組在年齡、性別、初次發病年齡、高熱驚厥史、既往腦損傷史、圍產期高危因素、陽性家族史、神經功能缺損癥狀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2.2 兩組患者在其它方面的比較 經比較觀察組在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部分性發作、多種發作類型、影像學異常、智能障礙、精神心理異常、治療后腦電圖癲癇波異常方面發生率較對照組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1 兩組患者危險因素的比較(±s,n=100)

表1 兩組患者危險因素的比較(±s,n=100)
項目年齡(歲)初次發病年齡高熱驚厥史既往腦損傷史圍產期高危因素陽性家族史神經功能缺損癥狀觀察組(DNR-EP)32.6±13.24 12.6±12.1 26 25 19 26 34對照組(DR-EP) 31.6±14.46 15.7±13.5 18 19 13 19 26 χ2/t值0.51 1.71 1.86 1.04 1.34 1.40 1.52 P值>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兩組患者在其它高危因素的比較(n=100)
3 討論
3.1 本研究發現兩組在年齡、性別、初次發病年齡、高熱驚厥史、既往腦損傷史、圍產期高危因素、陽性家族史、神經功能缺損癥狀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說明難治性癲癇患者在人口學特征、既往疾病史、家族史、神經損害程度方面無特殊差異,也就是病程進展損害過程是難治性癲癇發病的重要因素。
3.2 本研究發現觀察組在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部分性發作、多種發作類型、影像學異常、智能障礙、精神心理異常、治療后腦電圖癲癇波異常方面發生率較對照組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2.1 難治性癲癇與對照組相比初次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多見,癲癇首選抗癲癇藥物治療,約2/3癲癇患者抗癲癇藥物治療基本能控制,1/3癲癇患者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稱為難治性癲癇。目前研究最多的是P糖蛋白(Pgp)及多藥耐藥相關蛋白(MRPI-5)。KubotaH[4]等對癲癇患者手術切除標本的研究發現,顳葉內皮細胞Pgp及MRP2有過度表達。
3.2.2 難治性癲癇與對照組相比部分性發作多見,不同發作類型和癲癇綜合征對癲癇預后的影響各異,國外Arts[5]等對453例新診斷癲癇患兒隨訪5年,發現隱源性或癥狀性癲癇是易發展為難治性癲癇的預測因素;國外Picot等[6]和Gururaj等[7]的研究結果均顯示,不管是成人或兒童癲癇患者,癥狀性部位相關性癲癇在難治性癲癇患者中更常見,其他研究也得出類似結果[8]。
3.2.3 難治性癲癇與對照組相比影像學異常多見,觀察組72例經過頭部CT或MRI掃描發現了顱內病灶及致癇灶,比例為72%,明顯高于對照組。影像學異常說明難治性癲癇患者存在各種明確的病因,另一方面,難治性癲癇頻繁發作癲癇造成的腦組織損害,可以在影像學檢查中表現出來。
綜上所述,難治性癲癇患者在年齡、性別、初次發病年齡、高熱驚厥史、既往腦損傷史、圍產期高危因素、陽性家族史、神經功能缺損癥狀方面無明顯差異。
近年來,難治性癲癇患者其它治療方法逐漸發展起來,其中手術治療逐漸被廣泛接受,外科手術可以終止90%具有手術適應癥患者的癲癇發作,手術方法包括:致癇灶切除術、前顳葉切除術、大腦鐮切開術、胼胝體切除術、顱內電刺激術、迷走神經刺激術、立體定向放射治療等。
[1] 欒國明.積極穩妥地開展癲癇外科手術[J].中華神經外科雜志,2002,18(4):207-208.
[2] Brodie MJ.Diagnosing and predicting refractory epilepsy[J].Acta NeurolScand,2005,112(Suppl181):36-37.
[3] Berg AT,Shinnar S,Levy SR.Early development of intractable epilepsy in children: a prospective study[J].Neurology,2001,56:1445-1452.
[4] KubotaH,IshiharaH,Langm ann T,et al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al activity of P-glycoprotein and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s in 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hippocampal sclerosis[J].Epilepsy Res,2006,68(3):213-214.
[5] Arts WF,Brouwer OF,Peters AC,et al.Course and prognosis of childhood epilepsy:5-year follow-up of the Dutch study of epilepsy in childhood[J].Brain,2004, 127:1774-1784.
[6] Gururaj A,Sztriha L,Hertecant J,et al.Clinical predictors of intractable childhood epilepsy[J].J Psychosom Res,2006,61:343-347.
[7] Kwan P,Brodie MJ.Early identification of refractory epilepsy[J].NEngl J Med,2000,342:314-319.
[8] 張燕芳,狄晴.難治性癲癇:臨床界定的難題[J].中華神經科雜志,2010(43):493-495.
10.3969/j.issn.1009-4393.2017.1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