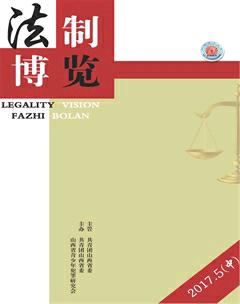論“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主客體中的雙向應用
摘 要:隨著法治化進程和建設現代化文明監獄進程的加快,保障罪犯人權的呼聲日益高漲,監獄面臨從“重強制、重規范”的傳統管理模式向“人性化”的新型管理模式轉型。近年來,罪犯管理工作中的傳統硬性手段逐漸被文明程度更高的新形式軟手段所取代。罪犯管理工作中傳統硬性手段所占比重的壓縮使得罪犯管理工作面臨瓶頸,如何運用新形式軟手段突破瓶頸已然成為一個不可規避的課題。本文旨在通過對“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主客體中的雙向應用的研究,試圖尋找出既能保障罪犯人權又能保障管理效果的“人性化”新型管理模式。
關鍵詞:陽明心學;罪犯管理工作主客體;雙向應用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7)14-0017-03
作者簡介:邵建偉,浙江余杭人,中國人民大學,本科,浙江省喬司監獄第六分監獄,黨總支委員、監獄長。
一、研究背景
在當前社會文明不斷進步,法治化進程和建設現代化文明監獄進程不斷加快,罪犯管理工作接受輿論監督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的大環境下,監獄面臨從“重強制、重規范”的傳統管理模式向“人性化”的新型管理模式轉型。近年來,罪犯管理工作中的傳統硬性手段逐漸被文明程度更高的新形式軟手段所取代。罪犯管理工作中傳統硬性手段所占比重的壓縮使得罪犯管理工作面臨瓶頸,如何運用新形式軟手段突破瓶頸已然成為一個不可規避的課題。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屢次談到王陽明及其心學。2015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談論時談到“王陽明的心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對王陽明的歷史作用進行了肯定。2017年,浙江省黨委書記、廳長兼浙江省監獄管理局第一政委馬柏偉提出,要突出服刑人員的“心靈改造”,以塑造健康人格為目標,以破除“犯罪人格”和“監獄人格”為重點,以再社會化為引領,在原有教育改造手段的基礎上,探索開展“修心教育”,努力把服刑人員教育改造成為人格健康、適應社會、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
鑒于以上背景,本文旨在通過對“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主客體中的雙向應用的研究,試圖尋找出既能保障罪犯人權又能保障管理效果的“人性化”新型管理模式。
二、“陽明心學”淺析
王守仁(1472-1529),漢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世稱陽明先生,故又稱王陽明。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哲學家,精通儒、釋、道。他早年學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廣讀朱熹遺書,后轉向陸九淵心學,并加以發展,成為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陽明心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不論對當時還是后世,對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有著廣泛的影響。
“陽明心學”的思想體系主要包括以下三大命題: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陽明心學的邏輯起點。“心即理”的理論基礎是物我一論,即身、心、意、知、物是渾然一體的,不能夠獨立自存。王陽明認為,朱熹將“心”與“理”加以隔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樣會導致“知行”分離。為此,他繼承和發揮了陸九淵的思想,認為“萬物皆歸于吾心”。[1]王陽明認為,人對外物的認知是本能,而心之本體為至善,只要能將這種本能發揮到極致,那么吾心便是天理。在此基礎上,王陽明更進一步提出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王陽明曾說“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1]認為理全在人心,應該向內求索。心在,天地在,枯木也逢春;心亡,天地亡,盛夏也嚴寒。
(二)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陽明的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基礎來源于孟子的“良知”觀點。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2]王陽明經過進一步的深入闡發,在晚年將其理論概括為“致良知”。王陽明將良知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認為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把良知等同于天理,良知便成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陽明看來,“良知”本就在人們心里,人性至善,這是人性的“本然”。而“致”的功夫就是“事上磨煉”,用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為,此乃“明覺”。“致良知”就是在實際行動中實現良知,這就是王陽明的“心本體論”與“修養論”直接統一的表現。
(三)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核心與精髓。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此處的“知”不是“知道”的“知”,而是“良知”的“知”,是每個人內心與身俱來的道德感與判斷力。找到并遵循內心的良知,復雜的外部世界就將變得格外清晰,致勝決斷,了然于心。[3]王陽明認為,知是行的主導,行是知的體現,“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由此可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將認識論與實踐論高度統一,批判了“先知后行”與“重知輕行”,認為“知行”本就是一個整體,不可離開實踐空談學問,不去實踐永遠得不到真理。
總而言之,陽明心學博大精深,本文僅淺析幾點。他的心學思想突出了良知與心的主體作用,弘揚了主體精神的雄渾博大,故將其心學思想融入罪犯管理工作并對探索開拓罪犯管理工作的新模式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三、現狀闡析
在罪犯管理工作中,管理的主體是民警,客體是罪犯即服刑人員。本文將從主客體兩方面進行闡析:
(一)“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客體中的應用現狀——以浙江省內某監獄為例
在浙江省黨委書記、廳長兼浙江省監獄管理局第一政委馬柏偉提出要探索開展“修心教育”之后,浙江省內某監獄將“陽明心學”廣泛應用于罪犯管理工作客體即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中,創新了教育改造模式,將以“陽明心學”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引入服刑人員教育改造,探索形成了一套以“四修四正”(“四修”即修心、修行、修性、修省,分別對應思想教育、行為矯正、藝術矯治、本質改造;“四正”即正言、正行、正諾、正品,分別對應言行規范、遵規守紀、信守承諾、品格健康)為內核,以“懺悔教育修良心”、“國學教育修善心”、“感恩教育修孝心”、“主題教育修正心”為驅動的新形勢下服刑人員“修心教育”的新模式。
由此可見,在浙江省內某監獄范圍內,“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客體即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中的應用相當廣泛而深入,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修心教育”新模式。
(二)“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主體中的應用現狀與不足——以浙江省內某監獄為例
相較于“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客體中的應用,目前“陽明心學”在主體中的應用就顯得相對缺乏且未形成較為完善的新模式。
1.罪犯管理工作主體即民警在思想意識上對融入“陽明心學”理念的“人性化”管理新模式認知不夠,觀念尚未轉變完全,心態尚未調整完善。
本文以對融入“陽明心學”理念的“人性化”管理新模式的看法為內容對浙江省內某監獄的某分監獄進行了問卷調查,發放問卷120份,回收113份。
調查結果顯示,48.67%的民警認為在實際管理中,“重強制、重規范”的傳統管理模式比較實用;有44.25%的民警認為融入“陽明心學”理念的“人性化”管理新模式能突破當前管理模式的瓶頸;還有7.08%的民警對融入“陽明心學”理念的“人性化”管理新模式不怎么了解。由此可見,部分民警在罪犯管理工作中對以往“重強制、重規范”的傳統管理模式依賴性較大,在管理工作中依然保持傳統管理模式的習慣性思維,對當前社會呼吁保障罪犯人權以及罪犯管理工作接受輿論監督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的大環境認識不清,對“人性化”管理的新模式認知不夠,在思想意識上并未轉變觀念、調整心態。說明部分民警并未意識到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傳統管理模式會導致罪犯及其家屬上訪投訴,從而使罪犯管理工作陷于被動;并未意識到“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中的對于探索開展罪犯“人性化”管理的新模式大有裨益;并未意識到當下亟需調整心態,管理工作亟需轉型,在管理過程當中應摒棄以往傳統模式中民警與罪犯的對立關系,利用“陽明心學”重建一種良好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
2.罪犯管理工作主體即民警在自身素質上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陽明心學”的學習與研究不夠,管理素質有待提高,自我修養亟待提升。
本文對浙江省內某監獄的某分監獄民警學習“陽明心學”的現狀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下發110份,回收107份,調查結果如下:
如圖可見,只有14.02%的民警系統研究了“陽明心學”,31.78%的民警大概了解“陽明心學”的理念,54.21%的民警尚未學習過“陽明心學”。由此可見,罪犯管理工作主體即民警在自身素質上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陽明心學”的學習與研究不夠,管理素質有待提高,自我修養亟待提升。
3.罪犯管理工作主體即民警在實際管理罪犯的過程中對于傳統硬性手段依賴較強,新形勢下傳統硬性手段的比重逐漸被壓縮,管理工作出現瓶頸。融入“陽明心學”的“人性化”新型管理并未形成系統且有理念指導的管理新模式,各項新型軟手段亟待探索應用。
四、對策及現實意義
針對以上現狀,結合“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客體中應用的“修心教育”,本文就“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主體中的應用提出了一套民警管理工作中的“心靈管理”理念:
“心靈管理”的核心思想來自于“陽明心學”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管理理念的內核為“以心為本”,驅動為“知行合一”。旨在將以往管理中“以人文本”的理念更深層次地提升到“以心為本”的全新管理理念,將“陽明心學”三大核心思想體系融入罪犯管理工作的每一處細節,突破“重強制、重規范”的傳統管理模式向“人性化”新型管理模式轉型期的瓶頸,使廣大民警在新形勢下罪犯管理工作中轉變管理觀念、調整管理心態、提升管理素質、創新管理手段,真正在管理中做到“知行合一”。同時與罪犯“修心教育”相互配合呼應,形成一套在新形勢下與時俱進且行之有效的的“人性化”新型管理模式。
(一)轉變思想意識方面
在民警中以“心靈管理”為主題開展一系列活動,通過在民警中開展各種關于新舊管理模式的辯論賽、座談會、視頻學習會等方式,將融入“陽明心學”的“心靈管理”與“重強制、重規范”的傳統管理模式做對比,將在當前大環境下傳統模式暴露的弊端與民警過度依賴傳統管理模式的硬性手段導致罪犯及其家屬上訪投訴從而民警管理陷入被動的風險案例進行剖析、學習和討論,通過各種形式轉變民警在管理工作中的傳統觀念,幫助民警在管理工作中摒棄舊式的“警囚對立”心態,重塑以“心靈管理”為理念指導的全新心態,讓廣大民警意識到當前的大環境下,只有在管理工作中轉變觀念,調整心態,才能在規避自身執法風險的同時與時俱進地將人性化“心靈管理”模式落實到位。
(二)提升自身素質方面
在民警中開展一系列有關“陽明心學”的講座及讀書活動,以各項生動有效的活動調動民警學習“陽明心學”的積極性,并采取一定的競賽獎勵措施,在民警中形成一股熱愛學習與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崇學新風”,促使民警在新形勢下不斷提高自我素質,提升自我修養,從而為更好地在罪犯管理工作中落實“人性化”新型管理模式奠定扎實的內在基礎。
(三)創新管理手段方面
1.在監內創建罪犯“修心室”,將陽明心學中的“心即理”和“致良知”的思想融入進“修心室”使用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
在管理過程中出現罪犯不服管教或是發現罪犯有自殺傾向等情況時,先不使用傳統硬性手段,優先使用“修心室”,引導罪犯在“修心室”內最大程度地發揮良知和心的主體作用,爭取將各種不安定因素和不良心態解決在“修心室”內。
2.創新罪犯個別談話教育模式,將“陽明心學”的“致良知”滲透到個別談話教育的每一個細節,爭取做到每一次個別談話教育都能追根溯源,以心為本。
北宋歐陽修說“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原”,即治療病患,要從病源生發處去治愈;拯救弊病,要從弊病本源處去解決。這種追根溯源、醫人治本、對癥下藥的思想,融入陽明心學的“心即理”與“致良知”,可以為罪犯管理工作提供一劑以心為本、標本兼治的藥方。本文認為,應當在民警隊伍中成立一支個別談話教育“修心團隊”。通過各種選拔方式將有個別談話教育專長、精通陽明心學理論以及具備專業心理咨詢師資質的民警整編為一支多元化、專業化及針對性強的“修心團隊”,針對罪犯的不同類型對癥下藥,為罪犯量身定制個別談話教育方案。例如針對文化程度較低且暴力傾向較為嚴重的罪犯需要“修心團隊”中善于簡潔明了地直擊問題本源的追根溯源型;針對文化程度較高且性格較為不合群的罪犯需要“修心團隊”中親和力較強且文化修養較高的諄諄善導型;針對存在一定心理問題的罪犯需要“修心團隊”中具有專業心理咨詢師資質的對癥下藥型等等。只有將陽明心學融入進個別談話教育的細節中去,才能真正發揮其良知與心的主體作用,才能通過罪犯管理工作中的主體即民警將陽明心學真正轉化為罪犯改造的內在原動力。
3.充分落實包干民警責任制,將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真正落實到罪犯管理工作的實際行動中去。要求每位民警對自己包干罪犯的“心之所想”掌握到位,并能為每一名自己包干的罪犯量身定制改造方案以及走上社會后的人生規劃,使每一名罪犯在高墻內能安心改造,走出高墻外能重獲新生,能真正做到將良知與行為“知行合一”。
綜上所述,“陽明心學”在罪犯管理工作中主客體的雙向應用對于新形勢下罪犯管理工作的創新與發展有著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 參 考 文 獻 ]
[1]王陽明.傳習錄上下冊[M].江蘇:廣陵書社,2010.
[2]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8.
[3]度陰山.知行合一王陽明[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