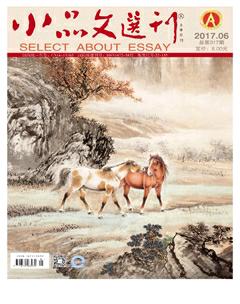沒病的人是無知的
陳思呈
去年某天,正一個人吃飯,突然心臟區域一陣絞痛。我停下碗筷品味陌生的疼痛,但恐懼的程度更大于疼痛的程度。因為想到前幾年某友心梗去世,也是類似的心臟絞痛,第一次發作時他并未引起重視,只以為感冒所致,第二天再次發病,便無力回天了。想到這里我趕緊給我婆婆打了個電話求助,說疑似心梗。
我婆婆心臟不好,經驗豐富,她聽我描述了癥狀之后,認為應該是心肌缺血。就帶著硝酸甘油之類的基礎急救藥往我家趕來。雖然彼時我已恢復正常,但吾友的前車之鑒陰影太深,我二話不說,便把我婆婆帶來的藥悉數吃下去。
其中一種是麝香救心丹,但我忘了和婆婆說明,當時我處于生理期,而我也不知道這個藥在生理期是禁服的。吃下之后心肌沒有再痛過,但出現新的癥狀,不到一小時,全身已被冷汗濕透,寒冷一陣陣襲擊兩條被子下的我。
兩天的時間我真正履行了一個病人的職責:沒離開床上那兩條被子。———盡管當時已經是四月。
對了,那天正好是四月一號。我瑟瑟發抖發了條朋友圈:我可能有心臟病!誰知,多數以為這是愚人節玩笑,完全得不到想象中的慨嘆或者關心。更有甚者,深圳的師兄趕緊微信告訴我:“看新聞,深圳設立了免費遺囑庫,要不就來深圳發展吧?”
大概是朋友的態度讓我覺得,不去醫院看一看倒顯得自己不真誠似的。從床上爬起來之后我就去醫院掛了個心臟科,查了心電圖胸透什么的,最后的結果是健康得可以上山打虎。我除了慶幸,也略有一點奇怪的空虛。
吾有一友甚至跟風聲稱她也有心臟病,她說,論起病來,心臟病好像顯得很優雅。那段時間,我無意讀到一本心理學著作,里面提到,“快樂也是一種有害的情緒,中醫說喜傷心,所以少壯就有心臟病的人,多半是成功太多的人。”這個說法簡直是為吾友的觀點添油加醋。
小疾怡情,有一些小疾似乎確實頗能增添風情。我們小時有個同學,她的骨骼比普通人要柔軟些,體現在她的手指甲都是軟的,可以一邊與我們聊天一邊把它像紙那樣撕下來。但似乎也沒有別的麻煩,只是家長讓體育老師稍微照顧她一些,因為她確實就是嬌弱些。這個備受照顧的女孩子一直有眾多的愛慕者,我總覺得與她的身體素質不無關系,這種可能稱不上疾病的疾病增加了她的神秘感,讓她區別于我們茫茫大眾。當然我也不得不心情復雜地交待一下,她確實長得非常美麗。
另一個風情出名的病美人,大概就是《圍城》中汪處厚的汪太太了。她患的也是具風雅的可能性的病:貧血,錢鐘書說她“終年嬌弱得很,愈使她的半老丈夫由憐而怕”,具體是怎么又憐又怕,這就不多說了。
至于心臟病,美國知識分子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提到了。她說:“沒有人會考慮對心臟病人隱瞞病情:患心臟病沒有什么丟人的。人們之所以對癌癥患者撒謊,不僅因為這種疾病是(或被認為是)死刑判決,還因為它———就這個詞原初的意義而言———令人感到厭惡:對感官來說,它顯得不祥、可惡、令人反感。心臟病意味著身體機能的衰弱、紊亂和喪失;它不會讓人感到不好意思,它與當初圍繞結核病患者并至今圍繞癌癥患者的那種禁忌無關。”
桑塔格說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談論疾病,沉重的筆觸似乎是一種起碼的修養。但在這沉重之外,若能感到各種疾病被我們或勢利、或無厘頭地品味出各種不同意味,似乎也是非常冷酷的幽默。
吉田兼好的《徒然草》里很漫不經心地寫過一句,有幾類人不能與之為友,前面幾類人都很合理,因此看過也就忘了,而最后一類人是———“身體很好、從不生病的人”———這句話里的道理,一時說不清楚,卻可以意會。從不生病大概有種不留余地的氣質,同樣也很難對“弱”有真正的體恤,因為他的想象力未必能細膩到讓他感同身受。
在那些偶爾的疼痛、微小的不適、可以迅速治愈的病患里,我們似乎能得到很多健康時得不到的人生況味。就像以前,我曾經不知道胃在哪里,自從有一次胃痛之后,就知道了它的位置。以此類推,是不是可以說,如果從來不知道心痛是怎么回事,也可能因為沒有患過愛情這種疾病。沒病的人是無知的。
選自《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