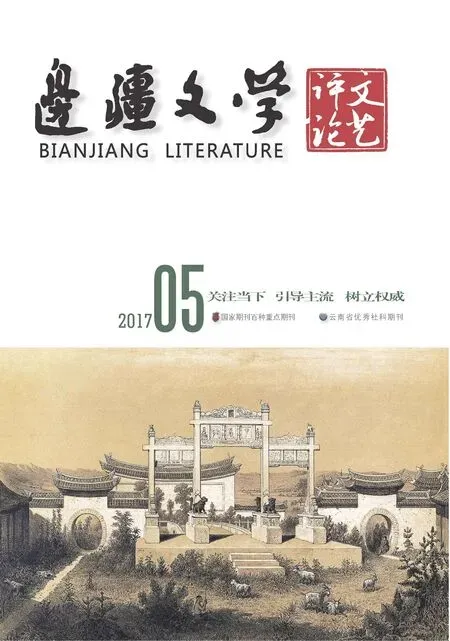讓理想引領文學走向美好
蔡 毅
讓理想引領文學走向美好
蔡 毅
寫完《加強文學的道德追求,創造高貴神圣的文學》的文章,我就知道該接著寫理想了。因為沿著敘事邏輯和個人思路,接下來就走到了文學最核心的地帶——理想高地。理想是內心的希望,是關于未來的愿景。理想不是空想、幻想,它是心靈思維向上的運動,雖然大多數時候看不見摸不著,卻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無形卻有力,指向價值世界的深層維度。理想通常是一種高遠的目標、具體的希望,它和現實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為人們描繪一幅美好的精神圖景,能喚起人們的強烈的奮斗動機與拼搏潛能,激勵人們投入積極的求索與創造,通過努力把尚未實現的東西轉化為現實。
理想高于現實,超越現實,所以它能引導人們突破現實去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理想挑戰自我,超越有限,引導人們不斷創新,拓展未來。理想有大小高低不同,理想的魅力在于未知、希望和未來。最高的理想是超越有限達到無限,用自己的思想與設計建立一個新世界。
理想能讓我們內心充滿希望,變得有方向,有目標、有力量,日益飽滿,濕潤和善良。人是在追求和實現理想的過程中獲得幸福的。阿諾德曾說:“文化以美好與光明為完美之品格”。仿照此話我要說:理想以“高大上”為品格。“高”,高度、高端、高遠;“大”,大氣、大義、大雅、大道;“上”,上進,上升,上乘、上檔次。與之相連的積極進取、朝氣蓬勃、豪情萬丈,都是其基本品格。理想具有超凡脫俗的魔力,它非實現不可的特性鼓勵人“上窮碧落下黃泉”,不斷從事探索和追尋,誘導人“風物長宜放眼量”,培養人“不爭一時長短,而爭一世高低”,讓我們在關注現實問題時,更要看到一片廣闊的原野。庸常的生活波瀾不驚,理想讓人們從陳陳相因的瑣碎事務中浮出頭來,呼吸到神奇的氣息。所以,理想是讓“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法寶。理想能讓生命發光,讓生命和生活更美好。
人是永遠力圖超越有限的存在,而向往無限未來的存在物。人之所以為人,因為人有迥異于萬物的人性、靈性,更有人性與靈性交融而升華成的精神境界——理想。“人類自有理想,乃教人求為一文化人、理想人。”理想許多時候并不關乎直接的認識功用,似乎無助于提高技能,無益于當下,卻能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認知能力,決定和成就懷抱理想者的人生與人品。人唯其有了理想、信念、信仰和追求,他在生活中才會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他的生活才有意義有價值。這表明追求理想、信仰、信念,不僅是人的一種主觀心理,也是構成他的生命本體、生存需要和發展趨向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
文學理想是人類理想之一翼,文學理想體現了人類普遍的真善美的價值追求。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中說:“偉大的作品誕生于藝術家表達其道德理想的掙扎。事實上,他的理念、情感全部源于這些理想……因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心靈的努力,目的在于使人變得更為完美:一個美麗世界,以其和諧的感性和理性,以其高貴和自持來贏得我們的心。”此話將任何偉大的文學都涉及心靈、道德和人性,內含著理想主義的升華力量,帶人進入一個美好的世界,闡述得深刻透辟,入木三分。
文學理想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描繪生活但又以變化奇幻的方式保持與生活的聯系。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九章指出:“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就是說作家可以運用想象、幻想、夢想、虛構、夸張、挪移、變形等多種方式,進行理想化描寫,用“可然律”去探尋事物的各種可能,用“必然律”去揭示事物的總體趨勢與規律,這就能把文學的疆域無限擴大,把文學的色彩、功用和魅力無窮增添。波德萊爾說:“描述現成事物,詩人就會自貶身價,墮入教師之列;敘述可能的事物,詩人啊,你這才是忠于自己的職守。”任何人的思想總是越自由越活躍無拘無束最好,任何人的武器總是越多越精良越好,任何人的技能總是越特殊越高超越好,理想給文學和詩人作家提供了最遼闊的馳騁原野、最絢麗的多彩舞臺和最豐富的表現天地,我們該很好地認識理想,運用理想,讓它煥發出無窮無盡的光芒與能量。
設立理想維度,將其作為文學價值系統中居于最高位置和核心地位的構成,是因為理想乃是統帥一切元素,聚合所有奮斗目標的核心價值。劉勰說:“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理想是精神活動的主宰,是統轄所有思想的關鍵。它對于引導、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指導文學活動與文學創作具有不可估量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提倡加強文學的理想成分,強調將理想作為每個作家詩人的靈魂,是希望所有文學和作家都樹立追求大目標,追求大精神、大境界、大前途的思想,既要為當今價值失范的時代構建起明確的價值坐標,又要為改變和提升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風格、氣度、內涵,高度彰顯時代精神和文化個性做出積極有益的貢獻。
居于核心地位的理想具有像種子能夠生長出大樹的那樣含蓄的偉力,具有起始性、統領性、導向性和普適性等價值特性。起始性是說任何一個希望、念頭、愿望和目標,都有一個起始的開端,一旦氣候合適,其種子樹苗萌芽,便能蓬蓬勃勃不可遏制地生長起來。統領性是說理想一旦萌生,它便能凝聚心力,聚合思維,成為一種占據重要地位的思想,主宰或支配人的言行,驅使人們去努力實現它。導向性是說凡屬理想,皆有明確具體的指向、規定和目的目標,它們形成一種合力,能引導人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聚,以榜樣楷模的方式,誘使更多的人參與、趨赴和追逐。普適性則表示理想皆是具有普遍價值意義的東西,能推廣復制,可共振分享,替人們帶來更大的利益。由于具有以上特性,所以王爾德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 海德格爾說:文學存在一種神性,它能幫助人獲得這種神性,讓他們詩意地居住在大地上。郭嚴隸在其長篇小說《瑣沙》中也說:“如果不能抵達神境,人類是沒有幸福可言的。”他們所說的“烏托邦”、“神性”、“神境”其實都不過是一種理想之境,是人類追求的桃花源、理想國。
1.理想像一束光,能照亮黑暗角落和前進的路程。
英國著名詩人亞歷山大·波普曾寫過一首贊美牛頓的詩:“自然與自然規律在黑暗中隱蔽著,上帝說,讓牛頓去搞吧!于是一切都光明了。”理想就是這束照亮一切的光,它能刺破陰霾,掃蕩黑暗,讓事物和規律顯形,幫助人們走上陽光大道。
蒙古族作家海日寒在其新浪博客評小說《凈土》里寫道:“歷史觀的失范、價值觀的迷惘是我們這個時代寫作者最深的痛和最不忍的愛。我們的寫作是沒有方向的,沒有終極意義的,一切都是轉瞬即逝,一切都是飄渺云煙,一切終為幻影。”他的這種感受與疑惑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另一位詩人也寫道:“在這個泥濘的時代/我不可能獨善其身。”在當前物質增長與精神惡化同步,私欲膨脹與急功近利盛行之際,我們該怎么辦,文學該怎么辦呢?只有靠亮起理想之燈,樹立價值之旗,去重樹希望,重建信心信念,才能走出泥濘,擺脫時代痼疾。因為倘若不能擺脫這種思想危機,缺乏理想信念,那就既識不透過去,也看不清未來,看什么都容易短視消沉。
強調理想不是為了給作品添上一些亮麗的色彩、光明的內容,理想是建立在對時代發展趨勢和社會關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礎之上的。時代與社會從來都是成績與問題交集、進步與倒退并存、生機與危機糾纏的復雜存在。何去何從,如何認識,怎樣抉擇,就考驗人們的心性、良知和智慧了。明智的態度是“在這個泥濘的時代/我一定要獨善其身”,當 “四面八方堆積著/同樣的虛無和絕望,/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奧登《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因為理想在,希望信念就在;理想丟失,希望信念就會蕩然無存。作家需要從自我的“黑暗心靈”中走出來,老去追索自己心靈的幽隱無濟于事,且容易走向悲觀失望。要用理想之光照亮自我和更廣大的外部世界,擺脫局限,脫出個人狹小的籠子,到外部世界去求取一個更重大的存在,這是一條大路。我們必須用文藝創作表達美的理想,用自己的寫作否定物的宰制與人的盲從。用美和藝術為人類建立穩固的審美標準,培育人類的思想精神。用文藝作品中那些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芒的人物形象傳遞正價值、正能量,直接參與時代和社會的精神文化建設。
2.理想是一種聚合向上之力,推動人類和文學前行。
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精神現象和價值理念,理想描繪藍圖,設計愿景,培植信念,涵養道義,激勵斗志,催生人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去實現和完成它。
理想是內在于心的東西,它首先是通過確立一個明確奮斗目標而將所有心思氣力聚合成一。誰都知道朝三暮四、六神無主、意亂情迷是種最糟糕的狀態,它會讓人斗志渙散,心思分裂,什么也做不成干不了。理想一旦形成,它便能喚醒人心,匯聚潛力,將所有的心思精力擰成一股繩,為一個目標全力以赴奮勇工作。其次,理想與精神、信仰、信念聯系在一起,形成一股勢不可擋導人向上的強力,思想可引燃思想,精神可激蕩精神,精神會轉化為一種強勁的物質力量,促使人們投入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追逐之中。
印度詩人泰戈爾說:“一個藝術家應宣布他的信仰:我相信有籠罩并滲透大地的理想,一個天堂的理想,它不是幻想的結果,而是萬物寓于其中并在其中運動的終極真實。” 他理解的理想,籠罩天宇,滲透大地,寓于萬物,比一般人理解認識的廣大深厚得多。當作家天才的思想噴薄而出,如滔滔江河奔涌不息,卷起震撼人心的美麗浪花,他的目光已經超越塵世,直抵宇宙萬物的核心和根本。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則說:文學最大的作用就是“通過喚醒人們對習慣和麻木性的注意,引導人看向美麗的新事物”。發現和揭示鮮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為知道而其實不甚了了的人世的真相,通過對現存事物的否定,讓文學成為生活最清醒的守護力量。中國女作家邵麗說:“我更傾向于在苦難里發現美好,在荊棘里發現花朵,在陰霾里學會看到陽光。文學的神圣在于,它始終使我們的精神掙脫沉重的肉體,以獨立自由的姿態,存活在另一個可以抵達永恒的世界里。”這些就是他們對理想的態度。雖各有側重不同,但于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肯定理想的存在及其神圣永恒價值,是比較相通一致的。
詩人李瑛寫到:“我不懼怕衰老/因為它們不會衰老/我不懼怕死亡/因為它們會替我活著//對我來說,當下/最急迫的是/要消滅一些詞/比如恐怖、屠殺、殘忍/要強化一些詞/比如和平、憐憫、花朵/要創造一些更深刻有力的新詞/比如關于愛、美、自由和藝術”。這就是一個高齡老作家對自己一生熱愛文學,追求理想而寫出的文字、語詞和詩篇的一種自白,也是他畢生的創作理想,這當中有自豪自慰,有堅定的信仰,更有對當下和未來熱切的矚望,令人肅然起敬。
理想以一種積極入世的、建設性的態度介入生活,介入文學。即便是揭露批判生活的陰暗面,也能讓讀者感到文字背后有積極、溫暖的力量。即便是寫到紙醉金迷的奢靡腐敗、貪嗔癡迷的物欲橫流,也能讓人感到一種鄙夷不屑、冷峻批判的態度,從而生出對美好和光明的渴望,那都是由于作家內心存有正大的理想。因此,只要是寫出了希望,寫出了人性的美好和期待,寫出了前途的光明與幸福,其作品便會是有力量的文學,并以激勵人心的“力量”鼓舞人,幫助人。這種積極性質的理想主義,是在苦難中尋求希望、在困境中追求高尚,它能撫平心底的創痛,鼓勵向上的目光和奮進的腳步,是一個時代精神生活健康和有力量的標志,是最值得倡導與弘揚的力量。
3.理想教人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藝術境界。
世間任何一個人都應當弄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么,怎樣生活,如何度過一生,讓生命放射光芒。理想就是幫助人思考、設計和實現這一目的的法寶。它對人提出超過現狀的更高要求,幫助人實現自我,取得成功。目標高度是非常重要的,人追求的目標越高,他必須付出的努力就越大,他的收獲才可能越多,人生也才會越有價值。
理想可以與崇高、道德、精神和信仰聯系在一起,也可以與金錢、財富、權勢、貪欲和性聯系在一起。前者導人進入更高的境界,牽引著歷史與社會上升;后者則可能將人拖入泥潭,導向毀滅。因此對理想的目標、內涵和去向不能不審查探究,以決定褒貶棄取。
一位詩人這樣闡述自己的理想:“我想和陽光同居/……我想把自己最后一口氣出得金光閃閃/……我還想做陽光最后的情人/朝朝暮暮/一輩子談笑風生”因為他的一生有太多黑暗的死結,生活在陰暗發霉的地牢間,大半生都沒能出人頭地。理想為每個追求者提供崇高的生活目標、精神方向,為人們提供靈魂的棲息地,為現實中迷失的心靈提供通往天堂的路徑,為從事創作的人提供心靈的圣殿。偉大美好的理想總是與偉大美好的事物緊緊相連的,偉大美好的作品都源于某種巨大而持久的熱情。因此,把世間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未來展示給人們,便能樹立人們對生活對未來美好的堅定信念,激發人們對前途光明的憧憬。詩人李瑛在《關于生命》一詩中表示:“要像鷹,像鷹/一生從不懼亂云,風暴,雷雨/……把夢交給星星/把渴望交給虹霓/把歌聲交給風/把影子投向大地/將終生靈肉埋進白云里/讓全身倔強的羽毛/滾燙的血和/一顆小小的心臟,化作/犀利的閃電/熊熊的烈火/驚天的霹靂”。他用擬人化的雄鷹,表述“即使翅膀已傷痕累累/也要高飛九霄……再一次為人間撩起晨曦”的博大心愿,用最深的愛和最高的美歌頌奮斗、尋覓、發現和永不屈服的理想,實現對生命的衷心禮贊。
理想助人仰視生命的高度,讓人向往生命的詩性或神性,自然也包括藝術的高度和意境,而神性是人性的最高表現。如中國偉大的詩人屈原,他在《離騷》和《天問》里以叩天問地的浩渺想象和“哀民生多艱”的憂患意識,以及對真理“九死不悔”不惜一切的追求,形成了一個民族最高貴的品質和風骨,既極大地拓展和提升了自己的生命價值,也為中國人奠定了最基本的情感結構,為中華民族提供了永恒不朽的精神標高,為中國文學樹立了最經典的詩篇。當代作家史鐵生則以自己愛人超己的道德情懷,堅守著心靈的高貴和生命的尊嚴,秉持著文學的崇高信念和理想,扶輪問路,向死而生,彰顯了文學和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在其病逝后,無數作家詩人齊聚深切緬懷他。張守仁先生發言說:史鐵生是我們身邊善良的楷模、最美的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榮耀。“它理應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像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具有感召和示范的意義。鐵生的精神啟示我們,對他這樣的人來說,就是死亡也是美麗的,會像燈塔那樣燭照人間。”
美國藝術史家赫舍爾在其著作《人是誰》中說:“在人的存在中,至關重要的是某些隱蔽的,被壓抑的、被忽視,或者被歪曲的東西。我們不應當不去探索人怎樣從心靈深處把自己同他的行為聯系起來。”作家就應該用理想之燈去照亮那些隱蔽的地方,被忽略的東西,從中發現它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遲子建就說自己“仍在用我的筆,向著人性深處開掘,因為我相信文學之光埋藏在那里。”這是她的創作理想。韓少功則說:“把文學當人學,力求對人性‘黑箱’有新的揭示,刷新人類自我感知的紀錄。”這是他的理想,另一種創作理想。陳世旭表示:文學是他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自己快樂和幸福的源泉、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他對文學感激涕零。曾在其一個自選集的扉頁上寫“我寫作著,我生活著,這就夠了……一個別無選擇的寫作者惟一可靠的便是把這種對文學的初戀的感覺,保持到生命的終點。”以初戀般的熱愛獻身文學,獻身理想,是很多作家對待文學的虔誠態度。
理想謀現世利益與幸福,也追求人類的長遠發展和終極關懷。金牌電視劇編劇高滿堂用5年時間專心做一件事,為8億中國農民立一部正傳。為實現這一神圣堅定的文化理想,他走訪了六個省份,采訪了上至市長、副省長一直到人民公社社長到無數基層農民200多人,當60集電視連續劇《老農民》與觀眾見面時,他說:“一句話,我竭盡全力,我對得起8億農民!”他秉現實主義之筆,把共和國60年農民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的波折、迂回、疼痛、沉重,把歷史的光亮、人民的光彩,一切的一切,都濃縮在了黃河岸邊的“麥香村”。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會引起轟動,獲得觀眾的廣泛好評,在人們的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記,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于這樣的作家我們感恩于他。
表達人類對理想的渴望,描述人們對審美理想、價值理想的追求歷程,賦予人們光明、希望和信心,文學就這樣用理想豐富心靈哺育心靈,從而也就提升心靈擴大心靈。作家是生命的探索者,同時也應是理想主義者,更是偉大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他們對人類的現狀和前途負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如何讓一切創造活力迸發,讓每一個夢想找到它的不竭動力,如何不斷提升價值寫作的自覺水平,讓夢想不是寫在紙上,而是變成行動的指南?如何闡述人為什么活著,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如何堅定信念,放飛夢想,找尋屬于這個時代的理想與榜樣,凝聚人類共通的最美好、最偉大的理想和信仰?如何讓文學積極參與文化建設,融入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進程,借助文學特有的情感驅動力和藝術感染力把美好的夢想置入廣大人民的心田,讓生活更美好,讓文學也更美好?如何超越文學創作,對人類命運走向發出哲學意義的終極追問?這些統統是文學理想應當解答并做出貢獻的方面。
今日之中國,時代巨變,社會轉型,人性復蘇,文化復興,正是需要出文化巨人、文藝巨作的時代。寫出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情有愛有陽光的時代史詩,記錄民族靈魂追索的曲折道路,展現民眾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熔鑄激昂壯闊的時代交響樂,正是可以大展身手建功立業的時刻。巴金說過:“一個作家、一枝筆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進海洋就有無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團結起來,億萬枝筆集中在一起,就能夠為后代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未來。這才是我們作家的責任。這是理想,也是目標。”( 巴金箴言錄《生命在于付出》)這宏大的浪漫主義情懷和高尚的理想主義精神,難道不令我們心熱血燙,躍躍欲飛?
要想寫出真正能震撼人心,獲得廣泛好評的作品是越來越難。但只要樹立遠大抱負,打開一條能洞察時代基本狀況的思想通道,尋找一條能溝通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精神思路,滿腔熱忱地關懷民生疾苦,關懷人類的生存狀況、未來發展和前途命運,抵御各種名利誘惑,文學依然能走出邊緣化困境,為人們提供希望、激情、理想和信念。
理想是心意、愿望和未來遠景的混合物。理想為人們提供“道路感”、“方向感”和向上目標。美好前景的召喚,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實現理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投入努力,預測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創造未來。歌德的名言說:“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飛升。”我要說:“永恒之價值,永恒之理想,引導我們飛升。”
【注釋】
[1]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7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出版。
[2] 安德列·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反思》第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3] 大頭鴨鴨:《一個后湖農場的姑娘》,轉引自2014年6月13日《中國作家網》,劉波文。
[4] 轉引自李云雷:《在荊棘里發現花朵》,見2014年3月12日《文藝報》。
[5] 李瑛:《詩二首》,見2013年1月30日《人民日報》。
[6] 楊見:《和陽光同居》,摘自《三只雁飛過》,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7] 李瑛:《生命禮贊》,見2014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
[8] 張守仁:《讓史鐵生這顆星辰永遠照耀我們》,見2012年6月14日《文學報》。
[9] 遲子建:《埋藏在人性深處的文學之光》,見2013年3月25日《人民日報》。
[10] 韓少功:《好小說都是“放血”之作》,見2013年3月29日《人民日報》。
[11] 陳世旭:《初戀的感覺》,見2015年9月11日《文藝報》。
[12] 任姍姍:《在生活里掘一口深井》,見2015年1月1日《人民日報》。
(注: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4年度西部項目〔14XZW04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責任編輯:楊 林

楊艷鴻 工筆畫 曇花一現為君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