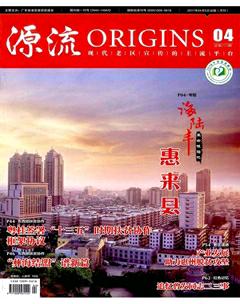追憶曾發同志二三事
黃柏軍



2月20日,星期一,早上十點,我的手機突然響起急促的鈴聲。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抗戰老戰士、原江門市市長曾發同志兒媳婦打來電話告訴我:曾發同志當天早上六時在五邑中醫院不幸病逝,享年94歲。突來的噩耗如同五雷轟頂。我的手握著手機,頭腦卻一片空白。曾老走得太倉促、太突然了。他還有很多故事沒有說,還有很多文章沒有寫,一部香港抗戰歷史的“活字典”就這樣走了,多么令人痛心!
我與曾老是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最初認識曾老,是2009年,他回來江門市參加東江縱隊抗日烈士陳冠時的追思大會。那次他在大會上發言,對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戰歷程抗戰故事如數家珍滔滔不絕,臺下很多抗戰老戰士一邊聽,一邊贊揚他是寫得講得的香港抗戰歷史“活字典”。大家對曾老的贊許,引起我對曾老親身經歷那些抗戰故事的濃厚興趣。等他從臺上下來,我馬上約他做香港抗戰時期見聞口述歷史采訪,他一口應允并約我去他深圳寓所詳談。就是那次深圳的采訪,我深入聆聽了曾老親身經歷的香港抗戰故事。
曾發是香港新界沙頭角梅子林村原居民。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日寇占領香港,正在知用中學讀初中的曾發,目睹山河破碎倭寇兇殘,毅然投筆從戎。他與父親一道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那年是1942年,他才18歲。抗戰中,他父親曾集芬因給游擊隊傳遞情報被日寇抓捕,死于日寇酷刑之下,曾發擦干眼淚,義無反顧走上抗戰征程。游擊戰堅持了整整三年零八個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告投降,香港重見光明。曾發歡欣鼓舞,他在心底向父親默哀:“爸爸,日寇投降了,我們終于勝利了,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那次深圳之行采訪曾老之后,我后來寫成《抗日老兵曾發和他的回憶錄》一文。文章發表后,反響很大,江門、新會一些老朋友看到文章后專程打電話給曾老表示祝賀,曾老也來電來信向我致謝。這幾年,我作為他的忘年交(我與他年齡相差50年),和他交往密切:他出版《中外共知的東江縱隊》、《搜腦袋》、《英烈千秋》、《營救克爾中尉》等四本著作,邀請我和黃華龍同志當責任編輯和校對;他每每寫好一些回憶錄和講話稿,他一定復印一份郵寄給我們,請我們找差錯、提意見。
曾老是香港人,關心香港事。他晚年做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拿出自己的離休金自費印刷自己的回憶錄,然后郵寄給香港各中小學,送給香港青少年閱讀和學習。他認為,香港年青一代首先要了解香港抗戰史才知道愛國團結的重要。他在《給香港青少年的一封公開信》中有這樣的自述和心聲:“有人笑我傻。我為什么這么做?因為我是香港原居民,我生于斯長于斯,我熱愛香港,我關注香港,我呵護香港,我要盡我最后一點余熱和微薄的力量服務香港。此心耿耿,可昭日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愛我香港,如此而已,豈有他哉?”老兵壯語擲地有聲。人過九旬,他時時刻刻想的不是安享晚年,而是香港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問題,字字句句閃爍和印證著老人家難能可貴的家國情懷啊!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有幾件事情令曾老頗感安慰:他和老伴李靈同志雙雙獲得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他不顧年紀老邁,赴香港參加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迎春茶話會,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深受好評;他一直牽掛和關注的《歷史是人民寫的》一書終于出版,在病逝前一直細心瀏覽這本書。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時間在新會、江門工作過,這里是他的第二故鄉。如今人生最后旅程定格在江門,在美麗僑鄉畫上句號,安眠在僑鄉,相信曾老也可以走得無悔無憾了。
說是無憾也有憾。作為后生晚輩,我再也不能聆聽這個可敬可愛的抗戰老兵的淳淳教導了。去年12月11日,距離他離世前40天,我去探望他,他在我的采訪本上親筆為我題詞留念:“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斯人已逝,風范長存;警句諍言,伴我前行。
五邑僑鄉山水作證,這個把青春熱血奉獻給僑鄉發展的老市長,他的名字將永久銘刻在僑鄉人民心中,與僑鄉人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