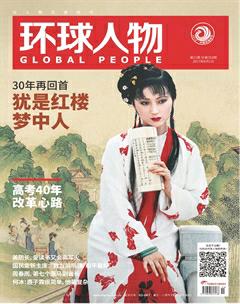高考40年改革心路
許陳靜+姜琨+鄭心儀

身為記者,有機會認識一種人,曾主導過我們命運的人。楊學為就是這樣的人。40年前的6月,40歲的他走進教育部高校招生會,和鄧小平走進了同一場歷史轉折中。恢復高考的文件經他之手起草,最終經鄧小平之手一錘定音,在1977年那個特殊年份里,成為冬天的第一聲春雷。
從那至今,又一個40年,楊學為的人生再沒離開過高考,國家教委招生處處長、國家教委考試中心主任、教育部(1998年改名)督學……與之相應的,是40年來1.08億人闖過了高考的大門。
人們會忍不住想象,那些主導過我們命運的面孔是什么模樣?京城一隅,門開處,是一位眉目慈祥、言談理性、思路清晰的老人。
“恢復高考就像在中國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彈”
我們的談話就從1977年冬天的故事開始。“楊老師,我的母親就在走進考場的570萬知識青年當中。比起考場里那些被‘文革耽誤了11年的老知青,她是幸運的,1975年高中畢業,沒有下鄉,留在母校當了代課老師,這讓她有了立即報考的勇氣。直到今天,她還記得那年的作文題是《心里有話向黨說》。”
這是湖南省的作文題。那一年的考題,各省都不一樣。這話,得從頭說起。
都知道“文革”里高考停了11年,但很少有人知道,中間有過兩次恢復的努力。1972年和1975年,我兩次被借調到教育部,籌備高校招生會,但都被“四人幫”破壞了,我又回到東北師范大學當教員,還不斷被“下放鍛煉”。1977年4月的一天,學校又接到教育部的電話,還是借我去高校招生會。這都是第三次了。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將參與一件改變千萬人命運的大事。
6月29日,招生會在山西太原晉祠賓館召開。從太原去賓館的路上,經過一家化肥廠,周圍污染很嚴重,天是黃色的,路邊的樹葉也已枯黃,空氣里有刺鼻的臭味。會上,“文革”的臭味也沒有消散——由于“兩個凡是”的束縛,教育部提出的《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草稿)》,只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作了個別修改。這個意見稿,自然引起大家的激烈反對。
開完會,秘書組讓我起草領導的總結講話稿。我就根據會上多數人的意見和自己的理解,通宵達旦寫了個草稿,把“四人幫”批了一通。結果,總結會不得不推遲到下午,領導親自改講話稿,把“調子”定得很高,通篇都是“高舉”“到底”之類的詞,而招生工作的重大問題一點都沒涉及。
最終,教育部送給國務院的報告還是一個舊東西——考生一般是高中畢業生,初中畢業也可以;堅持推薦制度,只提“文化考查”;只在少數學校部分專業試招2%—5%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繼續實行“四人幫”的“三來三去”,即學生從公社來回公社去,從工廠來回工廠去,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當時哪會想到還有第二次會議,說得直白點,鄧小平沒恢復工作前,誰知道會怎樣。但在招生會結束前夕,傳來了爆炸性消息:鄧小平復出了,而且自告奮勇抓科教!8月,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參會的教師和科研人員發言非常踴躍、大膽。8月6日下午,武漢大學的査全性老師石破天驚地提出:馬上恢復高考,已經耽誤太久,不能再耽誤了。這個話題一挑明,大家都很激動。鄧小平見狀,大受觸動,唯一擔心的是招生會已經開過了,今年還來不來得及,就問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劉西堯回答說,假如推遲開學就來得及。鄧小平當即拍板:“既然今年還有時間,那就堅決改嘛!把原來寫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重寫……今年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學生要符合要求。”座談會第一次響起熱烈的掌聲。
于是,教育部緊急通知,8月13日召開第二次招生會。一年之內,兩開招生會,只此一次。第二次招生會起初進展還是不大。教育部主要領導不敢表態。會議就在激烈的爭論中拖延下去。籌備組先住在北京飯店,后來遷到前門飯店,開了幾天又搬到友誼賓館主樓,結果時間太長又遷到配樓。會剛開時還是盛夏,開了45天,好多人不得不讓家里寄送秋衣過來。
9月中旬,會議簡報、招生意見討論稿陸續送到了鄧小平手里。鄧小平看到依然苛刻的政審條件,極為生氣,先嚴厲批評了劉西堯,接著連說3個“繁瑣”,大筆一揮全部勾掉,“政治歷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后來,我們起草小組就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的這段話。鄧小平的親自掌舵,促使第二次招生會達成了一致意見:廢除推薦,恢復考試,招應屆高中畢業生,按分數擇優錄取。
今天回想,還是要說:鄧小平真正了不起!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前,在這一切撥亂反正尚未開始之前,當機立斷恢復高考,這樣的魄力,除鄧小平外,別無他人。媒體常說,此舉改變了億萬人的命運。我要說:何止!恢復高考改變的何止是個人命運,更是國家命運。1966年6月18日,北京中學生發表了兩封公開信,要求廢止高考,這先于《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77年,恢復高考的決定又先于撥亂反正。高考的廢與立,是國家亂與治的先聲。前幾天,“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行,我就在電視機前數有多少個同聲傳譯耳機,這背后就是多少個我們培養的高級翻譯。如果沒有恢復高考,就不會有這么多現代化人才,就辦不好這樣的國際盛會,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當然,那時候想不到這么遠,因為時間來不及了。11年沒組織過考試,有資格參加考試的人又分散到農村去了,怎么通知他們?怎么出題?出什么水平的題?如果全國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出一套考題,怎么運到各地?怎么保證同時開考?沒辦法,只能各省命題,還得先各選一個縣試點。很巧,全國第一個試點縣,就是鄧小平領導起義的廣西百色。我們趕過去,按照初中水平出了一套題,手刻蠟印,一考,98.64%不及格,98.64%!就是這樣,當地的老百姓還是喜不自禁地跟我們說:“恢復高考就像在中國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彈。”
所以1977年的高考,各省的時間不一致,考題不一樣,570萬人里,父子同考、夫妻同考的比比皆是。考得最好的是66屆、67屆高中畢業生,他們基本在“文革”前完成了中學學業。
40年并不遙遠,就是我們的父親母親的故事。那一年,27萬人被錄取,錄取率僅為4.7%。自那27萬人起,奮發上進的個體命運,匯聚成滔滔向前的國家潮流。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
“考完高考,臉都瘦了一圈”
楊學為在考試中心主任的職位上干了13年,直到2000年,數次提出退休的他,確因身體狀況不佳,才獲準離任。當時高考正由上世紀90年代的“3+2”切換到新世紀的“3+X”。這是“80后”“90后”熟悉的兩個詞,貫穿了青春,左右了悲喜。恢復高考只是一瞬間的歷史拐點,而高考本身是一場40年的改革連續劇,從各省命題到全國統考,從英語只按10%計入總分到成為三大主科之一,從文理分科到“3+X”……
1977年的招生會爭論的是要不要恢復,至于要不要考試根本沒討論,1978年的招生會才補上,而且引發得很偶然。會上,華東組幾個人議論:以前說照顧工農,現在是考試復辟了?工農也不照顧了?這些話被記錄到簡報里。另一個對話發生在食堂,一名記者和一名副司長吃飯時也這么議論,被人聽見了反映到會上。兩個對話一匯總,會議就炸了鍋:到底要不要考試?怎么考試?
爭論的結果,確定要考,而且要全國統考。
1978年還有一個細微但重要的變化:考生能知道分數了。今天不能想象吧?但以前,分數是絕密的,不讓你知道。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成績好的有可能被“走后門”擠掉。鄧小平知道后,1978年3月8日明確給了一個指示: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績,“這是堵后門的最好辦法”。
進入上世紀80年代,高考帶來一個突出的矛盾——片面追求升學率。有多嚴重呢?高二的數學課本中,有的內容不是高考必考,老師就不講了。學生一天學習十五六個小時,文體活動都停止了,午飯也不回家吃,只啃干糧,“考完高考,臉都瘦了一圈”。老師也疲于奔命,一位54歲的中學物理老師在深夜工作時昏倒,再沒醒過來,活活累死了。
這一下子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們感覺到壓力巨大,采取了許多措施,把“德智體全面考核,擇優錄取”作為原則,想方設法去抬高“德”“體”的作用,降低“智”,也就是分數的作用。
到了1984年,我和同事討論:高考混同了選拔考試和水平考試。其實,高中首先應該是水平教育,過了這個水平再談選拔。現在中學都按高考的難度來教學,學生的知識結構殘缺不全,是否該有個專門的水平考試?討論的結果就是從1990年開始實行高中畢業會考制度,算是補上了一塊重要的缺漏。現在已經發展為高中綜合素質評價。
此后,我們又在分類與科目設置上,做了一些探索,1992年開始了“3+2”,1999年開始了“3+X”。高考形式一步步完善,就好像孩子一點點長大,終于有了比較成熟的面貌。
說到這里,就要講講考試標準化的問題。恢復高考后,題型延續了科舉以來的帖經(填空)、墨義(簡答)、策論(論述)等,以主觀題為主;評卷也有主觀因素,評卷老師的喜好對分數影響很大。有一天,北京師范大學心理系學生謝小慶跑來找我,說注意到高考作文評分誤差很大,想立個課題,問我要29個省的作文試卷做研究。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就一口答應了。那學生還真研究出了東西:判卷主觀喜好對同一篇作文的影響,高低分相差達29分。后來這課題得了北師大和北京市的特等獎,也引起了教育部領導的重視。從此有了規定:每份試卷至少兩人同評,分差大則送閱卷組長處評,再有分歧則小組集體討論評分。
評分標準化了,考題也得標準化。中國沒經驗,就去美國學。1982年我們到了美國,一看卷子上的選擇題,沒見過,真新奇!更新奇的是有種機器,選擇題的答案從這邊進去,從另一邊出來時就判完了,一小時能處理6000份試卷。我們就像小孩子趴在收音機前看里面有沒有人一樣,真想趴在機器上,看里面到底有什么。1985年,我們啟動標準化命題試點,從此選擇題成為重要題型;命題質量也穩定了,不再一年難一年易。
我們在采訪中聽到一件趣事。高考率先引進標準化命題后,選擇題很快就“占領”了各類考試。1988年,醫療衛生系統組織了一次職稱考試,首次采用選擇題。結果,某地恢復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醫生們,沒見過選擇題,考了個大眼瞪小眼:“現在高考考這個?1977年要是考這個,我們就考不上了。時代進步太快啊!”
“楊主任,你把階級感情都收沒了”
認識幾位早年參加過高考命題的老師。他們戲稱命題是“入闈”,而“里面的日子一點也不輕松,壓力山大,每天都要想出新的題目,拿到會上討論。沒有哪個題能贏得一片叫好,從來都是唇槍舌劍,從各個角度批評你的題不嚴謹、有漏洞,甚至直接斃掉,重新出。如此周而復始,最后命中的題,都是千錘百煉、非常科學的考題。”
這個命題制度,是我建立起來的。1987年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年份,因為考試中心成立了。
中國是考試的故鄉,我們去美國學習時,他們就說,考試這事還是從你們老祖宗那學來的呢!中國幾千年組織考試的竅門就是:一個專門的機構,一批有經驗的人。但廢除科舉后沒有了。恢復高考后,命題歸教育部計劃司招生處負責。1982年,處長的孩子高考,需要避嫌,我就被指派去負責命題工作。命題老師中午把試卷送到保密室,就去吃飯了,誰來看著?只能是我。我待在保密室里,突然有些害怕:如果現在來個小偷,把玻璃一砸,我是去追小偷呢,還是留下來看卷子呢?如果追小偷,有人趁機把卷子偷走了怎么辦?要是留下來看卷子,小偷跑了去哪找?真是一團亂麻。
后來我當了處長,情況也沒好多少。我桌子底下放了幾個大紙盒,裝著高中教材,一到命題時就拖出來給命題老師用。有一年我拖出來一看,呦,過期了,趕緊去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新教材,再火急火燎地組織命題。所以,幾乎每年命題,都沒有充分的時間來打磨試卷,考卷水平很不穩定,考卷上還常出現錯誤。
創辦考試中心成了刻不容緩的大事。1987年,考試中心成立,17個人,4個處室,一個命題處,一個考務處,一個科研處,還有一個辦公室,就在北京十一學校的宿舍樓里開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