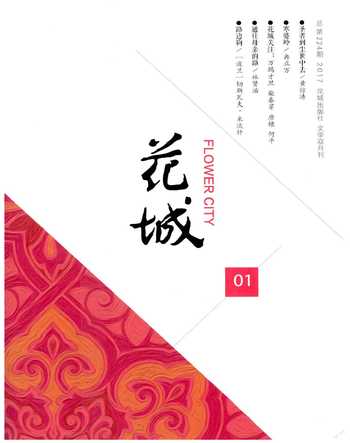這次我們不只談論電影,也談談他們的小說
何平
是的,萬瑪才旦導演過《靜靜的嘛呢石》《老狗》《尋找智美更登》《塔洛》等一系列電影,柴春芽和唐棣也各自導演過《我故鄉死亡的四種方式》和《滿洲里來的人》等等,他們都確實地有著電影導演的身份,也正從事著電影的事業,但僅僅因為他們是導演,都寫小說并不能構成我們把他們放在一起談論的充分理由,至少是表面皮相的理由。當然,我們可以投機取巧地用“跨界”“越界”來指認他們。不過,“跨界”“越界”這些詞在今天因為被濫用,或者經常被那些撈過界的人用來張目,已經不是每個人都樂于接受的了,就像一個木匠在木匠界做得三腳貓,偶爾他學會了砌院墻蓋雞窩的手藝,于是就儼然成了在木匠界最好的瓦匠,瓦匠界最好的木匠。你說,這種所謂的“跨界”“越界”是對一個誠實的手藝人的褒揚嗎?因此,在現時代,我們是能夠看到穿行于各行各業的旅行者,他們做到的也僅僅就是跨越了不同的邊界,成為各種時代歡場上的兩棲人或者多棲人而已。
所以,當面對萬瑪才旦、柴春芽和唐棣,我們是要電影的尺度衡量他們的電影,用小說的尺度來衡量他們的小說給當下的中國文學帶來了什么?回到他們的小說,回到他們各自的個人寫作史,都不是因為電影給他們榮光,轉而去“玩玩小說”。只是因為,比如萬瑪才旦的電影正逐步累積世界聲譽,追逐光環的大眾傳媒讓小說家的萬瑪才旦成為一種相對隱秘隱微的身份,而恰恰是,萬瑪才旦電影的異質性可能部分是源自他的“文學”。應該注意到,萬瑪才旦幾乎所有的電影都有一個自己獨立創作小說的“母本”,在他導演第一部電影《草原》之前,他就是一個成熟的短篇小說家。而與他這些電影并行不悖的是:他一邊以“個人風格”標記自己的電影,發展他簡潔干凈的電影敘事——這種標記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藏地”,而是他的電影作為卑微者心靈史詩的藝術方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作為中國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家方陣中的一員,已經有了屬于萬瑪才旦的辨識度。同樣,這樣的辨識度也不是因為民族身份和“極端”題材的異域風景。是的,哪怕我們還用民族身份來談論萬瑪才旦的電影和小說,他也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小說家的柴春芽,另一個比導演更著名的身份可能是曾經做過的攝影記者和大地上的旅行者。他對風景與人有異乎尋常的敏感,所以他的《我故鄉死亡的四種方式》這本書可以集成散文、劇本和影像的各種元素去挽留正在消逝的“故鄉”。而唐棣在成為“青年導演”之前其實已經是一個“秘密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在有限的范圍里流傳,像一個傳道者,“秘密”只是沒有被我們的主流文學期刊所接納而已。因此,如果要研究他們在電影和文學之間往返的旅行者身份,恐怕文學賦予電影的可能更多。
電影作為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幾乎是一門完全現代的藝術。因而,在諸種藝術門類中,新興藝術的電影也是商業化程度比較高的。但有意思的是,電影這門藝術的“技藝性”使得它又可能保留我們今天時代正面臨危機的手藝人精神。那些人類藝術史少數好的電影,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考究到肌理和細節的。如果從電影類型上,萬瑪才旦和唐棣的差異很大,但在敘事上的極致和挑剔上是共同的,萬瑪才旦是最大可能的做減法,而僅僅以《滿洲里來的人》來看,唐棣則不避繁復,繁復而秩序感。這也是他們小說的差異性。萬瑪才旦的小說是變化莫測的大千世界壓向一個個渺小的生命個體。宏大時代到每一個個人已然是神經末梢,一個時代的,或者也有一個民族的疼痛就在這些末梢的卑微無名者身上。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我理解柴春芽說的,“萬瑪才旦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遭受的疼痛,可能是我永遠無法體會的”。因此,讀萬瑪才旦的小說,我們以為我們可以解讀的部分可能是最膚淺的,而那些“無法體會”的也許正是萬瑪才旦小說需要我們愛惜的部分。在我們這個夸夸其談語言泛濫的時代,需要適度的沉默而無言,或者不能言,言而不盡,文學應該給我們的世界“留白”,留下冥思或者獨自憂傷的“余地”。唐棣是怎么發育成現在這樣的文學中的不可知論者,我們沒有仔細去研究。因為,對“巨大癥”的厭倦,我們的文學評價正在走向極端的反面——毫無價值立場地去強調去突出當下文學書寫中的失敗者、小鎮青年、灰色人群、邊緣人等等的瑣碎無聊。問題是當我們的文學在書寫這些人現實的百無聊賴,幾乎也只能貼著地面爬行。有一種危險的傾向:唐棣寫作的某些部分,也被放在這個譜系里來識別。而事實上,就像唐棣的小說題目,“西瓜長在天邊上”,唐棣小說的“無聊感”是有在天上飛和看的部分,就像他的電影不斷抖動的攝像機。唐棣的“無聊”和“虛無”是信仰意義上的,基于他的不可知論的世界觀。唐棣繼承了20個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精神遺產,至今他依然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文體實驗者。他的實驗性寫作目前公開的很少,如果我們假想的“80后作家”這個代際作家群確實存在,就像唐棣的電影被指認為“一種噪音”,他的這一部分實驗小說在他的同時代人中也會是“一種噪音”。經過90年代以來通俗文學網絡文學的洗禮,我們的寫作和閱讀已經變得越來越“雞湯”越來越“浮淺”。小說文體實驗的群眾基礎其實已經遠遠不如20世紀80年代。尚且不論唐棣的小說實驗能夠走多遠,能不能解決先鋒前輩沒有解決的形式止于“形式主義”的問題?至少我們的文學先要寬容某些“極端”的寫作。我在和年輕作家的交流中發現,類似唐棣這樣把文學作為“信仰”的不在少數。
說到“信仰”,這也是柴春芽最為可貴的氣質。“知行合一”,寫作是柴春芽的“修行”。在宗教世俗化的時代,柴春芽卻反其道而行之,追求著日常生活的神性尺度。或許柴春芽可以作為一個提問,在今天,寫作還能作為心靈史嗎?
2016年深秋于隨園西山
責任編輯 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