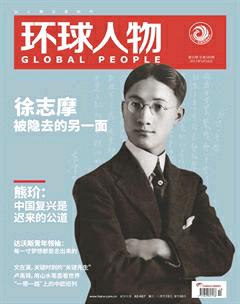把愛情故事寫成偵探小說
趙曉蘭
正如書名所昭示的,19世紀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戀情的終結》,講述了一個頗富悲劇性的愛情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莫里斯和薩拉是一對如膠似漆的婚外戀人。莫里斯在一次炮火襲擊中受傷,危在旦夕,薩拉偷偷向天主禱告:若莫里斯化險為夷,她就投身天主,為這段不倫之戀畫上句號。
莫里斯果真安然無恙,薩拉卻不辭而別。不明就里的莫里斯無法走出情傷。他腦洞大開,幻想著薩拉離開的各種理由,懷疑她另有新歡,在妒恨交加中煎熬地度過了兩年,甚至還聘請私人偵探對她暗中進行調查。直到有一天他看到薩拉的日記,才得知真相,悔恨交加。但此時薩拉卻在一次風寒中故去。
這聽起來老套又帶點狗血的故事,何以被威廉·福克納(美國作家,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認為是“那個時代最真實最感人的長篇小說”,又何以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作家,拉丁美洲魔幻現(xiàn)實主義文學代表人物)頂禮膜拜?原因就在于格林的作品剖析人心的深度與力度。他將最難表現(xiàn)的情感躍然紙上,讓讀者為之心驚。
佛經(jīng)說,困擾人的苦難主要有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而《戀情的終結》主要寫“愛別離”。
格林的文字像手術刀一樣,展現(xiàn)主人公內心的痛苦、猜疑和空虛,敏感地捕捉了那些一瞬即逝的情緒,刻畫出人性中的狹隘、自私與偏執(zhí),男女關系中的錯位,以及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宗教與人性的沖突。
格林沒有平鋪直敘地寫這個故事。他打破了線性敘事,以莫里斯第一人稱的口吻,在回憶的視角中,以散點交織的結構方式慢慢呈現(xiàn)沖突與真相。這種散亂多線條的結構又如同男主人公的心態(tài)——“我在一個奇怪的區(qū)域里迷失了方向:我沒有地圖”。在迷亂中,薩拉的日記又如同一股清冽的泉水。這樣的寫作令這個愛情故事讀起來如同偵探小說一般懸念迭起,讓讀者急切地想一探究竟。
格林的一生非常傳奇。他曾獲21次諾貝爾獎提名,但終未得獎,被稱為諾貝爾文學獎最大牌的陪跑者、最可惜的遺珠。他的人生顛沛流離、從未安定,大多時候都在羈旅中度過。他最擅長“窮游”,哪里最原始偏遠,他就往哪里跑,非洲腹地、南美、中東等戰(zhàn)亂之地都曾留下他的足跡。他還有個很獨特的嗜好——當間諜,曾因親戚介紹,在英國軍情六處工作,二戰(zhàn)期間被派往非洲的塞拉利昂潛伏。那些旅行中的所見所聞都成了他創(chuàng)作的素材,甚至間諜活動對他來說也與小說家的職業(yè)不無類似——同樣是采取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分析人的行為動機,窺探隱秘的人性。
格林一生最大的花邊新聞是與一位富有的人妻凱瑟琳長達16年的愛情糾葛。凱瑟琳是格林的忠實讀者。兩人的故事有點像《戀情的終結》中的情節(jié),因此也有人說這是格林最具自傳性質的一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