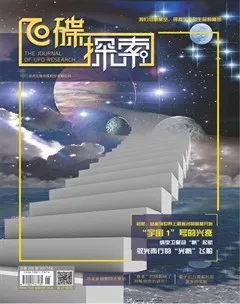“宇宙1”號的興衰
路易斯·弗里德曼
譯/ 晨飛
1980年,卡爾·薩根、布魯斯·默里和我一起成立了行星協會,旨在證實對行星探索的廣泛興趣并對其加以利用。行星探索是官方的一個重大項目,當時面臨著中斷的危險。要想證實大眾的興趣,就得成立一個會員組織,讓感興趣的人既能夠獲得行星探索方面的信息,也能夠有一種參與感。我們出了一份精美的雜志——《行星報告》,刊登其他星球的最新照片,以及參與行星探索任務的科學家撰寫的佳作。在前因特網時代,人們很難獲得有關行星探索任務的第一手信息和空間項目拍攝到的圖片,通常無處可找。

? ? “波浪”號火箭原用于從潛艇上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后經改裝用來攜帶和平目的的載荷送入太空。
當時,我們的業務顧問告訴我們,光靠會員交的會員費不大能搞一個組織,我們得靠相當的項目支撐,這樣既能保證很多人感興趣,也能吸引大量的捐贈。我們立刻做出回應,表示可以資助萌發未來重大項目的新穎實驗。我們的第一個成果是私人資助的搜尋地外文明(SETI)項目,這是在美國議會藐視NASA的項目并取消對其資助之后發生的事。在協會成立早期,我們做的另一件事是為發現太陽系外行星提供技術資助,并在10余年后發現了第一顆。我們也為一項先導性實驗提供資助,這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早期火星標本返回項目和火星遠距離低空氣球飛行新概念的內容。
早期的這些項目都是在地球上進行的。我記得我與卡爾·薩根的一次對話,當時他仔細地考慮有沒有可能開創我們自己的空間項目,把實驗放在飛船上,或者更進一步,用我們的項目促進空間探索的技術和發現極限。當時我們認為有這種可能,到20世紀90年代也的確成為可能。
薩根和默里也是太陽帆愛好者。卡爾·薩根給當時美國發行量最大的《行進》雜志撰寫了一篇關于太陽帆的非常熱門的文章。布魯斯帶頭支持研發,在噴氣推進實驗室開展了“哈雷”太陽帆的高端研究。我當然是一名愛好者,正如布魯斯所說的那樣,畢竟“是他寫的書”。可是,雖然我們都極其富于想象,但是作為項目畢竟還得落到實處,不能因為熱愛科技而做白日夢。我們未能找到足夠現實的機會展現我們的太陽帆。
1996年,卡爾·薩根英年早逝,很是不幸。1999年,俄羅斯同行向我們伸出了援手,十分誘人,無法拒絕。他們能夠提供免費的發射,而且還有用于再入飛行器的充氣結構捎帶的非常低成本的太陽帆研發。有了布魯斯的肯定,再加上行星協會董事會的支持,我們組織了自己的團隊,對他們的想法進行精細的審查和研究,拿出一個成本估算,希望協會成員能夠負擔得起,而且還能打動他們。因此,“宇宙1”號——世界上第一艘太陽帆飛船——誕生了。
這種“免費發射”是冷戰結束后意欲啟用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的一個結果,也許是為了開辟商業用途,把核彈卸掉,換上衛星,將其送入軌道。俄羅斯人向我們提供基于潛艇洲際彈道導彈系統的“波浪”號運載火箭,將太陽帆送入軌道。
我們大約400萬美元的預算對行星協會來說是多了些,因為之前最大的兩個項目——SETI項目和火星氣球——都沒超過100萬,但是按照NASA的標準來說卻少了點兒。這次的免費發射和俄美合作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兩位企業家——比爾和拉里·格羅斯——在帕薩迪納創立了一個創業孵化基地,名為創意實驗室。創意實驗室早期的冒險之一就是一家太空公司,名稱里有個驚嘆號——布拉斯托夫!(意為“發射升空”)。布拉斯托夫!為研究由俄羅斯發射、行星協會管理的繞地太陽帆項目的可行性提供了啟動資金。在俄羅斯經過認真的考察之后,我們深信該項目可行,可以操作。從俄羅斯
考察回來以后,我們都鼓足了勇氣,準備大干一場。布拉斯托夫!聘請了一位新的執行總裁,名叫彼得·迪亞芒蒂思,他覺得跟他們自己原先的登月飛行器相比,太陽帆的吸引力簡直太大了。他的看法也許正確:在他們努力研究自己更難更大的月球項目的同時,我們的合作是在向他們出售低成本的太陽帆項目,讓他們的空間計劃有機會迅速(三四年)取得成功。他滿載而歸。
另一位企業家喬·法爾馬格正在嘗試創建科學目的的因特網入口,對我們的太陽帆也非常感興趣。喬對天體物理學(包括親歷者描述外星人遭遇經歷)有著濃厚的興趣,打算支持關于太空探索問題的科學研究以及外星人的搜尋。

“波浪”號火箭負載“宇宙1,號部署測試儀進入俄羅斯潛艇
他向行星協會提供基金,支持創立SETI@home網站,讓用戶幫助分析射電天文學信號,尋找可能有外星生命的天空。之后喬與卡爾·薩根的遺孀安·德魯伊恩展開合作,她當時正在發展自己的宇宙工作室。安對太陽帆當然有著濃厚的興趣,非常支持行星協會。她和喬把太陽帆項目看作他們新伙伴關系有所突破的一個絕好機會,在此基礎上制作了一部宇宙工作室紀錄片。他們決心投入行星協會牽頭的太陽帆研究項目。
為了紀念安與她的新冒險,也為了向她和卡爾·薩根非凡的系列電視劇《宇宙》表示敬意,我們為自己的項目取名“宇宙1”號。俄羅斯人有他們的宇宙飛船系列,可以上溯到太空時代之初。他們很不喜歡我們的名稱,但是我們向他們指出,實際上沒有誰擁有“宇宙”這個名稱,并堅持使用這個代號。之所以用“1”,是因為我們想把它作為實現太陽帆飛行的第一艘飛船對待。
這意味著我們的飛行軌道得保證大氣的影響微不足道,也就是說,要到達820千米的高度。第一次太陽帆飛行的實現首先得保證將其送入這個高度的軌道,背負著俄羅斯將洲際彈道導彈轉變為商業運載火箭的渴望(這種渴望常被喻為冷戰后的“戰刀變犁頭”)以及俄羅斯航空航天業對再入飛行器充氣式結構的研制。
行星協會在俄羅斯有長期的合作伙伴——科學院太空研究中心和拉沃奇金聯盟。它們都是俄羅斯航空航天局下屬的公司,負責行星飛船等業務。拉沃奇金聯盟和太空研究中心執行了俄羅斯所有的行星項目,在開發金星- 哈雷彗星項目(VEGA)期間,我們的合作尤為密切。
拉沃奇金聯盟目前正在研發商業應用項目,其中包括能送入軌道并將舊衛星或其他軌道垃圾拖離軌道的充氣式再入飛行器。他們的充氣設計能夠用來制造充氣吊桿以展開太陽帆。
“宇宙1”號具有一種巧妙的設計:8個三角形的太陽帆,由長度1 5米左右的充氣吊桿展開并固定。飛船中心的帆頂端有馬達,每個帆板都可以傾斜(實際上共4對三角形帆板,4臺馬達各控制其中的2個)。這樣一來,整個帆可以卷曲、傾斜、偏轉,因此飛船本身可以朝任何一個方向跟蹤太陽。
這艘飛船的研制主要靠俄羅斯人,行星協會也派出專家對該項目實施監督,對系統設計提供意見和建議,對飛船無線電等次系統的要求提供幫助。吉姆·坎特雷爾、哈里斯·M.巴德·舒爾梅耶和我負責行星協會團隊,經常還有其他顧問人員參與。坎特雷爾自在猶他州立大學上學時就在行星協會工作,幫助研制火星氣球以及航空航天工業方面的軍用和民用項目。舒爾梅耶是NASA 優秀的項目經理,曾負責“旅行者”號和“伽利略”號項目,后來成為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副總監。
俄羅斯人許諾2年內完成該項目,我們當時聽到后覺得值得樂觀,結果卻花費了5年時間。研制的頭一年,俄羅斯人提議制作一個小點兒的模型,只有帆和展開系統,在他們用于測試再入飛行器的亞軌道免費試飛。我們趕緊去百思買集團(一家消費者電子產品店)購置了幾架飛船上安裝的攝影機,以便在亞軌道飛行的頂端拍攝帆板的展開。
該項目搭乘巴倫支海一艘潛艇上的“波浪”號火箭發射升空,飛行終點設計在俄羅斯的堪察加,在那里回收太空艙和錄像。不幸的是,火箭發生異常,什么也沒能收回。我卻獲得了一次獨特的體驗:乘坐俄羅斯海軍駛離摩爾曼斯克的軍艦進入巴倫支海,去觀察潛艇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跟隨我的是宇宙工作室的一個攝影小組,他們在為自己計劃中的紀錄片收集素材。我通過衛星電話從艦上給行星協會提供實時現場評論。

? ? “宇宙1”號由三大部分組成,儀器板、帆平臺和天線平臺。整個飛船放置于俄羅斯“波浪”號火箭有效載荷內。
在這次旅程中,我看到了公眾對人類未來宇宙飛行表現出的興趣。在試射的前一天,我們在摩爾曼斯克市走了一圈。在一條大街的一個報亭,我注意到有張報紙上刊登著一篇文章,說的就是我們將要發射的太陽帆。我買了一張,翻過一頁,高興地看到一張太陽帆飛行圖,我認為那是最好的一張圖片。我們一直沒能找到畫這張圖的藝術家,是他還是她,是從哪里來的靈感,都無從知曉。我很喜歡這張圖表現出的人類太空飛行的方式。
2001年7月,亞軌道試飛行結束后,我們花了將近1年的時間才搞清楚“波浪”號火箭的問題出在哪里。與此同時,我們恢復建造我們的飛船。
最終飛船建成,準備在2005年年初發射。在最后的測試、復查、安排全球地面站跟蹤和遙測接收以及對任務運作的組織之后,我們在行星協會辦公室設立了一個衛星控制臺,與拉沃奇金軍民共用衛星的內部半機密控制臺保持緊密聯系,共同操作。然后,我們把發射時間定于2005年6月21日。
為了此次發射,我留在莫斯科,和巴德·舒爾梅耶一起去拉沃奇金聯盟的項目控制中心。在那里,還有我的老朋友加同事、科學院太空研究中心的斯拉瓦·林金,他在促成這個項目中出力最多。我們一起觀察,目擊了俄羅斯軍方負責“波浪”號發射和雷達跟蹤至軌道的部門提供的通信信息。吉姆·坎特雷爾待在行星協會負責協會活動,與我們的成員和報界保持聯系。
2005年6月21日,“波浪”號火箭第一級發射失敗后82秒,“宇宙1”號墜入海中。我們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太陽帆宇宙飛船,可是它沒有機會告訴我們飛船會怎樣工作。我感到很沮喪。但是,行星協會所做的巨大努力得到了許多贊揚——不但有空間群體和全球報界的夸獎,還有給我們直接捐助的會員的贊許。有了會員的堅定支持,我們下定決心永不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