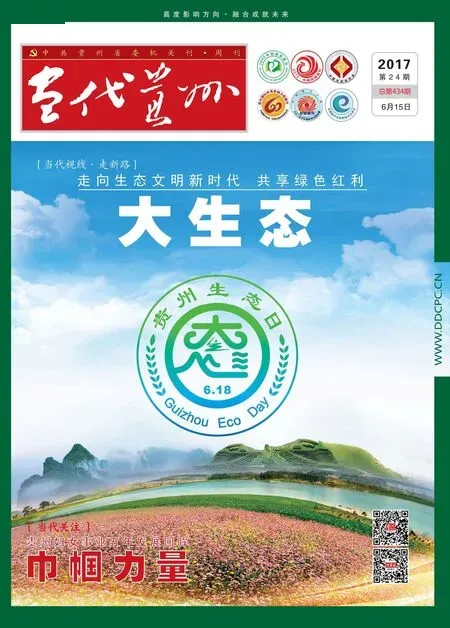政務微博還是政務微信?
政務微博還是政務微信?

朱春陽
媒介管理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媒介管理學學科帶頭人,復旦大學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長。曾入選上海市曙光學者、首屆中國最具影響力人文社科青年學者(100人)(2015年度),獲中國傳媒經濟學科發展杰出貢獻人物獎(2015年)等。
微博作為網絡輿情的第一落點,應該承擔起輿情引導主平臺的功能;政務微信平臺的交互功能相對較差,我們應該將平臺打造成線下政務大廳在網絡空間的延伸和放大,發展成“便民服務小秘書”。
2010年是中國微博元年,2011年被稱為是政府微博元年,很快,政務微博的數量就攀升至近30萬家。然而,2013年被稱為是政務微信元年,政務微信的數量也在2016年超過了10萬家。和既有的新媒體平臺的更迭一樣,我一開始認為,微信與微博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替代關系,很快,就應該是微信的天下了。但這個觀點在2015年發生了變化,微博與微信的關系,應該是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在很多調研中,我們發現,微博平臺的價值明顯被忽視了,而微信基于實名的社會關系網絡則讓輿情引導工作者變得焦慮不安,而且不得其門而入。究竟該如何認識“兩微”的價值呢?
從新媒體的使用上來看,微信的確居于主導地位。微信目前已經成為我們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網絡的承載平臺,使用者的高卷入度、高粘著性使得微信成為社交媒體毫無爭議的第一平臺。但從政務機構的視角來看,微信卻讓當下的輿情引導經驗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我們在調研中經常遇到一些領導給我們訴苦,說論壇時期和微博時期,網絡評論員還有廣闊的作為空間,而微信時期,網絡評論員好像一下就失去了作用。如何在微信平臺實現輿情引導?這一問題是近年來領導干部最為頭痛的事情。
在我看來,上述問題的根本是問錯了方向,不應該問我怎么進入微信空間引導輿情,而是微信空間能夠為政務機構提供什么樣的價值?而微博空間又能夠提供什么樣的價值?這就需要我們對微博和微信的角色做一個大致的區分。我們通常把微博空間比喻為城市中心廣場,而把微信空間比喻為私家客廳。這樣,人們的微博交流就類似城市中心廣場的言說,是公共空間的聚合與沖撞;而微信交流則類似私家客廳的沙龍。從輿情的特征來看,城市中心廣場的聚會和喧嘩是輿情關注的核心所在,也是一般性政務機構所要面對的日常事件。而微信基于社會關系網絡復制與放大的交往基礎,則放大了交流的私密性,更多情況下類似“私家客廳”的沙龍。至于私家客廳的密謀,自然有國家安全部門的監管,更多時候,我們所討論的輿情,也就是一般性政務機構面臨的輿情挑戰則主要集中于社會公共空間的眾聲喧嘩即微博空間。如果強行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進行輿情引導,初衷雖好,但公權力事務過度侵入私人生活空間帶來的社會情緒的反彈其實是讓這類輿情引導得不償失的。
微博具有大眾傳播功能,是開放的傳播場域和社會動員平臺;而微信則只是在群體和人際層面上傳播,是封閉的傳播場域。從社會動員的層面來看,微博大眾傳播平臺的屬性導致大量的被本地的民眾卷入其中,形成“脫域化”的輿情事態,而這正是網絡輿情區別于傳統社會輿情的核心特征;而微信好友則更多是本地化的社會關系,微信群內的傳播多以本地化的群體為主,“脫域化”的特征不明顯。從近期的諸多輿情事件來看,微博是輿情發作的的第一信息落點,微信則是對微博信息與觀點進行闡釋的二次聚合和再生產。
因此,微博作為網絡輿情的第一落點則應該承擔起輿情引導主平臺的功能,第一落點處置得當,輿情向第二平臺演化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政務微博近年來成為政府能力建設的重點也正是基于這一特征。
政務微信平臺的交互功能相對較差,作為輿情引導平臺的話,更多是單向傳播、信息發布。但作為線下政務大廳在網絡空間的延伸和放大,政務微信的核心功能應該是“便民服務小秘書”。上海發布等政務微信在建設過程中,既考慮了既有政務微博的功能區分,又考慮了政務微信的獨特性,成為便民服務小秘書功能聚合平臺,值得政務機構學習。
(責任編輯/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