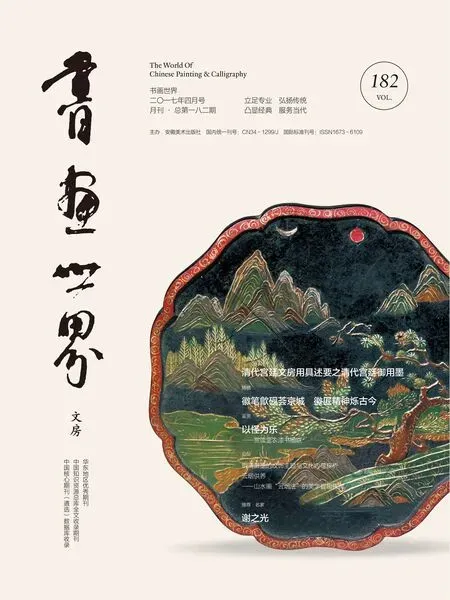名家集評
文_周勛君 等
名家集評
文_周勛君 等
杜勝蘇與他的書法
周勛君| 中央美術學院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
學藝術學博士后、青年書法理論家
勝蘇為人樸厚、謙和,時有魏晉士人骨鯁的風度。品讀他的書作,則能接觸到一個更為細膩、豐富的他。
勝蘇主要寫行草書,對《懷仁集圣教序》、王羲之《十七帖》、孫過庭《書譜》下力尤深。他的書案上長期擺放著這些法帖。此外,包括賀知章的《孝經》以及懷素的《小草千字文》等,隨讀隨臨、隨臨隨寫是他生活的常態。
他的書作多用筆圓轉、流暢,結字雅正,章法疏澹,加上墨色的妍潤與內在流貫不絕的氣息,使人頓生 “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的感受。—這恰是唐代書法批評家李嗣真對行草書境界的一種描繪。它們使得勝蘇與“務求險絕”、在行筆用墨上大起大落的那類行草書區分開來,頗能見出其不俗的個性與美學追求。
目睹勝蘇揮毫,則更能見出他內在的氣度和蘊藉。他對用筆控制有度。在精心引帶的同時,于節奏、力量,于保持內在氣息的連貫和字結構的準確上,令觀者有精絕之感。使人印象深刻的還在于,他始終態度從容。可以想見,假使一個人獨自沉入書寫,他該是怎樣靜默與自如,并從中獲得巨大的喜悅與對書法這門藝術的至高領悟。
勝蘇少年時代即跟隨黃綺先生習書。及長,入南京藝術學院書法專業受教于徐利明教授。弱冠之年,其已負書名。之后,其轉赴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念教育學,其間擔任全日本華人書法家協會理事。學成后,其作為北京市政府引進人才留京工作,現于北京師范大學攻讀在職哲學博士學位。讀書、覃思之余,其須臾不忘翰墨之事。
有志如斯,勝蘇前程當不可限量。
2015年8月6日于望京南湖中園
清朗瀟灑意 墨韻君子風—杜勝蘇先生書法品賞
陳錦若| 當代青年詩人、作家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勝蘇書法里的清逸秀俊以及嫻雅氣度。與勝蘇相交,始于我混跡文壇之初,而今亦有兩三年之久。只是未承想勝蘇竟年輕至斯,因一直有個印象,為書者,大多乃是暮年之士。初見勝蘇之時,其帶了幾分靦腆,反倒是這幾分靦腆讓我等生出了些許親近感。我向來無攀高之心,雖則平和無爭,骨子里卻也有幾分傲骨,所以對于成名之士大多心存仰慕卻并無意去結交。好在勝蘇曠達而隨和,言語之間也十分相投,便相邀為友。古語云:“與君子交,如入芝蘭之室。”誠然,勝蘇的風華意氣也讓人如沐春風。

3.杜勝蘇 馬云與友人對話35cm×75cm2017

4.杜勝蘇 杜甫詩漫興35cm×70cm2017

5.杜勝蘇 趙師秀詩有約35cm×70cm2017
勝蘇習書法始于幼年時期,寒窗數十載,頗有些水滴石穿的韌勁,把一項愛好升華為終生的事業,非有些鐵杵磨成針的堅持不能為。其勤學苦練從他手間的厚繭便可知一二。所以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有堅忍不拔之志。天分、博學、苦練,萃三者于一身,勝蘇的書法能有所成乃是情理之中了。

6.杜勝蘇 毛澤東沁園春?雪135cm ×50cm2017
古語云:“筆墨技法,熟而后巧。”勝蘇取法“二王”,兼學孫過庭、米芾、董其昌等諸家書法。俗話說“書宗魏晉”,即是說,學習書法,魏晉的法帖做范本是最好的選擇之一。勝蘇宗法“二王”,字字力透紙背,帶了些魏晉遺風。他的書作運筆大膽精準,墨色變化豐富,章法得宜,講究虛實避讓,深諳傳統之韻味,又不乏自我性格的張揚。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氣韻游走于字間,觀之讓人如清風拂面,跌宕起伏之間便見幽谷禪風拂面而來,頗有些清風舒朗、飄逸灑脫的晉人韻味。
古人云:“書法講究法度,合法才能質美。”然則今日之書法行列,比比皆是沽名釣譽者,以為能書便是大家,實不知犯了書法之大忌。勝蘇向來將“法度”作為行書之根本,筆筆都不離其宗卻字字見其性情,其字法、筆法、章法得體,乃是經過苦習所得。評書法之優劣莫過于理法、筆力和姿態,古人云:“寓新意于傳統,寄妙理于法度。”“神韻為上,形質次之。”一件好的書法作品,只有達到線條美、結體美、章法美、墨色美、神韻美方才稱得上書法中的上品。無疑,經過數十年的淬煉,再加上本身的悟性使然,勝蘇之書法在而立之年已有所成。其以瀟灑意氣和深厚的書法功底來描繪書法之境,有傳統的曲折方圓,亦有自我創新的變化,從而形成自己的書法之道,展現其書法中的意趣之美、形制之美和氣韻之美。
大雅儒者—杜勝蘇書法藝術
路毅| 青年書法家、篆刻家
書者,寫其心。提筆落墨間,書寫著自己的心靈世界,一橫一豎,一點一畫,將真性情融于筆墨,溢于紙上,在翰墨中找到真實的自我,喜怒哀樂無須掩藏。進而從字可以觀人,有什么心性就寫什么樣的字,點畫的力度和墨色的韻味就是一個人內心世界的外在展示:格高者,字自然高妙;心靜者,筆墨靜遠。杜勝蘇就是這樣一位筆墨高妙靜遠的儒雅書家。

7.杜勝蘇 莫放最難聯135cm ×35cm×22017
觀杜勝蘇書作,可以體味到不激不厲的閑情雅韻。在這個浮躁的世界里,他以純凈極致的筆墨醞釀著自己心靈的散淡和清雅。杜勝蘇書法扎根于“二王”一路,日課不輟,藝道俱進,深得“二王”書法之神髓。觀其書作,可以感受到一種儒者的雅致,不刻意,不造作,折射出儒者的智慧和對藝術本真的信仰。
杜勝蘇早年師從南京藝術學院徐利明先生,后留學日本,并在東京組建“杜勝蘇書道會”,有較高的知名度。經過幾十年的不斷求索,不論是線條還是結構、筆法還是章法,杜勝蘇都將其錘煉得很純凈。觀其書作,可發現有很強烈的“二王”基因,且如“二王”尺牘手札一般,頗具書卷氣息,瀟灑文雅的儒者之氣彌漫其間。觀其章法,行與行拉開了一段距離,這是比較有難度的。行距的拉大增加了行與行之間的張力,這就需要讓行與行互相吸引,不能斷氣,杜勝蘇在這方面做得尤為突出。再從形而上的角度去品讀,我們可以感受到其具有儒家的中庸之道。儒家的思想文化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這一強大的思想和文化體系深深地扎根在中華大地,作為六藝之一的書法也在儒家思想和文化背景下生根發芽。我們現在看到杜勝蘇的書風是不激不厲、風規自遠的,在意境上是爛漫至極而復歸平淡的一種沖淡和中和。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淡、中和并不是像西方的折中和平均那樣刻板。中國的中和是一種動態,是一種平衡,而且這種中和的風格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
“二王”是書法史上的不朽巔峰,當今學“二王”者數不勝數,流行于大江南北。但慣性的用筆造成點畫形態單一雷同,單字結構的定勢使作品上下缺少動勢,這些都是現今“二王”潮流的弊端。杜勝蘇不僅避開了這些流俗,而且寫出了自我,寫出了性情,寫出了格調。這在當今的書壇里是很難得的。這源于杜勝蘇內心的修為。他真正讓藝術滋潤著自己的心靈,不斷提升著自我的精神境界,用散淡的閑情、儒者的心境書寫著自己的藝術人生。
這就是杜勝蘇,一位大雅儒者!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