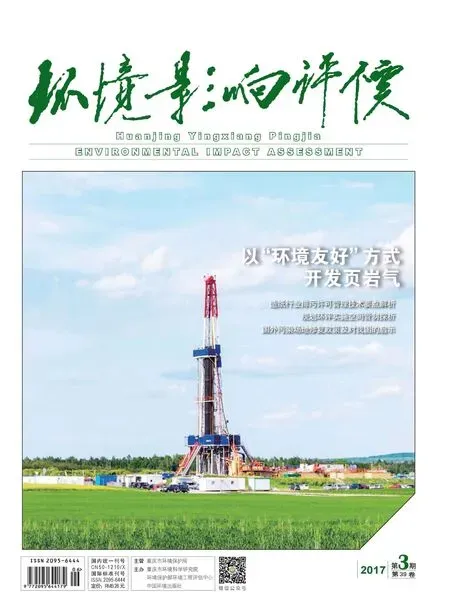國外污染場地修復政策及對我國的啟示
陳瑤,許景婷
(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1816)
國外污染場地修復政策及對我國的啟示
陳瑤,許景婷
(南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1816)
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我國造成大量的場地污染問題。首先探討了我國現階段污染場地的修復狀況,分析了我國場地修復存在的問題,主要有污染場地修復數量巨大、場地修復技術粗放單一、場地修復資金較為缺乏、法規管理體系尚不完善;其次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污染場地修復扶持政策進行了詳細闡述,分別從歐美國家污染場地的修復成本、投融資能力、環境政策實施等方面展開討論;最后在借鑒歐美國家先進的場地修復技術及應用案例、相對完善的場地修復管理體系的基礎上,構建環境保護政策強制力下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管理機制,包括污染場地修復的外部保障體系、污染場地信息與風險識別體系、污染場地修復的內部實踐體系。
污染場地;場地修復;扶持政策;管理機制
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我國帶來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特別是造成大量的場地污染問題。根據2014年《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我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全國土壤總采樣點超標率為16.1%,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占全部超標點位的82.8%。我國針對污染場地修復的前期場地調查、修復風險評估、修復技術采納和政策扶持等一系列管理體系已開展了許多相關研究,由于相應的管理體系尚未完善,具體到污染場地修復過程中,仍然存在著法律法規不健全、污染場地資料缺失、污染場地修復技術工程營運不足、污染權責不清、場地修復的投融資金落實不到位以及污染場地引發的地下水修復等一系列問題[1]。本文在分析我國污染場地特征及場地修復狀況的基礎上,借鑒歐美國家場地修復的管理體系,提出我國污染場地的修復機制,以期為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管理政策發展提供理論借鑒。
1 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管理現狀
1.1 污染場地修復數量巨大
我國礦區的污染區域已達到300多萬畝,實際修復的僅不到20%,由于絕大部分場地在使用過程中都沒有采取相應的土壤和地下水保護措施,因此大部分工礦業場地、固體廢棄物和垃圾填埋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問題[2]。目前,國內城市中遺留下來約有5000個以上的污染場地,包括已經被污染的和潛在污染的場地。如果沒有足夠的前期調查和對場地進行修復,施工過程中將導致急性中毒事故。例如,北京和武漢曾發生在以前的農藥廠址施工時因場地有毒物質導致工人住院治療,廣州由于土壤污染致使亞運村被迫改址,但是現在這塊污染場地仍然被當地居民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用于新建房屋[3]。
近年來,全國各地針對污染場地開展了一系列的修復工程,修復場地大部分位于發達城市,如北京煉焦煤氣廠污染場地的異位修復[4]、上海電子機械廠污染場地及地下水修復工程[5]。
1.2 場地修復技術粗放單一
國內對土壤污染中有機物或者重金屬污染仍然以阻隔填埋與異位修復或植物修復為主[6],其中植物修復技術發展于2000年以后,是目前研究最多、發展最快、應用最廣的修復技術[7]。我國大部分污染場地修復工程實施集中在借鑒歐美國家技術的基礎上模仿,因此修復設備的生產研發、修復過程的運營、修復技術的應用規模等尚處在起步階段。雖然第一批場地修復技術目錄包括土壤阻隔填埋、固化/穩定化技術等15項修復技術,但實際工程應用中仍然非常粗放,修復過程中會出現修復失效、過度修復或者修復風險較大等問題[8]。在具體修復技術應用層面上,修復技術和修復方案相對單一,且過度依賴傳統的阻隔填埋或者固化/穩定化的處理技術[9]。
1.3 場地修復資金較為缺乏
我國缺乏對污染者追責問責機制,因此污染場地修復行為責任主體不明晰,未來較長時間內修復資金都將依賴各級政府以及財政撥款。“十二五”期間,中央政府直接用于土壤修復方面的治理資金達300億元。此外,部分多邊機構也為土壤修復產業提供了額外資金,例如價值4.5億元的世界銀行項目“中國污染場地修復項目”[10]。但由于我國需要修復的場地數量巨大,分配到每個修復場地的費用很少,與美國20世紀90年代污染土壤修復近1000億美元的資金更是相去甚遠。
1.4 法規管理體系尚不完善
2014年國家發布了一系列技術性污染場地準則,為開展污染場地環境調查、風險評估、修復治理提供了技術指導和支持,但是仍缺乏專門的場地污染法律來規范場地管理程序和修復市場。部分省份的場地污染標準比國家標準發展更完善,尤其對于一些城鎮化快速發展需要管理污染場地的發達城市,如北京、上海、重慶、沈陽、深圳,當地很多標準被用于完善國家污染場地的政策制定。場地修復不僅是修復技術及方案確定的過程,還包括前期調查、風險管理、修復評估及過程監管,由于缺乏類似美國的《資源保護和回收法》和《超級基金法》等專門針對污染場地管理的法律法規,導致污染治理責任主體難以認定,無法進行后續修復工作的落實。現有的不能分離重金屬的場地修復技術如阻隔填埋、固化穩定化等都存在長期的潛在環境風險,需要后期持續性的環境監管,因此迫切需要加強長期風險防范的具體管理制度。
2 國外污染場地修復的政策支持
20世紀6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已經開始發展環境修復,美國的污染場地修復歷經“超級基金”的三輪變革與創新,在技術、立法和資金上不斷完善,1990年前后主要以填埋和焚燒處置為主,21世紀以來其環境修復理念已經轉為資源的修復、污染場地的風險管理、評估以及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決策。加拿大土壤修復主要以污染者自我修復為主,各省在聯邦政府指導下實施立法,聯邦政府則對國有土地和“遺孤”土壤實施修復管理。英國和日本則主要借鑒美國模式。同時,歐美發達國家廣泛采用基于風險的管理策略,開展了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污染場地修復評估與實踐研究,包括修復技術篩選矩陣、多目標決策支持技術、費用效益分析、生命周期評估、環境效益凈值分析等定量評估模型以及文件導則、決策流程圖、計算機軟件等決策支持系統,其關鍵技術方法包括污染物的土壤質量環境準則制定、修復技術研發及應用、污染場地的風險管理及評價等。這些管理決策系統與技術手段為污染場地的前期調查、風險特征、評估決策以及后期的修復管理提供了理論支撐、技術保障和法律依據[11],如圖1所示。

圖1 發達國家污染場地修復的管理體系Fig.1 Management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2.1 美國污染場地修復的政策支持
1980年美國議會通過《綜合環境反應、補償和責任法案》,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超級基金”,這項法案填補了污染場地修復的空白。“超級基金”設立了高達16億美元的信托基金,專門用于治理無法確定責任方的污染場地,并通過確定“潛在責任方”,以“污染者付費原則”解決修復經費問題。1980—2015年,美國國家環保局(EPA)設立的國家優先處理目錄(NPL)和基金替代協議(SSA)共納入1439個污染場地,受地下水污染遷移的場地累積1138個。截至2015年,NPL中已有1177個場地完成物理修復實施工程,“超級基金”項目共完成93 901個污染場地的評估[12]。除了設立超級基金,EPA還通過多元化的融資渠道來支持場地修復的資金需求。超級基金(EPA以及潛在責任組織)聯合美國能源部、美國軍方、州政府修復計劃、資源保護和回收、地下儲備、私人公司共同成為美國污染場地修復的資金來源渠道,其中國家能源部是當前美國污染場地修復的最大責任方,污染場地年修復費用均超過20億美元。同時,美國提出“棕地開發”的土壤環境管理模式:國家鼓勵企業進行土壤修復和土地開發,并對由于污染而不能有效開發的土壤提供各種補貼和政策優惠,從而使美國場地修復產業呈現良好的發展前景。美國除在超級基金中設立修復技術和法規,制定風險管理的策略和工程評估,還參與地方州環保署設計系列的環境修復實踐工具共同完善場地修復管理,如明尼蘇達州環保署實施的全過程污染場地風險管理決策支持系統以及伊利諾斯州實施的污染場地修復技術評估矩陣等[13]。
美國在環境訴訟方面推動部分類別對原有污染場地清理的做法,對我國的污染場地治理也有很多借鑒意義,尤其是污染場地涉及地下水污染的場地修復問題。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環境責任方面制定有一系列法律,如表1所示。相關法律規定了排污者需要負責治理污染并賠償由于污染對環境造成的財產損失。聯邦和州環境行政部門可以依法要求排污者停止排污,并對已經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進行治理,同時聯邦和州檢察機關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并加快治理污染;直接受害的單位和個人也可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并加快治理。

表1 美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環境責任相關的法律
2.2 歐盟污染場地修復的政策支持
歐洲環境局(EEA)聯合研究中心對39個歐盟國家(包括33個EEA成員及6個EEA合作成員,稱為EEA-39)中近1/3的土壤進行了調查,發現每1 000名居民居住地中有4.2個潛在污染場地,每10 000名居民居住地中有5.7個污染場地。初步推斷整個歐洲約有250萬個潛在污染場地,其中約14%(3.4萬個)的土壤可能已經被污染且需要修復。截至報告日,EEA-39中27個成員國約117萬個潛在污染場地已經得到識別,約占EEA-39總污染場地的45%。EEA-39污染場地總量估計達34.2萬個,其中1/3的污染場地已經被識別,約15%的污染場地已經得到修復。28國已經實現了在報告中呈現全面的污染場地目錄,25國已經建立了污染場地中央國家數據庫。
歐盟污染場地管理的總支出,平均約42%來源于各國的公共預算,最高如愛沙尼亞為90%,而比利時為25%;每年污染場地管理的國民支出約為人均10歐元,從塞爾維亞的2歐元到愛沙尼亞超過30歐元不等,相當于0.4歐元/百萬GDP。污染場地管理的全國財政支出中約81%用于修復,僅15%的支出用于場地調查。德國實行“誰污染、誰付費”原則,如果污染企業無力治理,即使向政府提出申請并獲得批準,仍要承擔10%的費用,其余90%的費用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擔。針對歷史遺留的礦區,德國聯邦政府成立了專門的礦山復墾公司,復墾所需資金按照聯邦政府75%、州政府25%的比例分擔。面對嚴峻的污染場地修復形勢,歐盟各國也正致力于污染場地風險管理模式的相互借鑒與協調,已經初步構建了包括場地修復政策、標準、市場、決策等統一的污染場地管理體系。
3 構建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管理機制
修復產業屬于政策驅動型的產業,通常基于國家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目標,以政策法規的強制性為基礎,間接地、被動地實現修復需求。在借鑒歐美國家場地修復技術及研發、工程應用、管理體系等經驗的基礎上,立足污染場地特征、經濟社會發展、科研水平及現階段技術水平等,構建我國場地修復的管理機制。環境保護政策對污染修復的強制力推動修復產業的發展,政府采取相應的激勵政策應對企業的污染修復行為,企業實施場地修復工程也促進場地修復政策體系的完善。修復產業的內部實踐活動以修復技術體系與投融資體系為核心,在外部保障體系、信息系統與風險識別體系的支持下,構成相互反饋的動態管理機制,如圖2所示。

圖2 環境政策引導下我國場地修復的管理機制Fig.2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site remediation conducted b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
3.1 污染場地修復的外部保障體系
污染場地修復管理機制的外部保障體系由貫徹整個修復過程的環境經濟學理論、歐美場地修復成熟經驗、我國相關環境法律以及污染場地責任制構成。環境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污染治理的根本理論前提,因此污染場地的環境修復應遵循基本的環境經濟學原理,在我國環保法律的大環境中實施具體的場地修復實踐。由于我國的污染場地產業起步較晚,因此需要借鑒歐美國家成熟的場地修復技術及工程案例,并根據我國場地污染的不同特征來實際應用。以“超級基金”為啟發點,遵守《環境保護法》中“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落實污染者責任,實現污染修復全過程的責任追究體系,堅持“污染責任終身制”原則,有效促進環境法律法規在場地修復中的執行力,切實解決當前我國污染場地責任追究過程中的追責問題。
3.2 污染場地信息與風險識別體系
污染場地管理機制中信息與風險識別體系主要由基礎信息體系與風險評估體系構成。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我國開展了首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全國土壤的點超標率為 16.1%。這些只是對土壤的總體狀況、污染類型和區域的調查,對具體污染場地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都缺乏基本的信息數據,部分已經調查的污染場地存在數據和資料嚴重缺失的狀況。因此,針對需要修復的污染場地,須進行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構建信息的共享平臺與管理體系,以區域為單位建立類似美國“國家優先治理目錄”的場地檔案或者類似歐盟的污染場地中央數據庫。借鑒發達國家的修復理念,風險評估的目標也應從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多目標管理決策出發,尋找最合理解決污染場地風險評估的途徑。
3.3 污染場地修復的內部實踐體系
污染場地修復管理機制的內部實踐體系由修復技術體系與投融資體系構成。發達國家的修復技術已經從簡單的技術應用與研發發展到修復技術的篩選與評估,因此我國污染場地修復可以借鑒先進的修復技術,并結合我國土壤的實際狀況構建較為完善的修復技術標準體系,在污染場地大量實際案例應用的同時能與場地調查及評估體系相結合,實現場地不同污染類型的修復技術選擇與評估。鑒于修復技術篩選存在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場地修復技術體系應以修復技術原理為基礎,構建場地修復的國際交流和合作平臺,結合國外先進場地修復技術的應用案例,規范和優化國內場地修復技術的選擇。由于無法追究責任方,缺乏相應的融資手段,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的資金來源單一,70%以上的修復費用來源于國家財政;而美國和歐盟的場地修復資金來源廣泛,均呈現多元化融資渠道,且60%以上的污染控制資金均由私人企業或社會來支付[14]。隨著我國場地修復產業的市場需要不斷擴大,財政撥款無法滿足場地修復的資金需求,因此必須創新現有的資金投入,擴展投融資渠道,有效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進入修復產業。
4 結語
場地污染由于其隱蔽性、滯后性、不可逆轉等特點存在極大的風險和環境危害。通過分析近年來我國場地修復的現狀、相關的環保法規、修復技術標準、及工程案例實施,在借鑒歐美國家場地修復先進技術和系統的場地修復管理機制的前提下,意識到場地修復產業風險與機遇并存,我國污染場地土壤修復蘊含巨大市場需求。
我國污染場地修復產業的發展是復雜的博弈過程,涉及國家、地方政府及相關的環保部門、污染責任方、污染受害方、污染治理方等多方利害相關人,修復過程需要循序漸進地發展。因此面對場地修復發展的困境,需要構建完善的場地修復產業管理體系,以環境法律法規、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支撐,遵循“污染者付費”原則及污染追責機制,在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的保障下,借鑒國外先進的修復技術標準體系及科研設備,創新修復產業的投融資機制,通過多渠道資金籌措方式全面提升我國場地修復的技術水平以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1] 宋昕, 林娜, 殷鵬華. 中國污染場地修復現狀及產業前景分析[J]. 土壤, 2015, 47(1): 1- 7.
[2] 謝輝, 胡清, 張鶴清, 等. 中國污染場地修復發展回顧建議與美國經驗借鑒[J]. 環境影響評價, 2015, 37(1): 19- 23.
[3] Yang H, Huang X J, Thompson J R,etal. China’s soil pollution: Urban brownfields [J]. Science, 2014, 344(6185): 691- 692.
[4] 劉寶蘊, 閆永旺. 煉焦煤氣廠污染場地修復工程案例分析[J]. 環境工程, 2014, 32(10): 161- 164.
[5] 張晶, 張峰, 馬烈. 多相抽提和原位化學氧化聯合修復技術應用——某有機復合污染場地地下水修復工程案例[J]. 環境保護科學, 2016, 42(3): 154- 158.
[6] 周靜, 崔紅標, 梁家妮, 等. 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技術的選擇和面臨的問題——以江銅貴冶九牛崗土壤修復示范工程項目為例[J]. 土壤, 2015, 47(2): 283- 288.
[7] 苗欣宇, 周啟星. 污染土壤植物修復效率影響因素研究進展[J]. 生態學雜志, 2015, 34(3): 870- 877.
[8] 陳瑤. 我國生態修復的現狀分析[J]. 生態經濟, 2016(10): 183- 192.
[9] 宋云, 尉黎, 王海見. 我國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技術的發展現狀及選擇策略[J]. 環境保護, 2014, 42(9): 32- 36.
[10] World Bank. Project Information Document (PID) Appraisal Stage[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4.
[11] 張紅振, 於方, 曹東. 發達國家污染場地修復技術評估實踐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 環境污染與防治, 2012, 34(2): 105- 111.
[12] U.S. EPA. Fiscal Year 2015 Superfund Accomplishments Report[R]. 2015.
[13] U.S.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Forum.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white paper—Integrating sustainable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metrics into remediation projects [J]. Remediation Journal, 2009,19(3): 5- 114.
[14] 安樹民, 張世秋, 王仲成. 試論環境保護投資與環保產業的發展[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3): 96- 99.
The Policy of Foreign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CHEN Yao, XU Jing-t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also caused a lot of site pollution problems. First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estor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econdly, supporting remediation policies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were elaborated in detail, including remediation costs, ability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se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site remediation, and relatively completed management system on site remediation, we constructed a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under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was comprised of external security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information and risk identification system for contaminated sites, and internal practice system of contaminated site remediation.
contaminated site; site remediation; supporting policy; management mechanism
2016-10-25
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企業生態修復與環境保護政策的互動機制研究”(2015SJB085)
陳瑤(1982—),女,江蘇揚州人,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會計、財務管理,E-mail:cy1087@126.com
10.14068/j.ceia.2017.03.011
X53
A
2095-6444(2017)03-00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