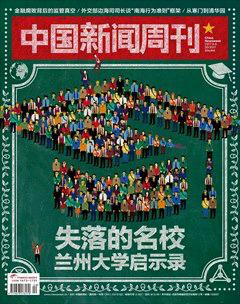“雙一流”建設需要深化大學治理體系改革
錢煒
謝維和既是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者,又是大學管理的實踐者。他是清華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歷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首都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清華大學副校長。因此,對于怎樣辦好大學,他既有理論上的研究與思考,又有很多切身體會與實踐經驗。
就中國高校究竟該如何建設“雙一流”,以及身處欠發達地區的重點大學出路在哪里”等問題,《中國新聞周刊》近日采訪了這位高教領域的專家。

2014年6月30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意大利駐華大使白達寧出席了2015年米蘭世博會中國企業聯合館批委會與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合作共建伙伴簽約儀式。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曾經的名校,蘭州大學正在經歷一場以人才流失為主要標志的衰落,這個現象反映出的問題是什么?
謝維和:據我所知,由于現在全國高校都在爭創“雙一流”,很多大學為此都在大力引進人才,相應地,就會有一些學校的人才在流失,可能蘭大表現得更加突出一些。
教育部在今年年初下發了文件,要求東部的高校不要去中西部高校“挖人”,但我覺得,在支持西部高等學校建設的同時,更應該去分析和研究這個現象背后的某些深層次的因素,特別是體制性的因素。
西部高校人才流失問題,從根本上而言,反映出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體系存在著某種結構性的缺陷。而這些現象與問題也要求我們進一步全面地和歷史性地認識、理解和實施中央進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若干重要措施與計劃,包括“雙一流”的建設方案。
根據國務院2015年下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除了上述“雙一流”目標外,還有“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高等教育強國?我們可能會首先想到,在世界TOP100的大學里要有中國的高校,且越多越好,名次越靠前越好,但這并不是全部。高等教育強國是一個結構性概念,它指的是,能滿足不同層次和類型的人才需要,適應與引領不同地方與行業的發展,以及支撐國家和地方不同戰略的高等學校與學科的整體。
實際上,在高等教育領域,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真正差距并不僅僅體現在頂尖大學這個指標上,而更多地表現為結構上的落后。
中國新聞周刊:但也會有人說,我們的財力有限,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先辦好幾所世界一流大學再說。這種想法是否合理?
謝維和:從高等教育發展的時序而言,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211工程”與“985工程”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戰略。但是,現在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經濟學的發展理論上,有個庫茲涅茨倒U曲線理論,它說的是,在經濟起飛階段,經濟越發展,貧富差距越大,到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情況才會慢慢改善,最終達到一個比較公平的狀況。這種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差距的關系及其發展呈現出一種倒U形的曲線。
教育的發展也具有這樣一種規律性的發展趨勢。我們現在就已經處在了這個倒U曲線的拐點上,因而要更多地從結構優化的角度考慮教育資源的配置,使高等教育能夠得到更加全面和協調的發展,這與國家的整體部署是一致的。
如果說,“985工程”的思路是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的話,到了“雙一流”,就不應該再按照原來那個思路辦事了,應該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調整,應該更加強調高等教育的結構性優化。這也是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特征。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是怎樣的呢?
謝維和:以美國為例,從波士頓到西雅圖,從芝加哥到紐約,都有很好的大學與學科。從它的辦學層次上來說,除了最頂尖的“常春藤”大學,還有“小常春藤”大學,以及很多優秀的州立大學。比如亞利桑那大學,它的地球與天體學科水平就非常高,據說美國的太空月球車就是他們研制的。
除了上述這些大學,還有一些小而精的學校。例如,位于波士頓附近羅德島的羅德島設計學院,雖然它并不在排行榜里,但是它其實是設計行業的世界級頂尖學府。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高等教育資源分布相對均衡,結構也比較合理,在不同層次和類型方面都有非常優秀的學校。
另外一個典型例子是德國,盡管在各類排行榜中,德國大學的名次并不那么顯赫,但是德國大學的整體水平卻不能不讓人佩服。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蘭州大學的發展困境,很多分析人士認為是受地域所限,因為甘肅省的經濟較為落后。你對此怎么看?
謝維和: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當地高校發展確實有關,但并非直接的因果關系。例如,美國的康奈爾大學水平很高,卻坐落在遠離紐約的伊薩卡鎮。再比如,UIUC(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其實也并不在芝加哥市區,而是在一個小鎮上,而這個小鎮就完全是一個大學城。
由此可見,大學并非都要建在經濟發達的繁華大城市。當然,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美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相比中國還是更加均衡的。這種經濟發展的均衡性也是美國高等教育分布均衡的重要基礎。
中國不同地區發展的不均衡性,的確影響了高等教育的結構優化。然而,這種不均衡恰恰要求當地的大學能夠積極主動地推動和促進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在這方面,美國的耶魯大學加強與學校所在地紐黑文市的合作,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提升城市水平,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這里所反映的一個突出問題,正是中國高等學校的治理體系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地方,即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系不夠。可以認為,中國高等學校的治理體系仍然是一種政府與大學之間的二元結構,需要不斷地調整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系。這也是自從1985年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改革的基本取向。
這種二元結構的改革,簡單地說,是不斷下放或取消某些行政審批權,給予高等學校更多的辦學自主權。同時,改善和提高政府管理與服務的能力。然而,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高校不僅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與政府的關系,同時也需要建立與市場的聯系,形成一種政府-大學-市場(或社會)的三元治理體系。
中國新聞周刊:大學治理結構如何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謝維和:在保證政府投入的同時,高等學校應當進一步加強與社會和市場的聯系,爭取從市場上獲得更多的辦學資源,完善人才培養模式,提高辦學水平與質量。
據我所知,很多地方高校,政府撥款占到學校收入的70%~80%,甚至更高。而有些辦學水平比較高的大學,常常能夠從市場上或者通過與企業的合作獲得較多的資源。
如果在一所大學的預算或總收入中非財政性收入的比例太低,那也就說明你從市場上獲取資源的能力是有限的。更加重要的是,這并非僅僅是一個資源的問題,它反映了一個大學的定位,以及與社會經濟相結合的程度。
現在,我國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基本上是二元體制的產物,學校的職能部門基本是對應政府機關各部門來設置的。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比如,目前有些大學就已經設立了基金會、理事會、企業合作委員會,以及相關的部門與機構,進一步加強拓展與市場、社會和企業的合作。
“雙一流”建設的目標是世界一流大學與學科,而深化治理體系改革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路徑。“雙一流”方案明確要求,把“構建社會參與機制”作為改革的重要任務,要求“高校要不斷拓寬籌資渠道,積極吸引社會捐贈,擴大社會合作,健全社會支持長效機制,多渠道匯聚資源,增強自我發展能力”。這樣,才能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與內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