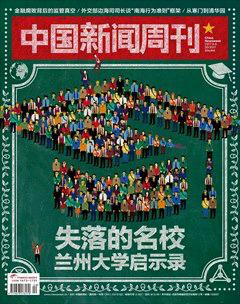煤都卡拉干達:在新與舊之間
文龍杰
也許,煙火比燈火更接近城市的本質吧
從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朝東南方向開車約三小時,就到達了這個國家最大的工業城市卡拉干達。這里也是該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龍興之地”,他正是由此逐步登上政治舞臺的。
卡拉干達是卡拉干達州首府,人口約50萬,與號稱100萬人口的首都阿斯塔納相比,倒顯得人氣更著。城市有時候就像水果或者蔬菜,其孕育和成長需相當的時間,若假諸大棚之類現代技術催生速成,韻味總是差那么一些。
談到卡拉干達的孕育與成長,則不得不提煤礦。蘇聯時期,這里坐擁全蘇第三大采煤區。今天的卡拉干達仍以采煤和采煤機械制造為主,依煤礦而建的居民區遠近皆是。城中心還矗立著一座名為“礦工之榮譽”的塑像,一名俄羅斯礦工和一名哈薩克礦工共同將一塊煤托過頭頂。
城市不大,從市中心開車10多分鐘就能到大巴扎(自由市場)。循著食物的味道,我們找到了大巴扎的入口。所有小吃店的門臉都被煙火熏得烏漆麻黑,烤包子的馕坑和烤肉的鐵架子是標配。這巴扎比阿斯塔納的規模要大,布局也稍顯雜亂,既有常年在此經營的各色坐商,也有閑暇時隨手將自家地中果蔬用小桶拎來換點花銷的哈薩克老奶奶。一把韭菜才100堅戈,這在阿斯塔納可是要賣到1000甚至1500堅戈。如此新鮮的寬葉韭菜在中亞是稀缺物,同行的朋友識得奇貨趕緊出手搶下。西紅柿、黃瓜、蘋果、干果比阿斯塔納要便宜近一半。物美并價廉,我們這些“中央來的人”被驚得目瞪口呆。看來,坊間傳言許多住在首都的人周末要來卡拉干達囤貨,倒真不是空穴來風。
城外西南方有一座由勞改營改建成的紀念館,開車自駕一小時可達。門票500堅戈(約合人民幣10元),拍照則每個拍攝設備另加收300堅戈。游客不多,也就十幾個,我們一行6人就占去了近一半。
勞改營建于1930年,早于卡拉干達市的建市時間1934年。這是全蘇規模最大的勞改營——有研究說是全世界最大的,當年關押著來自全蘇的政治犯、科學文化界人士,出身地主等階層的“壞分子”,二戰時還關押了數量眾多的俘虜。勞改營于1959年關閉,但許多人在卡拉干達留了下來,或許“山中一日,世間百年”,物是人非,已無去處。
那些留在卡拉干達的精英們為當地的科教文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便是“戴罪”勞改期間,許多科學家的研究也是可圈可點,從勘礦到牛羊育種,不一而足。許多藝術家則借各種慶祝日的機會舉辦音樂會,排演話劇,甚至演出芭蕾舞劇。
整個紀念館的敘事框架是“過去黑暗,如今光明”——哈薩克斯坦的獨立就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結果。這是歷史本來的邏輯嗎?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或許會批評這樣的提問太過幼稚。在哈氏看來,博物館等作為形塑集體記憶的重要場域,指向的從來不是歷史的真實(假如存在的話),而是當下的需要。哈薩克斯坦獨立25年,主權和民族建構仍然是擺在面前的現實課題。君不見,當前又熱絡起來的“去俄化”風頭?
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題為《面向未來:社會意識到現代化》的署名文章中指出,應從2018年起在全國推廣哈薩克字母拉丁化。這意味著,襲用俄文基里爾字母的現行哈薩克文很快將成為歷史。
去年12月16日,納扎爾巴耶夫與阿斯塔納市長為哈薩克斯坦獨立25周年紀念碑揭幕。擔任主持的市長大概哈語不太流利,納扎爾巴耶夫(據說當時酒后微醺,興致頗高)說:“快別用哈語講話了,你的哈語我都聽不懂。”這句揶揄不意由麥克風傳了出去,該國官媒發了一則《總統聽不懂阿斯塔納市長說哈語》的新聞,點擊量爆表。媒體還發布了一張全哈高官哈語水平top 10排行榜。
實際上,自獨立以來,哈語和俄語的地位一直是哈國的敏感問題。哈語拉丁化作為一種激發民族主義的手段,讓很多人擔心,潘多拉魔盒打開容易關上難。
不久前一位中國土豪在哈征婚或許就是例證。其實他也在其他國家搞了類似活動,卻不想在哈鎩羽,還引發了當地的示威游行。哈國一位小有名氣的歌唱演員甚至在網上公開謾罵,稱只有無德的妓女才會外嫁給中國人,誠實善良的哈薩克人一旦與中國人結婚便會丟失原有的優良品質。
回到阿斯塔納時,已近晚上9點。一座座現代感十足的建筑在夜里顯得光怪陸離。對于阿斯塔納,納扎爾巴耶夫總統是頗以之自矜的,他曾在一次國際論壇上與馬云對話時感情流露,稱自己窮20年之心血才建起了這座城。不過,也有一些哈國民眾走向街頭抱怨,國家靠石油獲得快速發展,可出產石油的西哈并未受益,因為所有的錢都拿來建造新首都阿斯塔納了。
一時竟有些想念既破且舊的卡拉干達,十分希望能再去那里體會一下“民間疾苦”:地下通道中賣便宜貨的地攤、街頭兜售盜版音樂碟片的小哥、大巴扎里高低錯落的叫賣和認真的討價還價……也許,煙火比燈火更接近城市的本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