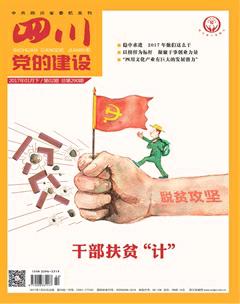長江路上的一個春節
賈永
長江路上的一個春節
賈永

編者:
雞年新春將至,在舉國歡騰、辭舊迎新、闔家團圓的日子里,或許在團年的餐桌上還能聽到些許對革命歲月的回憶,然而大多數的年輕人可能早已忘記憶苦思甜的傳統。為提醒年輕人不忘老一輩革命家為了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拋頭顱灑熱血的偉大歷史,珍惜如今來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樹立遠大的理想抱負,編者在本期帶領讀者回到80多年前那個硝煙彌漫的年代,了解一段紅軍長征路上過春節的感人往事。
中央紅軍在長征路上度過的那個春節,是公元1935年2月4日,農歷乙亥年(豬年)春節。在本該萬家團圓的日子,辭舊迎新的煙火卻并不能沖淡濃烈的戰場硝煙。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遵義會議之后的紅軍依舊是危機重重,必須盡快殺出一條血路,突出重圍。

年關將近,土城血戰
豬年的春節漸漸臨近,長征隊伍卻籠罩著低沉的氣息。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之際。紅軍的前方,是沿長江設防的川軍;身后,是追擊而來的中央軍,雙方力量之比為3萬: 40萬。
湘江血戰,8.6萬人的長征大軍損兵5萬之余。中國革命的航船進入最為狹窄的航道——黨和紅軍在痛定思痛中,又一次選擇了毛澤東。臨危受命,立于船頭,擺在剛剛過了41歲生日的毛澤東面前的是如何帶領這條風雨飄搖的航船,沖出險象環生的漫漫航道。
一路征戰,傷兵滿營,隆冬時節,缺衣少彈。此刻,東去湘西與賀龍肖克的二六軍團匯合的計劃早被敵人識破,而地貧人稀的黔北又難以建立根據地,更為嚴峻的是,蔣介石已經電令他的各路大軍務必圍殲紅軍于烏江西北地區。北渡長江進而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似乎成了中央紅軍絕地重生的唯一選擇。
危機四伏。留給紅軍的機會越來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從遵義轉至桐梓縣城,隨即下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地域定在宜賓、瀘州之間。毛澤東的設想是,趁著年關臨近,川軍江防麻痹、國民黨追擊軍尚在途中之際,避其鋒芒,悄然過江,擺脫圍追堵截。
在土城方向,紅三軍團等后續部隊則遇到了川軍郭勛祺部的尾隨追擊。自從紅軍進入黔北,劉湘就讓他的川軍出境迎戰,“抱必死決心,奮勇阻截”——川北的紅四方面軍已經難以應付,“四川王”劉湘顯然不讓中央紅軍再入川攪局。
土城至赤水盡是峽谷,毛澤東決定以紅三軍團3個師,占領土城東北5公里的607.5至楊柳莊一線南面高地,紅五軍團2個師占領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線北面高地,干部團在土城以東兩公里處的白馬山作預備隊,以絕對優勢兵力速戰速決,對尾追之敵打一場“殲滅戰”。
28日拂曉,戰斗在蒙蒙細雨中打響。戰至黃昏,雙方仍呈膠著之勢。紅軍發現,川軍不是情報中所說的兩個團,而是兩個旅,另有兩個旅的增援部隊還在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為像黔軍一樣一擊即潰的川軍戰力絲毫不亞于中央軍,輕重武器裝備甚至優于中央軍。“殲滅戰”成了“拉鉅戰”。人均僅有20發子彈的紅軍陷入危機。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劉伯承親臨一線指揮。

紅軍“四渡赤水”一渡渡口圖/新華社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彈雨中。炮彈,在朱德身邊爆炸,氣浪幾次把這位“紅軍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50歲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樣端著機槍沖入敵陣。山谷之中,已經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體。紅五團團長趙云龍犧牲,紅十團團長姚喆、政委楊勇、副團長文年生、團參謀張震先后負傷。在戰役核心之地青杠坡參戰部隊中,20年后出了200多名將軍,而在整個土城戰役的紅軍一方,后來則出了新中國的三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劉少奇、楊尚昆;七大元帥:朱德、劉伯承、彭德懷、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和五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林彪、葉劍英、耿飚、張愛萍,堪稱“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觀”。
雁陣驚寒。眼看短時間取勝無望,中央政治局連夜命令停止與敵人糾纏,暫時放棄北渡長江計劃,避實就虛,西進川南。29日拂曉,紅軍從土城渾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過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開。
毛澤東的年夜飯:唯一一碗臘肉送給了傷員
殘陽如血。部隊撤至四川敘永縣城南79公里處的石廂子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這里與貴州畢節縣大渡鄉和云南威信縣水田寨接壤。雄雞報曉,三省可聞,故而三地交匯處統稱為“雞鳴三省”。當時的石廂子是一個僅有400多人的小村莊,75戶漢、彝、苗人家雜居。地處大山深處,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連除夕之夜的爆竹聲也是稀稀拉拉,警衛員好不容易弄來一碗臘肉,被毛澤東送給了傷員。
雨,依然淅淅瀝瀝。毛澤東的心情也仿佛雨天一樣。雖然在此前的遵義會議上成為政治局常委,重回中央領導層,但出山后參與指揮第一仗就遭受重創,顯然讓他難以接受。土城戰役,雙方損失均為3000人左右。然而在毛澤東眼中,敵我力量如此懸殊之際,即便慘勝也意味著失敗,更何況,戰死的紅軍都是經歷過蘇區反“圍剿”和長征戰火千錘百煉的精英,是中國革命的種子。抗戰時期,連紅軍的衛生員、炊事員都能到敵后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若干年后,毛澤東還對土城之戰難以釋懷。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說:“我是犯過錯誤,比如打仗……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
與毛澤東此時的心境所不同,進入人生又一個本命年的蔣介石似乎迎來了剿共以來難得愉悅的一個春節。從失守贛南到兵敗湘江,紅軍元氣大傷。眼下,這支疲憊之師已經被他的幾十萬大軍團團圍住。在他看來,全殲中央紅軍,以消心頭之患,只是時間問題。按照“攘外必先安內”的一貫思路,這個春節,他的要務是與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周旋。大年初六,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在他的廬山別墅“美廬”下達了《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一)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生擒者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生擒者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三)周恩來、張國燾、項英、王稼祥、陳昌浩,生擒者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四)王宏坤、王樹聲、何畏、孫玉清、余天云、王維舟、劉伯承、葉劍英、倪志亮,暨偽軍團政委、偽軍長等匪首,生擒者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毛澤東顯然沒有看到1935年2月15日刊登這則消息的云南《民國日報》,自然也無暇把戰爭中的春節放在心上。這段時間,他與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緊落實遵義會議的未盡事宜。大年初二,部隊向云南威信境內轉移。當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棟因門窗雕有花草蟲鳥圖案而聞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裝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著中央最高“權力”的幾副挑擔。

石廂子,“雞鳴三省”中央紅軍長征會議陳列館圖/廉鋼
那個春節,重要會議一個緊接一個。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灘召開會議,正式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縣城所地扎西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新的戰略方針,鑒于張國燾借口嘉陵江“江闊水深,有重兵防守”,不僅不率紅四方面軍南下以吸引川軍,反而北攻陜南致使川軍無后顧之憂,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紅軍北進,會議決定改變原定北渡長江的計劃。會議同時決定,對中央紅軍進行整編,徹底改變長征以來“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的局面。
這一系列的會議后來被黨史界統稱為“扎西會議”。“扎西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未能及時解決的問題,完成了領導人的更迭和全軍的思想統一,成為遵義會議的有力續篇。
扎西整編:紅軍師長當團長,10個連長一個班
“二月里來到扎西,部隊改編好整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幾……”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由陸定一、賈拓夫編寫的《長征歌》中有這樣的描述。大年初六的政治局會議,開了一個通宵。凌晨,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簽署的《關于各軍團的縮編命令》隨即發出。中央紅軍由30個團縮編為17個團,機關和后勤人員大幅度精簡,充實基層;運輸隊、掩護隊、保衛局、供給部等機構的大部分人員,以及司號員、理發員、炊事員、通訊員等等,大都編入作戰連隊,紅軍師長當團長,10個連長一個班。整編后的一個團兵力達2000多人,相當于整編前的一個師。
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精簡。凡兩個人抬不動的東西都要甩掉。早已成為部隊沉重負擔的X光機、造幣機、造彈機、印刷機、磅秤、鑄銀模子等笨重機器和器材則一律處理掉。長征開始后,大搬家式的長蛇陣隊沒有了。
丟掉了“包袱”,實現了“消腫”,部隊面貌煥然一新。那支高度機動靈活、善打運動戰的紅軍隊伍又回來了。趁著國民黨幾十個團匆匆在長江南岸布防阻攔,貴州兵力空虛之際,毛澤東再度揮師黔北,殺了敵人一個回馬槍。紅軍先頭1個團先敵搶渡二郎灘,成功掩護部隊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取桐梓、奪婁山關、重占遵義城,5天內殲滅和擊潰蔣介石謫系吳奇偉部兩個師另8個團。
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落荒而逃的吳奇偉匆匆下令砍斷烏江上的浮橋。尚未過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為紅軍俘獲。蔣介石如夢方醒:果真是毛澤東又回來了!
硝煙未散。毛澤東在血色黃昏中策馬而至,登上千古雄關婁山關,吟誦他長征后的第一首詞《憶秦娥·婁山關》。此時此刻,離毛澤東重新指揮紅軍不過40天。在他看來,得意之筆才剛剛開始,盡管長征依然山窮水復,但前路同樣柳暗花明。
正月未出,按照當地人的說法,這一天,還在過年之中。這正是——
毛澤東撒豆成軍,三萬余紅軍成天將;
蔣介石瀕于奔命,四十萬追兵徒奈何?(稿件來源: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責編:張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