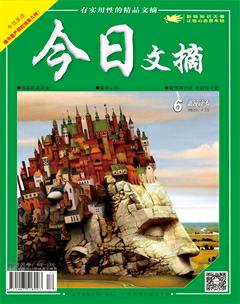世界“逆城市化”帶給中國的思考
佚名

最近,一篇名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員的自白:我為什么選擇離開》的文章,又在網上帶火了一波“逃離北上廣”的節奏。對于這種思潮的解讀,最流行的說法莫過于:中國已經開始“逆城市化”。
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逆城市化”潮流,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的美國,當時,有錢的中產階級紛紛搬離擁擠的城市,住到城郊的別墅中。
仔細比較,不難發現“逃離北上廣”與這種逆城市化的區別:美國逆城市化的進程由社會上層發起,“逃離”的目的是為了享受生活。而中國的“逃離者”大多是處在奮斗期的年輕人,他們“逃離”的理由只是為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結婚買不起房,孩子上不了學。
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多次發生過與中國當下類似的情況。
早在古羅馬時代,地中海世界已經開始了第一輪城市化熱潮,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城人口曾達到120萬之巨。隨著人口暴漲,城內擁擠不堪,瘟疫橫行。為了逃避這座巨型城市所帶來的疾病和混亂,人們開始紛紛“逃離羅馬”。到了公元550年,羅馬城內只剩下了25萬人。
在羅馬衰亡后,歐洲有近千年沒有出現人口上百萬的大型城市。然而,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隨著工廠的開辦,大量人口開始向大城市聚集。1900年,倫敦人口已經達到650萬。紐約曼哈頓的人口也從1790年的3 3萬暴漲到1910的233萬。
然而,曾經困擾羅馬的夢魘再次降臨。尤其是對于底層平民來說,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嚴重,死亡率上升,成了大城市給他們帶來的噩夢。于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早期,受夠了的人們開始出現了一波“逃離紐約”“逃離倫敦”的熱潮。
看上去,羅馬衰敗的悲劇又要重演。然而,與中心城市人口減少相對的,是同時代英美的城市化率直線上升。那些從中心城市出走的人,在各地建立了新的城市,比如世界聞名的電影城好萊塢、飛機城西雅圖等。在這些新興城市的助推下,英美邁過了城市化率50%的門檻。時至今日,英美依然是世界“大城市病”解決得最好的國家,紐約和倫敦中心區域的人口都未超過千萬。
眼下,中國的城市化率如當年的英美一樣超過了50%,在這個臨界點上,出現“逃離北上廣”式的思潮是正常的。但愿我們能通過深化改革,讓各地資源的分配平均化,讓那些“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從“逃難者”變為“播種者”,在新的城市播下自己的希望。■
(范慶峰薦自《齊魯晚報》)
責編:我不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