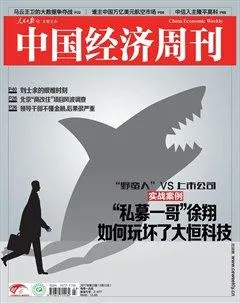上市公司獨董怪象:為何各方都不滿意
賈國強
從獨董不“懂”到獨董不“獨”
從2016年萬科獨董張利平自稱因存在潛在關聯利益回避表決,到今年5月12日深交所修訂獨董備案制度強化獨董忠實履職,再到5月22日民生銀行因未按相關規定聘任獨董受到上交所監管關注處理,與獨董相關的事件似乎從未離開過人們的視線。
自2001年8月證監會頒布《關于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獨董指導意見》),獨立董事逐漸成為上市公司管理層的標配。然而在此后該制度實行的16年里,從紅頂獨董到高校獨董再到專家獨董,從獨董不“懂”到獨董不“獨”,獨立董事制度暴露出來的缺陷被不少市場人士詬病。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為此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再升科技獨董范偉紅,瑞益榮融(北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東湖高新獨董馬傳剛,圍繞獨董制度所面臨的困境、上市公司獨董為何不“獨”、該如何解決這一難題等進行探討。
地位“尷尬”的獨董
獨立董事制度,是一項從國外引進的制度。然而自在國內建立以來,似乎一直面臨著窘境和尷尬。
“2005年10月,立法機關把獨董制度寫進了《公司法》。如果從證監會發布《獨董指導意見》算起,獨董制度已經走過了16年的歷程。”馬傳剛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然而,從獨董制度建立之日起,人們對其議論就不絕于耳,且幾乎所有與獨董有關聯的當事方,都對這一制度頗有微詞。
馬傳剛分析說,“一些上市公司認為獨董制度只是個工具,獨董只是湊湊數、簽簽字、領領錢;中小股東和市場人士認為獨董是個花瓶,中看不中用;監管機構也經常說,獨董未能做到勤勉盡責、誠實守信,‘獨立和‘董事做得不到位;很多獨董也常常抱怨,上市公司及大股東沒把他們當回事,得不到尊重,責任太重,權力太小。”
各關聯方的吐槽并非沒有根據。以獨立董事為例,今年3月13日成城股份因未按期披露2013年年度報告,證監會對其下發了行政處罰書,獨董鄭江明、姜明輝、艾勇等3人也被給予警告,并領到3萬元罰單。獨董艾勇申辯說,自己任職時間短,年度報告并非其所能控制,成城股份也尚未支付獨董報酬,從權利義務對等角度來說,其未享有權利,應減免責任義務。這種說辭似乎不是沒有道理,但證監會并未采納認可。
與以往在類似事件中獨董只受到警告等行政處罰不同,這次對獨董進行了罰款,獨董的責任認定在加強。事實上,今年以來,有關加強獨董監管的信號也頻頻出現。
5月22日,上交所對民生銀行在信息披露、規范運作等方面存在的違規行為下發了監管關注函。其中比較嚴重的是民生銀行沒有按照相關規定聘任獨董:其一,公司董事會由18名董事組成,按規定應聘任至少6名獨董,但實際獨董僅3名,且長期未能補充;其二,這3名獨董中有兩名任期超過6年,違反獨董任期年限規定。
在此之前的5月12日,深交所修訂了2011年以來實施的獨董備案辦法,進一步細化了獨立董事任職資格和獨立性的相關要求。這被不少市場人士解讀為監管層在獨董制度方面監管將趨嚴的信號。
更早之前的5月4日,上交所公告稱,旗濱集團獨董周金明在股份買賣方面存在違規事項,對其公開譴責,并通報湖南省政府,記入上市公司誠信檔案。
不過,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監管層對獨董制度缺陷的修補以及對違規公司和獨董的輕微處罰,很難從根本上阻止上市公司和獨董違規現象的發生。據相關統計,獨董違規主要表現為內幕交易、超限兼職、兼職不報和隱瞞不報等行為。
“任性”的獨董津貼,差距近2000倍
獨董的津貼一直被市場關注,也被認為是影響獨董積極性和獨立性的重要因素。范偉紅教授告訴記者:“獨董津貼很重要,津貼過高勢必影響獨立性,津貼過低又不能覆蓋履職成本,不符合市場規律。”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根據Wind資訊數據,對3115家上市公司2016年的獨董津貼進行了統計分析:這些公司總共支出獨董津貼7.85億元,平均每家公司支出津貼為25.21萬元;從單個公司的獨董津貼支出來看,中國平安支出394萬元,位居第一;從獨董人均津貼來看,分眾傳媒以69.24萬元位居第一。
總體分布來看,有2790家上市公司獨董津貼支出在10萬元~49.99萬元,獨董人均津貼在1萬元~10萬元的上市公司有2580家。
分行業來看,無論是每家公司獨董津貼支出,還是每家公司獨董人均津貼支出,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上市公司均位居前列。
在2016年報告期內,共有8923名獨董領取津貼(不包含0元)。如果不考慮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獨董情況,曾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鄭海泉在民生銀行所領取津貼為95萬元,位居A股獨董津貼第一名;大華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葉金福和上海匯石投資董事長王晉勇在利亞德所領取津貼僅為500元,墊底A股獨董津貼;最高獨董津貼是最低獨董津貼的1900倍。
根據《獨董指導意見》,“獨立董事原則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并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的職責”。《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統計發現,大多數的獨董在不超過5家上市公司任職,不過,在監管趨嚴的背景下,也有個別獨董違規兼職超過5家上市公司的,如上海立信會計學院教授邵瑞慶兼職6家公司獨董,包括西藏城投、東方航空、華域汽車、廣聚能源、凱眾股份和第一醫藥。
如果考慮一人兼職多家公司獨董情況,北京華明富龍財會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葛明從分眾傳媒和中國平安兩家公司領取津貼137.48萬元,位居A股獨董津貼第一名;中興財光華會計事務所丁小銀在*ST智慧(601519.SH)領取津貼為600元,最高獨董津貼是最低獨董津貼的2291倍。
在《獨董指導意見》中,對津貼有簡單規定,“上市公司應當給予獨董適當的津貼。津貼的標準應當由董事會制訂預案,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并在公司年報中進行披露。”
不過,有一些專家認為,這項規定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對于獨董的津貼問題缺乏強制性規范,而是交由公司自行處理;二是規定模糊,對于獨董津貼的支付形式、來源及標準等問題缺乏統一規定。”
獨董提名的“熟人機制”是禍根
獨董不“獨”被不少市場人士認為是獨董制度的缺陷。在范偉紅教授看來,除了津貼會影響獨董不“獨”外,獨董選任、獨董地位、獨董權威性和執業上的規范性等都與獨董的獨立性相關。
范偉紅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無論是盛極一時的官員獨董,抑或是高校獨董,還是專家獨董,都沒有改變提名上的熟人機制。盡管經過了董事會和股東大會的選聘表決程序,但根據‘由誰選任,對誰負責的選舉邏輯,獨董履職的獨立性還是會受到一定影響。人家控股股東或董事長請你來,你若把獨董做成‘對立董事,至少面子上會有顧慮。”
因此,范偉紅向監管層建言,“可將獨董歸于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管理,改選任制為委任制,按照行業地區建立獨董花名冊,由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委任并統一收取上市公司獨董費,這樣一來,一方面能強化獨董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另一方面,也能解放獨董的束縛和顧慮,讓獨董真正獨立履職。讓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統一獨董這一服務手段和服務途徑,加強對獨董的服務與監督也是順理成章的。”
高明華也認為,當前對獨董制度的修修補補起不到多大作用,“長效的解決辦法是建立董事會備忘錄制度。該制度是把董事會集體責任轉化為個人責任的制度,即每次董事會上,都要求董秘把每位董事的發言、投票、會前與其他董事和相關者(如股東、員工等)的溝通、是否做了可行性報告等行為都記錄在案,并經每位董事核實無誤后簽字。這樣,一旦決策出現錯誤或失誤,可以判定誰負責任以及責任大小。需要注意的是,對責任的處罰力度要足夠大,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三重責任,要使每位董事認識到違規、犯錯的成本很大,不值得。”
他還呼吁,“獨董要更多地來自經理人市場,市場要透明,這樣的市場具有信號傳導和懲戒作用。減少從退休公務員、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學者中聘請獨董,因為他們不能受經理人市場約束,干不好退出,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沒有任何影響。職業經理人擔任獨董,做好了有利于他們的職業發展,身價上漲,而做不好則不利于他們的職業發展,身價會大跌,甚至不得不退出經理人市場。”
相對獨董的制度缺陷,馬傳剛更側重認為是當前監管執行不到位造成了獨董制度的窘境,“目前缺少的不是規則,而是規則的執行。證監會、交易所、上市公司協會制定的制度、規則、辦法已經不少了,翻一翻這些文件,就會發現,關于獨董的任職、履職、權利、義務、責任、問責都有詳細的規定,只是在執行的過程中走了樣,有些事沒人管,有些事管得不到位,這樣一來就逐漸導致了獨董的行為異化。因此,監管部門要把監管做實,督促獨董履行好忠實和勤勉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