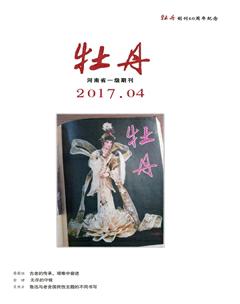無盡的守候
金珺
第十屆桃李杯舞蹈大賽獨舞類金獎作品《徽娘》以古徽州女子的生活狀態為創作背景,以安徽花鼓燈為元素,講述了一個徽州女子一生守候的故事。
一、作品《徽娘》的形式與內容
在現如今日新月異的舞蹈作品中,以安徽花鼓燈為素材、以安徽人物形象為背景的作品并不多。在第十屆“桃李杯”舞蹈大賽中,獨舞《徽娘》算代表性的作品。《徽娘》以安徽花鼓燈為素材,用舞蹈的形式呈現了安徽古民居女性的生活境遇與內心世界。它講述的是一位古徽州女性在家中對丈夫的守候與盼望,六分鐘的時間內,敘述了這位傳統徽州女性的心路歷程與情感變化。整個作品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一位獨守空房的女子身著徽州特色的服裝,手捏絲巾一步一步地走來,時而快,時而慢。眼睛望著遠處,腳步緊追。但又突然停住,女子面容惆悵,不舍地往回走了。手里的絲巾纏在手腕上,她回身抱著手臂晃動,像是在哄自己的孩子睡覺。但又停住,慢慢回頭,依然望向遠方,她還是沒看到什么,眼神難免失落。接下來的一系列動作,充滿了她對遠方的一種思念,可能她的丈夫就在遠方。
第二部分:音樂漸漸歡快起來,這位女子的眼里充滿了期望,也許是聽到了一個消息,可能自己的丈夫就要回來了。所有的心理活動都表現在了臉上,在這一部分中,安徽花鼓燈“溜得起、剎得住”的特色被很好地融入進來,充分體現了這位女子很想趕緊見到丈夫卻又不得不矜持住的糾結心理。害羞、竊喜,像是自己剛出嫁時的樣子。靈巧的腳下步伐巧妙地體現了她的心情。手上的絲巾隨著身體擺動,一系列的動作將這個舞蹈提到了一個小高潮。最后,這位女子將絲巾拋了出去,跑向了遠處。
第三部分:音樂開始變得沉重起來,女子的表情也突然凝重了,慢慢回頭望向自己的絲巾。突然,她快速地跑了過去,拿起絲巾,沖向舞臺前方,雙手推開的動作也許是推開了門。緊接著,痛苦、絕望的表情在她的臉上一一呈現。什么造成了她突然的情感轉變?一定是一個噩耗,也許是她的丈夫在外去世,也許是她的丈夫在外永遠不回來了。悲痛的心情爆發出來,緊接著一系列的旋轉、碎步以及大動作都體現了她的心情。但是,一段悲傷過后,她仿佛想到了什么,收拾了自己的心情,繼續凝望,也許望不到頭,但是這也許是一種精神支柱。舞蹈的結尾是這位女子和開頭大致一樣地走步,一步一步,循規蹈矩,是守候,也是希望。
二、徽州女子的生活狀態以及與作品《徽娘》的聯系
徽州,簡稱“徽”,古稱歙州,又名新安,為浙江省最早雛形之一浙江西道的組成部分,也是清初江南省分割后安徽省之“徽”的命名來源。徽州處于黃山與天目山脈間,山水人文系之,粉墻黛瓦的江南徽派建筑與之相得益彰,素有“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之美稱。
而在這樣以“商”為生的徽州,女性都干什么呢?徽州人經商都是男性,而女性的工作則是在家中操持家務,等待丈夫歸來。古徽州思想封閉,不允許女子外出,不允許她們拋頭露面,她們能做的就是“等待”,等著丈夫回家,這一等也許就是一輩子。而獨舞《徽娘》的創作思路完全符合徽州女性的生活狀態,無論多大的情感轉變,也離不開這個家。《徽娘》第一部分中,女子一步一步地慢慢走來,也許這正是她的生活寫照,日復一日的等待,無非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走到門邊,望著遠處,也望不到自己的丈夫,女子只有無奈地回頭。在房中懷抱自己的孩子,也許這是她們唯一的生活樂趣和心理寄托。漫長的等待中也會有一絲絲微小的驚喜,也許是丈夫歸期將至,這一天,她盼了很久,已經控制不了內心的喜悅,從作品的碎小急促的腳步上就能看出,而這腳底功夫也正是“安徽花鼓燈”的要點所在。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古徽州女子以小腳為榮,大多數女子都從小纏足,“三寸金蓮”是徽州女子視為榮譽的象征。而人們所了解的“安徽花鼓燈”,也有這個元素,最一開始的“安徽花鼓燈”不準女子跳,只能由男子演繹,而且時常需穿著“三寸金蓮”,發展到后來,有了男子的“跳蘭花”。現如今,“安徽花鼓燈”多為女子演繹,在演繹的過程中,大多數腳底動作都是半腳掌著地,給觀眾的視覺感受正如當初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被徽州女子視為不能破的規矩,但是也在無形中束縛了女子,不能大步走路,不能快走,必須循規蹈矩,步步驚心。《徽娘》這個作品的第二部分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雖然很喜悅,但是也不能將矜持拋到腦后。徽州女子含蓄內斂,在《徽娘》這個作品中,所有的大動作里也不失它的“小范兒”。第三部分里,這位女子的情感轉折也來源于她的絕望,一直盼望著歸來的丈夫沒能回來,也許還要很久,也許再也盼不回來。痛苦充斥著內心,絕望在臉上展露無遺。不停地旋轉表達了她無盡的愁緒,急促的碎步代表了她不愿相信的事實已展現在她眼前。可是,這已成事實,無法改變。一段悲傷的大動作之后,不停的旋轉突然停止,好似這位女子突然領悟了什么,身為一個徽州女人,丈夫沒能回來,自己也得守住這個家,哪怕沒有盡頭地守候,直到自己油盡燈枯,老死家中。這也許就是徽州女子的一生,只用兩個字概括,那就是“守候”。
三、作品《徽娘》的服裝道具與燈光以及對人物心理的詮釋
《徽娘》這個作品在服裝選取和燈光上也恰到好處。演員身著具有徽州特色的紅色衣衫,保守、精致,正體現了徽州女人的生活狀態。紅色一般用作重要場合,而女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莫過于出嫁了。編導用紅色作為服裝色調,也許表達的是女子希望每日等待丈夫歸來時都能看見她最美的時刻,突出了徽州女子日夜盼望丈夫歸來的心,更加突出了徽州女子視夫為命的思想。作品中,編導運用了繡花絲巾作為道具,絲巾是徽州女人的生活用品,不同時期代表的含義也稍微有些不同,也許代表了少女時遮羞的手帕,也許代表了出嫁時的蓋頭,也許代表了照顧孩子時的手巾,也許在最后代表了她對丈夫的心理寄托。
在觀看這個作品時,燈光營造了很多心境。伴隨著水滴聲,開頭運用了白色的束光,表達了在漆黑夜里徽娘無盡的等待。第一部分,隨著音樂的進行,白色束光慢慢變換成深藍色的場光,無疑表現了徽娘內心的孤寂與失落。在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的銜接處,燈光變紅,隨著音樂的進行,燈光越來越強,變成了綠色的場光,綠色代表希望,也正好體現出了徽娘的內心變換。在第二部分到第三部分的銜接處,燈光慢慢變暗,預示著噩耗的來臨。到了第三部分,燈光變成深藍色,仿佛敘述了徽娘內心的沉重與絕望。第三部分后半段,音樂變緩,黃色的束光配合深藍色的場光,也在告訴觀眾,這位徽州女子還在繼續等候,哪怕什么也等不來。最后,場光熄滅,束光漸漸淡去。
四、結語
在短短六分鐘之內,編導從女性視角帶領觀眾領略了徽州的情懷。雖然當今社會中,這樣的社會現象已不存在,但是不難看出,那個時候雖然思想守舊,女子行為舉止被束縛,但是恪守婦道、視夫為天的徽州女子不僅僅只有無奈與等候,還有她們對丈夫的忠貞不渝。這樣一來,徽州女子堅定不移的品格更值得人們稱贊。一個好作品的背后必定蘊藏著它的文化內涵,《徽娘》這個以人物為主體、以徽州情懷為創作背景的作品完全體現了這一觀點,值得人們細細咀嚼,慢慢品味。
(廣西藝術學院舞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