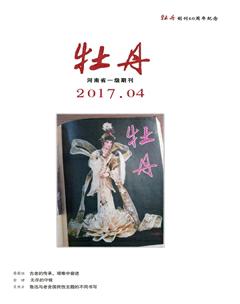伊瑟爾“空白理論”在《寒冬夜行人》中的運用
19世紀以來,文本中不斷增加的空白成為西方文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也是現代和當代文學作品中的顯著特征。現代文學研究中讀者的地位日趨重要。德國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伊瑟爾指出了“空白”與作品意義的關系,讀者在閱讀中以想象填補作者有意設置的“空缺”。他的文學理論提高了讀者的地位,把閱讀活動看作文學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以其多重交織的文學主題和嫻熟的后現代藝術手法著稱。本文將以伊瑟爾的“空白”理論解讀卡爾維諾的小說《寒冬夜行人》,指出該小說在語言符號層、藝術形象層和內在意蘊層方面存在的空白,并分析作家在設置空白與填補空白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本意義。
一、理論概況
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寫道:“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注重作者,聚焦文本以及轉向讀者。其中,讀者的地位向來最低,而實際上,沒有讀者就沒有文學作品——它們是僅在閱讀實踐中才能被實現的意義過程。”對于接受理論來說,閱讀始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只有讀者才能將文學作品從一般存在物中解脫出來。閱讀不是一往直前的線性運動,而是反復回蕩、前后修正的動態運動。
在西方,最先在文學的接受理論中提出“空白”一詞的是德國接受美學的創始人之一沃爾夫岡·伊瑟爾,他在代表作《文本的召喚結構》(1970)一文中明確使用了“空白”一詞,指出它是文本召喚讀者閱讀的結構機制,并深入研究了空白與作品意義的關系。在《閱讀活動》中,他更詳細地闡釋了關于空白的接受理論觀點。在他看來,文學研究應當充分重視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文學文本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圖示化”的框架,這個框架在各個層面上都有許多空白,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去填補與充實。正是這些空白,把讀者“牽涉到事件中,以提供未言部分的意義。”所謂“空白”,就是指文本中未實寫出來的或未明確寫出來的部分,它們是文本中已實寫出的部分向讀者所暗示或提示的東西,需要讀者根據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在伊瑟爾看來,閱讀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它使讀者產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識,促使讀者更加批判地觀察自己的種種觀念。閱讀仿佛一個放大鏡,人們閱讀書本,其實從中看到的是自己。
二、文本分析
在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中,空白理論的運用主要分為三大方面:語言符號層的空白、藝術形象層的空白和內在意蘊層的空白。
(一)語言符號層的空白
小說中的空白首先體現在語言符號層,展現為一種藝術形式上的表現技巧和手法。在故事情節的設置上,卡爾維諾采取了元小說的形式,在小說中套入小說,在男主人公閱讀十部殘篇的過程中,讀者也在同步閱讀十個故事并閱讀男主人公的生活經歷,這種雙線交織的寫作手法使得小說充滿了多元化和可變性,小說節奏時而放緩時而加快。作者以各種緣由打斷男讀者的連貫閱讀,通過他對下文的追尋,巧妙地將十部毫無關聯的各類小說連綴在一起,以基礎文本的空白打破真實讀者的期待視野,引出一系列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減少了小說中相對平淡的部分,使得整部作品波瀾起伏,十分緊湊。作家常常在趣味盎然之際驟然停筆,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好奇心。由此便開始了讀者和文本的交流與互動,讀者不再是源源不斷地接受作者賦予文本的信息和觀念的被動角色;他們同文中的男讀者一樣,因為手中的這本《寒冬夜行人》卷入了整個漫長而多變的閱讀活動中。
其次是在人稱和視角的變換上,小說就是以第二人稱——男讀者“你”來開篇,持續到第七章時中途轉變為女讀者“你”,在二人發生關系后又轉變為“你們”,最后復又回到了男讀者“你”;第八章整章以作家西拉·弗蘭奈里日記的形式用第一人稱講述,幾個主要角色在此相互交織在一起。內聚焦寫作方式的優勢在于,可以最大程度地呈現人物的內心活動,增加真實感和親切感。讀者隨著這種內聚焦的敘述方式抽絲剝繭,層層遞進,不斷地發現空白又填補空白,在這一過程中,小說里關于整個寫作、翻譯、印刷、出版、閱讀的流程和思考在作者筆下鋪展開來。
(二)藝術形象層的空白
《寒冬夜行人》中藝術形象層的空白表現在兩個方面:人物形象的空白和環境描寫的空白。在人物形象的設置方面,從男讀者的讀書活動切入正題,對他的年齡、外貌、職業等身份和特質都采取了模糊處理;對于女讀者,也只是從行為方式和家居擺設上對她的脾氣秉性略窺一二。作者在文中明確寫道:“女讀者,你究竟是什么模樣呢……本書一直十分注意讓閱讀本書的讀者能夠進入角色并與小說中的‘讀者等同起來,因此未曾給他起個名字。因為,那樣做會把他與第三人稱自動等同起來,把他變成一個人物。而且本書還讓小說中的男讀者處于抽象狀態,只是個代詞,可以給他附加各種定語,令他完成各動作。”男讀者形象的空白便于調動讀者的想象力和創作性,把自身代入到故事中去,讀者與文本的互動性得到了加強。
在十個斷篇中情況也是如此。它們無一例外地都是以第一人稱“我”講述故事,讀者只能從敘述中偶得關于主人公的職業、身份、性格方面的一絲信息,故事強調的是文本特質——正如之前柳德米拉所言——例如讓人讀來清晰的小說、能感覺到即將到來的事件的小說、只管敘事的小說、令人焦慮不安的小說和似乎蒙上外罩的小說等。印象和思想成為小說的表達重點,主人公退居其次,只需擔任功能上的作用,情節連貫性被打破。這里的空白讓讀者的關注點從典型人物轉移到戲劇性沖突和文本意義上來。
在環境描寫方面,男女讀者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并沒有明確交代,似乎被默認為與當代讀者相當,自然環境就更不必說;在故事斷篇中,每一篇的背景都很模糊,時代不明。例如,第一篇《寒冬夜行人》中不乏這樣的敘述——“故事發生在某火車站上”,卻沒有對火車站的具體描寫,“我就是小說的主人公……或者說,小說的主人公名字叫‘我,除此之外,你對這個人物什么也不知道;對這個車站也是如此,你只知道它叫‘車站,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處于模糊之中,像被一團云霧籠罩著一樣,直到結尾處才云撥霧散,知曉了主人公有特殊身份,但仍然對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一無所知,這就挑起了讀者繼續閱讀的興致,得到如同在閱讀偵探小說時的快感。在《從陡壁懸崖上探出身軀》里,主要地點是小海灘、礦物般的監獄高塔和安裝了無數儀器的天文臺,整個故事里彌漫著壓抑、潮腐的氣息。這種環境描寫為次要角色的特務身份作了鋪墊,預示著下文情節的急轉直下。
(三)內在意蘊層的空白
內在意蘊是整個文學作品意義的關鍵所在,作品中語言符號層的空白和藝術形象層的空白最終構成了內在意蘊的廣闊空間,在讀者的參與下實現作品的意義。王瑞在《伊瑟爾“空白理論”在小說藝術中的運用》中談道,凡是成功的藝術作品,其內在意蘊總是多維的、不定的,能夠給讀者留下一個巨大的想象和思索的空間。《寒冬夜行人》并沒有單一明確的主旨,小說中男讀者閱讀《寒冬夜行人》卻被出版商的印刷錯誤打斷,企圖尋找小說下文,在尋找的過程中與女讀者相遇,最后經歷一系列追尋與歷險,和女讀者喜結連理。作者并沒有單獨講述尋書或求愛,而是借各種人物之口表達了關于讀書、寫作、成書的不同觀點與思考。例如,在《寒冬夜行人》中揭示出作家的寫作心理;第五章探討作者與作品間的關系;第七章討論隱含作者、隱含讀者和敘述聲音的可靠與否;第八章談到零度寫作、非個性化、潛在的作品和理想讀者;第十一章以七個讀者的自敘展示了七種毫不相同的閱讀方式。在一部只有二百來頁的小說中、在一個大故事里套入十個小故事,探討了讀者觀、作者觀、閱讀觀、翻譯觀、國家對文學的控制、造書與偽造等多個話題,卡爾維諾在小說中體現出來的后現代寫作手法(元小說、戲仿、拼貼等)也歷來被讀者和學者津津樂道。內在意蘊的空白使得整部作品的解讀具有多元性,這本書也成為卡爾維諾的代表作。
作者在很多小故事里也運用了空白理論,指出了小說本身的虛構性。例如在《寒冬夜行人》中,頻頻出現跳脫性的句子:“蒸汽機活塞發出的聲響掩蓋了你打開書本的聲音,一股白色的蒸汽部分遮蓋了小說的第一章第一段”;“這本小說的文字模糊……霧氣罩住了書頁”;“書中的文字描述的卻是一種沒有明確概念的時空,講述的是既無具體人物又無特色的事件。當心啊!這是吸引你的辦法,一步步引你上鉤你還不知道呢,這就是圈套。”在《不怕寒風,不顧眩暈》中,情況也是如此,“也許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橋梁。故事在展開過程中不斷描寫各種各樣的消息、感覺和心緒,為各種事件制造一種背景并在這個背景上開拓出一條人生道路”。《一條條相互連接的線》的開頭是這樣的:“這本書應該給予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聽見電話機鈴響時的那種感覺。”這種在小說中指出其虛構性的句子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作者從單純的敘事跨入到探討小說創作的本體的層面中,增強了小說的內在意蘊和豐富性。
不僅如此,卡爾維諾還在文中明確提出了空白的重要性。“我覺得書中寫的東西不應該就是一切,不應該實實在在,應該有點捉摸不定,字里行間還應有某種東西,我也說不清楚是什么東西……”,“小說中未言明的東西比言明的東西更加豐富,只有讓言明的東西發生折射,才能想象出那些未言明的東西。”這些都與伊瑟爾的空白理論不謀而合。在小說的結尾處,作家借一位讀者之口說道,一切小說的最終含義都包括繼續的生命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但并不是每一篇小說都必須要有開頭和結尾。在內容上,每本小說都有相近的意涵,但在外在形式的表現上可謂多姿多彩。在小說的發展中可以插入形形色色的含義和信息,包含各種各樣的觀點與思考,不必拘于形式,也沒有固定的標準,卡爾維諾認為,這樣的小說才是韻味豐富、值得再三重讀的。
三、結語
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作為后現代小說的經典之作,包含多重文學主題和精妙的藝術手法,歷來被研究者和讀者以不盡相同的視角進行解讀。小說中的諸多空白之處,在最大容量地展現了后現代生存語境的光怪陸離之外,還調動了讀者的參與性和閱讀興趣,為文本留下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增加了作品的容量,富含言外之意,成功實現了讀者與本文的互動與交流。本文以伊瑟爾的“空白”理論對它進行解讀,在語言符號層、藝術形象層和內在意蘊層方面發掘表層之下的深層含義,寫作之樂與閱讀之愉悅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文學”的內涵也隨之擴充,不斷向前發展。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
作者簡介:陳茜(1992–),女,河北秦皇島人,文學碩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