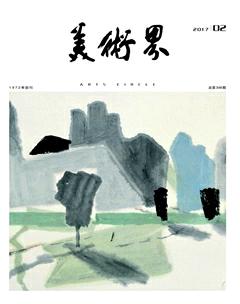當代工筆畫的品評標準芻議
王海濱
工筆畫的品評標準要放在中國畫的改良和革新的背景下討論。上世紀以來,改良和革新中國畫的思潮,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背景下的產物,文化的自卑感和追求自強的欲望是美術界提出改良和革新的根本動因,“中西融合”“推陳出新”構成19世紀以來的中國畫發展史并深刻左右著藝術家的文化心理,影響至今。新世紀來臨,一個逐漸強盛的中國,它的文化和藝術如何自處,我們怎樣看待自己的傳統,這是每一位藝術家應該考慮的問題。中國畫應該堂堂正正、坦坦蕩蕩地展示中國人文化上的自信,每一位藝術工作者都應該擔負這樣的責任。
宏大的敘事總是需要具體實踐的支撐,任何一個藝術門類,任何一個畫種面貌的些微改變,都會自下而上,由具體到宏觀地影響藝術史的演進方向。中國工筆畫身在其中,并且因為與西方寫實主義的淵源最為緊密,表現也就更為突出,所以,中國工筆畫的品評標準直接影響了它的發展方向,值得討論。
首先,工筆畫的品評標準不應該是依據西方藝術標準展開的,也就是說,不是一廂情愿的與西方同軌跟進,不是“他看我”,而是“我看我”。
余英時先生在《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一文中對各國民族主義思潮作了深入的思考之后,特別提到一種普遍存在的“羨憎交織”心理,這種心理在近代中國美術史中影響深遠。誠然,中國工筆畫的面貌,并不是以單純守護傳統或者一味西化革新的姿態出現,但我們選擇的視角,絕不應該源于他者的邏輯范式,不應該是一種尊崇并迎合西歐中心主義的,“世界性”的歷史發展模式,不應該是以犧牲自我面貌而獲得“融合”的委曲求全。
這些現象的產生有一個現實的基礎,素描教學對中國工筆畫的影響。現代美術學院教育的基礎全部源于素描,西方古典寫實風格的素描作為所有專業學生統一的基本功訓練課程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一直在今天,“寫實素描是一切繪畫的基礎”仍然是中國畫教學的基本理念。反觀西方,隨著寫實主義畫風分化,素描也失去一統天下的地位,“寫實”也并不是唯一標準,拿著這一標準來要求中國工筆畫就更顯偏頗。當然,由于工筆畫自身天然的寫實成分,由寫實素描入手未嘗不可,但如果止于“寫實”而喪失了原有的“神、妙、逸、能”的品評方式以及意境、品格等批評觀念,不僅喪失了對工筆畫的審美能力,連正確的解讀都難以為繼。中西融合、事盡兩極固然鼓舞人心,但陷入“唯寫實”的泥沼卻難以脫身。郎紹君先生在《談當代中國工筆畫的十大問題》中講到中國工筆畫的十個弊端,我認為“一味制作、無意義的變形、想象力貧弱、格調趨俗”等問題都與沒能正確認識素描教學在工筆畫創作中的作用有關。拘泥于“寫實”和準確不準確,就會在肌理、效果上用猛力而一味制作,就會為了變形而變形,就會把話說盡說滿而喪失韻味趨向柔靡、香艷、光膩。這反過來告訴我們,素描是一種科學的研究對象的方法,但要學到家,理解透,然后才能自由地運用它,不被束縛住。這同時說明工筆畫對待“寫實”、對待素描的角度和態度,不是“素描”看我,而是“我”看素描,“我”用素描。
其次,工筆畫的品評標準不能脫離傳統審美另起爐灶。
中國畫從古至今,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基本的內核,這種內核,同西方繪畫體系全然不同。表現在審美上,其范圍涉及到文化理念和倫理道德,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內涵和人文意蘊。它以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為文化背景,蘊含了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形成獨有的審美精神。在我們的傳統中,最早把“道”“氣”“象”作為中國畫的基本審美標準,古代的畫論都是圍繞著幾個基本的審美概念展開闡述的。并且,我們傳統的審美中,從沒有把藝術、把作品當作專門的學科去研究,而是把它同“人”緊緊聯系成一個整體,藝術和藝術家的生命歷程緊緊貼合在一起。藝術是什么?藝術就是人的生活,是人日常行為中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把藝術作為修身養性的一部分。可以說,傳統的審美,既有外在標準的共性,又有與不同個體內在契合的個性。所以,我們品評前人的藝術作品,要看技法、看線條、看筆墨,更要看品味、看心緒、看精神境界。
以《韓熙載夜宴圖》為例,在西方寫實性還沒有介入,在畫家們還不懂得西方解剖學、焦點透視的情況下,其人物造型是成功的,這個成功,既有人物造型的準確和統一性,又有韓熙載這個人物應有的意味在里面,還有畫家自己的精神關照在里面。傳統的“寫真”與意象已經使形象手段達到了意識層面的高度,在對人物的“寫真”式取舍以及細節的精準描繪中體現出中國文化獨有的品象。

需要我們思考的是,現代工筆畫的審美,是因為缺乏西方寫實性而不能達到更高級廣闊的階段,還是因為西方寫實性的介入斷送了其再生和拓展內涵的可能?現實實踐中,不和諧的現象不少,不少大學一年級二年級的學生,寫實素描能力很好,但一涉及到創作就難以為繼,不少學生把寫生的模特生硬地畫在畫面上以后,靠在環境中反復渲染某種顏色,造成一種統一的色調來營造“意境”,或者把人物刻意置身于帶有典型西畫意味的環境中,認為這樣很有“情調”。傳統繪畫中,人物造型與意味素來是統一的、同步的,今天又怎么會硬生生割裂,成了不相干的事情?
解決這種不和諧,還要在傳統中獲得滋養。現代工筆畫的審美,必然產生于傳統完善的文化系統和對事物的完美認知,法度森嚴又意出象外,嚴謹又痛快淋漓。
以色彩為例,“惡紫奪朱”“五色令人目盲”等成語中的色,都不是色相上的色,而是中國人對色彩的文化認識。一個“青”字,可以是青綠山水中的石綠的色相,也可以是“垂青、青絲”中的觀念,“金碧輝煌”不但表明了色相,還包含了色澤。再分析“墨分五色”這個中國獨有的觀念,是中國畫用色的一個規范,墨能代表一切色彩來表達物象,它的使用方法超越了一切水色和礦物質色。與此同時,色彩承接的感情也是鮮活生動的。“寒山一帶傷心碧”“鶯嘴叼花紅溜,燕尾分波綠皺”,這些色彩是活動的,它有無窮的轉折變幻。傳統繪畫把色彩視為文化標準共識,在對色彩的運用過程中都會涉及到中國文化對色彩的判定及其文化意味。懂了這些,我們怎么還會照抄模特的顏色而不知所措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留在遠古的田園牧歌止步不前,我們需要往下進行的,是把自己身處時代的精神內涵歸納、概括,找到新的承載方式,以適合的題材加以表達,從而達到新的文化高度。
最后,工筆畫的品評應該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
回顧歷史,工筆畫因其特有的寫實特性而具備了“記錄”功能,它成為歷朝歷代研究社會現實的重要依據。大到歷史事件,小到服裝服飾,都能在工筆畫中找到依據,亦能看到作者對現實事件的態度。歷史上,《步輦圖》《文姬歸漢圖》等都是此中典范。但近時期以來,畫家過于關注自我內心世界,反映小事件、小環境、小情趣,作品中看不到畫家從人生體驗和獨立思考中得到的認知,缺乏真正的思考,缺乏表達的深度,缺乏對社會現實的真切關照,人云亦云,鸚鵡學舌的作品暴露出畫家自我反省、批判意識的不足。
“判斷是一件藝術作品成功的開始”不關注人生與社會問題,不關心人的命運特別是普通人的命運,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意識,自然影響了工筆畫精神的深度。藝術家應該沿續對人生、對社會負有道義責任的傳統,藝術創作呼吁與現實緊密相連,需要畫家獨立地對人生、社會、自然表達自己的看法,要求畫家具有獨立思考與感悟人生、社會的思想,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揚善伐惡,醒世警世,從而增加精神深度,產生有分量的作品。

王海濱
河北任丘人。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畫系副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畫創作與理論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工筆畫學會理事、北京市海淀區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作品參加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美展;第五、七、八屆全國工筆畫展并獲銀獎、優秀獎、特邀作品參展等;第三、四、五屆全國青年美展,并獲優秀獎;第三、四屆北京國際雙年展等國家級展覽40余次;參加在中國美術館、中華藝術宮、今日美術館、養墨堂美術館、炎黃藝術館舉辦的學術展覽60余次。
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國家博物館、中央美術學院、中央軍委大樓、中央辦公廳等機構收藏,作品《桐駿圖》作為國禮由原政協主席賈慶林贈送秘魯總統并永久收藏。
2012年11月申報并獲批了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