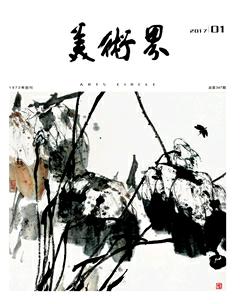空的空間:之中,之外
周文翰

黨震的“空間”系列作品有種特別的視覺效應“明晰之恍惚”。畫中立方建筑構形的確然性與通道的多向性并存,畫面中建筑表皮污跡暗示人為活動的長期性與畫面某一截面的豐富肌理引發的即時觀看的時間交錯,形成微妙的“實中虛”“斷處續”的“空的在場性”,一種“不在的在”。
由此想到戲劇家彼得·布魯克早前對戲劇的極簡定義:選取任何一個空間,稱它為空蕩的舞臺。一個人在別人的注視之下走過這個空間,這就足以構成一幕“劇場行為”了。那么,一張為觀者矚目的繪畫,可否以及如何“成為劇場”?
初看這一系列作品具有攝影的紀實性,的確,黨震是根據自己拍攝的一系列建筑物的照片作為“現實模板”,然后再進行重構形成基本的空間布局,不同的建筑塊面組成結構性很強的整體,主要建筑物都用毫不猶豫的水平、垂直、傾斜的線條標明,某些局部他仍然手繪勾勒點染,另一些則直接使用兩種不同的拼貼——來自對墨、水、紙與大理石等特殊質地的綜合反應的實驗成果構成:一類是欄桿、扶手之類平直的建筑邊沿或者延伸物,另一類具有非人為出來的自然流溢的肌理和意象,功能是構成某一建筑的某個側面,可稱之為“拼貼截面”。“拼貼截面”和手繪部分的重組在纖薄的宣紙上不引人注目的實現,而且他還常在“拼貼截面”上用墨線、墨漬、飛白在精細的流溢性肌理中點染、強化三兩處的墨跡,退一步,可視作可能的污垢、破損、老化之處,某種可直觀的性狀。
這些作品的戲劇性不僅僅在于不同維度,不同建筑表皮——截面的重組,還有銳利強硬的“建筑框架”與之上緊貼著的截面那種表現性、虛構性的“意象情態”形成的張力。后者具有綜合性的視覺意象,既有非手繪的細致肌理,同時某些部分以及手繪的點染又具有表現主義乃至抽象的意象,充分顯現出水墨這種特殊媒材——語言的特性,并使得此“截面”身兼平面結構和微觀形象的雙重功能。








相對都市建筑叢林構成的冷硬感、堅實感,這些“截面—結構—意象”,似乎在不斷溢出自己所在的那個平面,向其他的空間浸潤、擴張,形成詩意的、動態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說,屬于繪畫的“寫意”的部分。
黨震攝取的往往是“通道性場所”,出現路、臺階、窗戶、玻璃等這些可供穿越、透視、反射的“路徑”和“窗口”,一個人類必經但又具有臨時性的過渡場所。其中一些作品類似清場后的“空的劇場”,路面上的痕跡顯示著人們曾經的活動,多向的路徑暗示多重的可能性,拼貼截面則來自人們的視覺發現乃至臆想和眼睛的隨機、即時矚目和游移,這與那些一目了然的固態建筑結構構成對照,而觀者的視線既可能被立方實體囚禁、阻礙,也可以借助那些表現性的“截面—結構—意象”逃逸。
手繪和拼貼的多重結構——截面組合、拼貼截面的多義性以及他選擇的“通道性場所”本身的多向性,使得他的繪畫的視覺效應不僅向縱深發展,同時也在多個方向、截面上多向度延伸和流溢。或者說,他在建立整體的空間結構的同時又用大面積的流溢性截面及其肌理效果“侵蝕”和“瓦解”了縱深的“深度幻覺”。
同系列的部分作品出現了人物,諸如男人凝視游泳池中的女人,一個女人坐在餐桌邊進行午后遐想,她們被塑造為毫無個性面目的“某一類人”,而出現的玻璃鏡面則構成一個張開的,但是充滿虛幻感的“反射—反映”的中介物,造成某一自我審視和懷疑的距離,使得這一系列作品在貌似穩固的場所中顯露出迷失的可能性,更何況他們身邊、腳下的“拼貼平面”上色彩、意向還在沿墻而來,張牙舞爪,說不清楚是莫名的危險、誘惑還是光怪陸離的生存環境的象征。
這是黨震開辟的新場域——他之前的人物繪畫建構的“寓言劇場”無論在室外還是室內,都是主觀強力虛構的、超現實的人物與景觀的戲劇化組合場景,風景繪畫則對準遠離城市的鄉村、山水,而在新作中,他直面自己身處的都市這個無比庸常的場所,用手繪和半人工控制的媒材實驗品進行拼貼來探索觀念性繪畫的新可能。為此,他似乎有意壓抑自己的身體感性和技能而代之以更為觀念化、技術化的操作。我想,對他而言,這并不意味著感性力量的退卻,而是化合為新的形態進行衍生、集聚、傳導,以備新的噴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