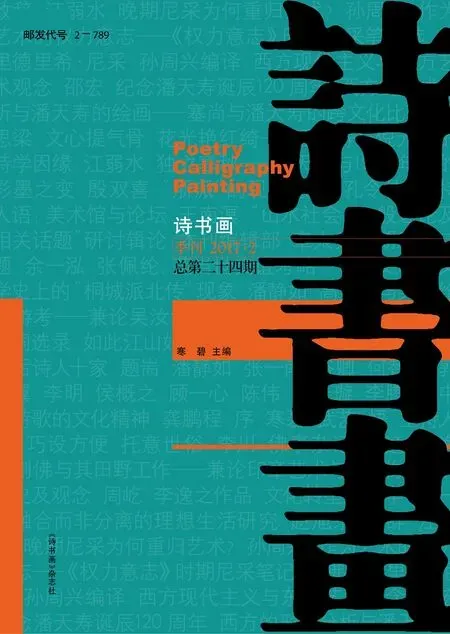西方現代主義與東方藝術觀念
邵 宏
西方現代主義與東方藝術觀念
邵 宏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西方現代藝術,是全球文明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國際化特征的文化事件。一般認為,西方現代藝術的起始點是一八八○年。①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trans. Charles Marriot, new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1964, p. 291.彼時,隨著被批評家喬治·里維埃[Georges Rivière]稱作“為色調而表現題材,而不是為題材本身”、②G. Rivière, "L’exposition des impressionnistes," in L’Impressionniste, 6, 14, 21 april 1877.且以感覺論[sensationalism]為要旨的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出現危機,法國藝術界顯露出了對形式原理[doctrine of form]的需要和朝向抽象藝術的趨勢。塞尚、點彩派畫家修拉以及象征派畫家高更都被視為法國抽象藝術的先驅。而在現代主義[modernism]觀念形成之初,我們見到一些作家的身影閃現其間。一八九○年法國畫家兼作家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 (1870-1943)題為“界定新傳統主義”[De finition of Neo-Traditionalism]的文章,是用下面一段名言開始的:
要記住,一幅畫在其是一匹戰馬、一個裸女、或某件軼事之前,本質上就是以確定的秩序鋪滿不同色彩的一個平展的表面。③Se rappeler qu’un tableau—avant d’être un cheval de bataille, une femme nue, ou une quelconque anecdote—est essentiellement une surface plane recouverte de couleurs en un certain ordre assemblées. 英譯文見From the Classicists to the Impressionists :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selected and edited by Elizabeth Gilmore Holt, New Haven &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09.
這種對畫面設計意識的強調,正是現代主義的意旨之一;其中對新的形式原理的需求與對再現性藝術的態度轉變,才是西方現代藝術中的革命性變化。然而,德尼的這種革命性態度,在中國則有著千馀年的觀念形態依據。同德尼身份相似的中國作家兼畫家蘇東坡[1036-1101],早于德尼八百多年便探討過這一問題:④滕固《滕固美術史論著三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17-226頁。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之一)
不過,其中的差異在于:德尼是從寫實轉向設計進而使之成為一種趣味;蘇東坡則是從寫實直接轉向文學性(詩意)趣味。⑤有關西方藝術批評中“設計與趣味”的關系,參見邵宏《設計的藝術史語境》,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6年,第87-103頁;有關中國藝術中“詩意進入畫面”的問題,參見邵宏“溫柔敦厚 潔靜精微—由讀嚴善錞的畫而想到的詩畫關系”,《詩書畫》,2016年第1期,總第19期。在西方這場實際上主要由作家們所倡導的現代主義中,東方尤其是中國傳統藝術觀念對之發生過的影響,則是本文的興趣所在。
一
初時,現代藝術中的觀念轉變是在德語和法語作家與藝術家之間進行的。旅居意大利二十年的德國畫家漢斯·馮·馬雷斯[Hans von Marées](1837-1887),最早受到造型欲望[desire for form]的激勵而重新發現了視覺的標準。⑥馬雷斯的格言是:“人們所需的唯有學會觀看”[all you need is learning to see]。他實際上左右了在意大利結識的兩位同胞菲德勒[Conrad Fiedler](1841-1895)和希爾德布蘭德[Adolf von Hildebrand](1847-1921)后來所導致的趣味發展,并一道發起了后來廣為流行直到今天的形式主義[formalism]。而馮·馬雷斯和菲德勒所提倡的所謂純粹可視性[reine Sichtbarkeit],我們能從雕塑家兼作家希爾德布蘭德的那部廣受贊揚的《造型藝術中的形式問題》[Das Problem der Form in der bildenden Kunst](1893)一書中略知一二。希氏在第三版修訂本的前言里明確地表達出自己的主要觀點:
與建筑截然不同的是,雕塑和繪畫常常被視為模仿性的藝術。但這種分類只是表達出三門藝術的差異而未考慮三者的相似之處。的確,雕塑和繪畫是模仿性的,就因為它們基于對大自然的一種研究。可這種研究卻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藝術家;因為他在模仿時不得不處理的形式問題便直接來自于他有關大自然的知覺[perception]。但如果僅僅是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亦即如果他的作品只是因這些理由而值得關注,那么其作品就絕不可能獲得一種與大自然相分離的獨立性[selfsufficiency]。要獲得這種獨立性,藝術家就必須將作品中的模仿性部分提升到更高的層面,而他達到這一層面所采用的方法我可稱之為建構法[Architectonic Method]。當然,此處我使用建構一詞并非取其通常的具體含義。就如在戲劇或者交響樂中一樣,此時我們的知覺也能使我們體認到[realize]一個沒有物體自然常態的整體形式。這正是我想用建構這一術語指稱的這種體認所絕對必要的特質。①Hildebrand, The Problem of Form in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ranslated and revised with the author’s co-operation by Max Meyer and Robert Morris Ogden, 3rd & rev. ed. (UT Back-in-Print Service, 1945), pp.11-12.另比較[德]阿道夫·希爾德勃蘭特《造型藝術的形式問題》,潘耀昌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頁。

希爾德布蘭德《造型藝術中的形式問題》
希氏此處將建筑、繪畫、雕塑三門藝術聯系起來討論的做法,實際上始于文藝復興盛期的意大利畫家兼作家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②邵宏《美術史的觀念》,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46-48頁。而他的“造型藝術”[bildenden Kunst]概念,則來自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中對“美的藝術”[sch?nen kunste]的劃分。③康德的“造型藝術”體系中包括建筑、繪畫、雕塑和園藝;參見[美]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邵宏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219-221頁;另見H. W. Cassirer, 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London: 1938, p. 97ff.至于他的“知覺”概念,無疑來自他的哲學家朋友菲德勒。菲德勒正是依據康德對主觀知覺[subjective perception]與客觀知覺[objective perception]所作的區別而對純粹可視性作出學理的表述。④康德認為主觀知覺決定愉悅或不愉悅的感覺,客觀知覺則是對事物的再現。對菲德勒來說,客觀知覺是藝術固有的領域,所以視覺與再現、直覺與表現就同藝術作品有了密切的關聯。藝術的本質特征引出了“能產性沉思”[productive contemplation]之概念,此概念反過來又將藝術與認知[cognition]問題相聯系,將感情排斥在藝術之外,并將藝術歸納為有關形式的知識和純粹可視性。見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p. 274-5.由此看來,希氏的主要發明在于用“建構法”這一術語技術性地將三門藝術統攝在一起。不過,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用過“模仿”[mimesis]這個非常顯眼的詞將詩歌、音樂、舞蹈、繪畫和雕塑串連在一起,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瓦薩里所謂“設計是三門藝術的父親”[Preche il disegno, padre delle tre arti nostre]之語。⑤見Erwin Panofsky, Idea: A Concept in Art Theory, Harper & Row, Publishes, 1968, pp.61-2.因而,希爾德布蘭德顯然是借鑒了瓦薩里的方式以反對古希臘以來的概念。希氏的真正貢獻在于:意大利語“disegno”在德語中沒有同義詞,而在形、音、義方面相近的“Dessin”指的是平面圖案,由此有著建筑學語源的“architektonisch”便成了最接近“設計”之意的首選概念。換言之,他用“建構”這一主要意指三維的概念輕易地將自己的雕塑專業包含其間了。
雖然希爾德布蘭德在該書中限定和削弱了菲德勒的觀點并顯示出學院派藝術的傾向,但他的確是更直接地查驗了將這位朋友的判斷理論用于雕塑時的結果。他發現了遠觀與近看之間在表征上[symbolic]的差別,遠觀的表征是綜合的,亦即藝術家的視象[vision],近看的表征是分析的,亦即經驗的視象。由于遠觀是有關表面的視象,所以任何意欲藝術地再現縱深感的嘗試,都必須不斷地求助于投影平面[projection plane]。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縱深的視象是在表面視象范圍內的一種暗示。這種視象用于表現表面整體的藝術需要。希氏指出,米開朗琪羅運用過這種視象;切利尼就沒有使用過它。同樣,由于這種視象部分是自然存在的形式,所以只有有效的形式[form of the effect]才符合藝術性視象。然而,明暗關系[light and shade]比立體造型[plastic form]有著更為強烈的效果。每一對象應當沉浸在空間里,而對象的意義又取決于對空間整體的印象,看起來像是一個封閉的體積。藝術無法表現動態本身,而是用靜態的人體呈動態姿勢來暗示,因為假如功能性意義沒有在空間整體中表現出來,那這些就不是藝術性的意義了。卡諾瓦[Canova]認為紀念碑是添加了立體塑像的建筑。這是誤解,因為假如浮雕要看起來有縱深感而非粘貼在墻上,那整個統一體就得有個建筑構架。另一個錯誤以著名的古代群像《法爾內塞公牛》[Farnese Bull]為例,其中的造型部分僅僅由行動而不是由緊密的空間整體來控制。在現代藝術里對空間整體的風格要求被完全遺忘了,然而希臘雕塑家和米開朗琪羅都遵守這些要求。簡言之,希氏試圖查明藝術性視象的特征以反對感官的模仿自然,而在歷史闡釋和論辯反應的范圍內,他毋庸置疑達到了目的。①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p. 278-9.
二
上述三位受意大利藝術影響的德國人所表達的純粹可視性理論,其與法國藝術中抽象派起源之間的歷史聯系,也許可以在比他們年輕卻早夭的法國象征派-印象派詩人朱爾·拉福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的寫作中見到。
拉福格十九歲開始發表詩歌,通過泰蕾茲·本特松[Thérèse Bentzon]一八七二年的一篇批評文章,②"Un poète americain, Walt Whitman: 'muscle and pluck forever", Revue des Deux Mondes (1 June, 1872), 565-82.他對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產生了興趣,之后的詩歌創作深受惠特曼的影響而成為法國最早的自由體詩人之一,后來影響到年輕一輩的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和T. S.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一八八一年,拉福格參加了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的系列講座,由此對繪畫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同年,他受雇為印象派作品最早的收藏家埃弗呂西[Charles Ephrussi]③埃弗呂西是從1880年開始對印象派藝術感興趣的,幾年里買了約四十馀幅馬內、莫奈、德加、雷諾阿和畢沙羅的作品。的私人秘書。自此拉福格的詩歌創作中又有了印象派繪畫的印記,并于一八八三年寫過一篇在其身后才發表的文章“印象主義”[L’Impressionisme],英譯作“印象主義:眼睛與詩人”[Impressionism: The Eye and the Poet]。④該文1883年初原計劃譯成德文發表于一家德文雜志上,以配合柏林古利特畫廊[Gurlitt Gallery]同年10月舉辦的印象派作品小型展覽。但估計未能及時完稿,故于作者去世后發表于Mélanges posthumes, Oeuvres complètes, fourth edition, volume III, (Paris, 1902-3), pp. 133-45 ;由William Jay Smith英譯為"Impressionism: The Eye and the Poet",發表于Art News, LV (May,1956), pp. 43-5。英譯之所以作如此改動,應該是因為拉福格文章的理論依據是揚-赫爾姆霍茨的三色論[Young-Helmholtz trichromatic theory]⑤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揚[Thomas Young]在1802年提出的三色理論假設,即視覺神經系統中有三種不同的感受器(今稱視錐細胞),分別感受紅、綠、藍三種不同波長的光。后經赫爾姆霍茨[Helmholtz]在1857年實驗證明,從此正式成為解釋色覺[colour vision]的權威理論。和費希納定律[Fechner’s law]。⑥“費希納定律”是表明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間數量關系的定律:心理量是刺激量的對數函數,即當刺激弱度以幾何級數增加時,感覺強度以算術級數增加。拉福格正是據上述理論而稱贊印象派,說他們是現代主義畫家,因為他們生著一雙具有非凡感受力的眼睛。他們摒棄傳統繪畫的線條、透視法和畫室布光[studio lighting],他們的造型是通過“色彩的顫動和對比”[vibration and contrast of colour]來獲得的,用色彩顫動與對比的自然透視法[natural perspective]代替理論透視法[theoretic perspective],用戶外作畫[pein air]代替了畫室布光。印象派看到和表現的自然是自然本來的模樣,即完全處于色彩的顫動之中。沒有線條、光線、立體感、透視法、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等幼稚的門類:所有這些都在現實中轉變成了色彩的顫動且只有通過色彩的顫動才能在畫布上表現出來。從整篇文章來看,拉福格依據當時有關人眼感官的生理學理論,闡述了印象派畫家的真摯和樸實,卻夸大了莫奈和畢沙羅的技術性作用。⑦Linda Nochlin (ed.), Impressionism and Post-Impressionism, 1874-1904: Sources and Document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6, pp. 15-8.
在一九○五年與一九一○年之間,法國繪畫界出現了決定之后西方藝術走向的兩場革命—野獸派[Fauvism]和立體派[Cubism]。其觀念背景是: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不同的藝術家對科學有兩種不同的態度:要么通過確定藝術的理性準則而受益于科學,要么為了想象力的權利而反對科學。野獸派采用的是第二種態度。相反,立體派則聲稱要用藝術代替科學,或者不管怎樣要創造一門他們自己的科學。這種目標就需要理論。塞尚、修拉、高更和凡·高也曾感到需要理論,但野獸派就沒有這種思慮,而且他們的美學也是含糊不清的。由于立體派具有理論的武裝而使自己比野獸派更具影響力,但野獸派與立體派并非截然對立,詩人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要是活到一九一九年或許能斷言,野獸派于一九○六至一九○八年的作品就是立體派的前奏。因為野獸派和立體派都不愿依賴由對各種現象[appearances]的反應所引起的情感,他們想根除印象派畫家的那種感覺論并接觸到更真實、更深邃的現實。由此出現了對傳統文化的否定,這種否定阻止了通過整個傳統慣例機能與傳統文化發生聯系,且出現了對歷史價值的深刻懷疑。實際上,他們試圖通過轉向無歷史[non-historical]的文化而繞開歷史,高更旅居塔希提島[Tahitian]和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赴非洲探險就是明證。所以,野獸派和立體派在視覺再現方面又同印象派一樣,都摒棄了傳統的透視法和立體造型的古典理想。他們轉向平涂色塊的繪畫,即是轉向色彩的絕對值和直接表現力。畢加索就十分明顯地受到了非洲藝術的影響,尤其是在他最早的立體派時期,但是立體派的另一領導者布拉克[Braque],卻主要受野獸派的熏陶。①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p. 292-3.
立體派第一篇重要的理論文本,是格萊茲[Albert Gleizes]和梅景琪[Jean Metzinger]這兩位畫家合寫的“立體主義”[Cubism](1912)一文。他們一開始便聲明:立體主義一詞只是用于讓讀者明白該文的研究對象,也是想急切地說明“體積”[volume]這一概念自身無法界定一場意在完整認識繪畫的運動;并聲言能理解塞尚便能理解立體主義。而立體主義就是繪畫本身。繪畫不要模仿對象,而要坦然地表現出自己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他們通過對塞尚的繪畫作仔細查驗而生發出對批判性思想的需求:
立體派畫家不懈地研究畫面結構及其產生的空間。
人們曾經不嚴謹地將這種空間與純粹視覺空間或歐幾里德[Euclidean]空間相混淆。
歐幾里德在一個假設中談到過運動中的物體之不可變形性[indeformability],我們不必堅持這一點。
如果我們希望將畫家的空間與一種具體的幾何學相聯系,那么我們應該求助非歐幾里德學派的科學家,我們應該學一些黎曼[Riemann]定理。
我們知道,視覺空間來自眼睛的聚焦和調節。
而繪畫這一平展的表面對于這種調節來講是排斥的,所以透視法教導我們去模擬的那種聚焦也無法喚起深度[depth]這一概念。我們知道,嚴重地違反透視法原則也絕不會損害繪畫的空間性。難道中國畫家不表現空間嗎?盡管他們十分鐘愛輻散視點[divergence]。
要建立畫面空間就必須訴諸觸覺、運動感和我們所有的官能……
畫面空間中布置的各種結構,都來自我們聲稱要控制住的一種活力[dynamism]。為了使我們的智慧具有這種活力,我們首先得運用我們敏銳的感覺。它只存在著一些細微差別[nuances]。結構似乎具有與色彩相同的諸種特性,它與其他結構相接觸時會得到調和或補充、會被消解或強調、會增加或消失。②Robert L.Herbert (ed.), Modern Artists on Art,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4, pp.2-8.
這一聲明告訴我們:立體派力圖研究結構[mechanism]中的體積,以及恢復透視法的多重角度。因而它實際上是對傳統的修正和新的嘗試,它試圖發現那些被認作是支配和約束自然的比例和數學法則。其分析意在恢復視覺語言中更深刻和最主要的價值。
另一方面,喬治·勒邁特[Georges Lema?tre]在《從立體派到超現實主義的法國文學》[From Cubism to Surrealism in French Literature]一書中,曾將立體派的發展劃分成四個分支:
1.科學立體派是這一運動的原初形式。它主要是反思和闡釋塞尚的一些創新,以及關注于發現感官錯覺之外的純粹現實。
2.玄奧立體派越過了科學立體派的分析過程而力求達到普遍意識[consciousness]的神秘交流,亦即“世界全部精神內容”的綜合表達。
3.客觀立體派,盡管這一名稱使人產生誤解,但他們進一步走向了抽象。為了與“純粹精神性的、沒有物質負擔的各種蘊涵[implications]”交流,他們希望從自身創造出各種客觀物體,而畫家必須求助于這種客觀物體去表達寓意[massage]。盡管早期立體派仍然利用自然形式的片斷,可這些片斷是以他們內心的自我所規定的方式來組合的,形式只能起源于主觀意識,與任何視覺經驗無關,所以他們有資格成為客觀立體派。
4.直覺立體派與柏格森[Bergson]所謂直覺[instinct]也是通往超驗悟性的道路這一論點有關,這種論點是超現實主義畫家自動主義[automatism]最早的系統表述。
事實上,自立體派以來現代藝術中所有最令人信服的宣言,都基于立體派形式上的新自然主義[neonaturalism],亦即基于非再現[non-represnetational]或是非具象[non-figurative]形式的原則,或者換一種說法,是基于形式現實[form-reality]而不是形式圖像[formimage]。立體派因此可以被視為屬[genus],而后繼的各種運動則可視為種[species]。③轉引自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 301.
三
差不多與法國繪畫革命同一時期于英美兩地舉辦的兩場藝術大展,讓英語世界的批評家和公眾注意到了當代藝術中的新動向:一個是一九一○年在倫敦格拉夫頓美術館[the Grafton Galleries]舉辦的“馬內與后印象派展覽”[Manet and the Post-Impressionists],另一個是一九一三年在紐約、芝加哥和波士頓巡回展出的“軍械庫展覽”[the Armory Show]。而此前英語世界的作家們也像高更和蘭波那樣不滿于傳統的文化,不過他們的不滿卻使他們轉向了東方世界。他們對東方藝術(主要是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及其觀念的詩意解讀或誤讀,在這兩場藝術展覽背景下便與西方藝術的新動向相映成輝。
早在一八八二年便向東方世界全面闡述西方“fine arts”(美術)概念的西班牙裔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 Fenollosa](1853-1908),①費諾羅薩1882年5月14日給龍池會作題為“Truth of Fine Arts”的演講,日文譯為“美術真説”;后英文以“The Nature of Fine Arts”之名,分兩次發表于The Lotos, Vol. 9, No. 9 & 10, March & April 1896.自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年在日本工作的十二年里,幫助建立了東京美術學校和帝國博物館,編輯了第一部有關日本國寶的目錄并由此發現了由日本僧人從中國帶回的古代中國書畫。他一八九○年回國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主任后,便于一八九三年在該館舉辦了“葛飾北齋及其畫派:日本和中國繪畫藝術特展”[Hokusai and His School: Special Exhibition of the Pictorial Art of Japan and China],及次年十二月的“京都大徳寺藏古代中國佛畫特展”[A Special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uddhist Paintings, lent by the Temple Daikokuji of Kioto]。②Seiich Yamaguchi (ed.), 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Published Writings in English, 3 vols. Abingdon: Routledge, 2009.這是中國藝術首次以“美術”之名在西方世界正式亮相。而費諾羅薩在藝術觀念史上的重要貢獻,就是他再次返回日本并于一九○六年完稿、身后由其夫人編輯、由法國漢學家佩初茲[Raphael Petrucci](1872-1917)作注的《中日美術的重要時期:東亞設計史略》[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1912)一書。
作為東西美術比較研究的最初嘗試,費諾羅薩在該著“導論”中說:將中國與日本的藝術放在一起討論,不僅是因為二者幾乎像希臘藝術與羅馬藝術那樣緊密地聯系成為一體,而且還因為那些持續變化的階段相互連接成了一種馬賽克圖案,或者說是展開的一幕戲劇性情節的發展。他將日語里來自中國畫論的“濃淡”這一批評概念,以羅馬拼音“Notan”的形式輸入到英語中,并運用于評價東西方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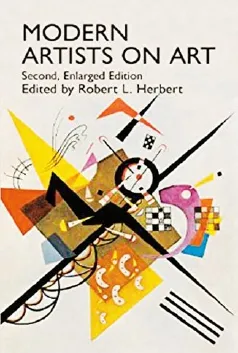
羅伯特·賀伯特(編)《現代藝術家論藝術》

費諾羅薩《中日美術的重要時期》(第一卷)

費諾羅薩《中日美術的重要時期》(第二卷)
我們正在走近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會將全人類的藝術品看作一體,看作是以一種單一的精神和社會努力而獲得的無窮變化。從前以及甚至最近,藝術家與作家似乎是憑借派性[partisanship]而持有自己的看法。古典主義者與離經叛道者相互攻訐。我們堅持有關“風格”的陳詞濫調。于是東方的藝術便被最嚴肅的藝術史排斥在外,那是由于這么一個假設,即東方藝術的法則與形式不適應既定的歐洲的類別。……我們認為所有[視覺]藝術都是在變化著的具體技術條件下和諧地分隔空間[spacing]。這些空間必須有邊界,因此便有了對勻稱的形狀作合比例的整合。眼睛注視著邊界,手則描繪出邊界,由此線條就成了再現的主要媒質。大量反射到眼睛的光線就成了空間里的另一種差異[differentiation],和諧地布置這些明暗關系需要一種新型的美( 濃淡創造構思的一種新能力。最后便產生了光線或色彩的特質,這種特質在天生具有這種新能力的人手中,就能產生無窮的差異和創造性的構思。……一方面是東方濃淡,[notan]),以及依據濃淡與希臘 濃淡、倫勃朗和委拉斯克斯[Velasquez]的濃淡的關系,繼而與威尼斯的濃淡,最后是與現代法國運動的濃淡的關系,都是一個顯見的事實。東西半球在中世紀的色彩方面也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主要的差別在于不同的再現方法,而方法方面的相似之處在我們接近當代時似乎也在日益增多。①Ernest F.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vol. I,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3, pp. xxiv-xxv.
在這里,費諾羅薩作為藝術史上的黑格爾主義者和藝術上的東方主義者,通過標舉中國畫論中的形式概念“濃淡”,從而替換了西方藝術觀念體系中從柏拉圖以來的形式概念“比例”[symmetria],進而使“濃淡”與現代法語中用于討論藝術的“細微差別”[nuances]一詞形成同義互釋。對于這種變化,我們可以從一百年后的艾倫·派普斯[Alan Pipes]在其頗具聲譽的教科書《美術與設計基礎》[Foundation of Art and Design]中對“濃淡”的釋義中見到:“濃淡—日語有關對稱的概念,指明暗關系。正(明)空間與負(暗)空間、物(或域)與底之間的相互作用。”②Notan: Japanese ideal of symmetry, meaning dark-ligh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sitive (light) and negative (dark) space, figure (or field) and ground. Alan Pipes, "Glossary", in Foundation of Art and Design,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04.而對于“nuances”,任何一部非專業術語辭典的《法漢詞典》第一義都是:“色調;深淺濃淡的程度。”的確,在今天的日語里,“nuances”已經逐漸替代了“notan”。不過,費諾羅薩和派普斯都忽略了“濃淡”在日本文化的母國自宋代以來的畫論中所具有的審美趣味:“老米[芾]畫難于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董其昌《畫旨》),以及在其藝術觀念體系中的技術性指向:“何謂六彩,黑、白、干、濕、濃、淡是也”(唐岱《繪事發微》)。
四
英國是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年這段時間里才逐漸認識同時代的法國藝術。一九一○年的倫敦展覽,雖然使其組織者羅杰·弗萊[Roger Fry](1866-1934)極大地喪失了對保守人士的影響力,卻使作為批評家兼畫家的他變成了新一代藝術家的偶像和帶路人。一般認為,弗萊直接受莫里斯·德尼的影響,他將后者討論塞尚的一篇文章譯成英文發表,③Maurice Denis, "Cézanne, I and II," trans. Roger Fry, Burlington 16 (1910), pp. 207-19, 275-80.還間接地受到德國藝術批評家尤利烏斯·邁爾-格雷費[Julius Meier-Graefe](1867–1935)的影響。邁爾-格雷費也認為“藝術是對潛存于現象之下的固定結構的再創造”。④Jacqueline V. Falkenheim, Roger F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Formalist Art Criticism, Ann Arbor, Michigan: Umi Research Press, 1980, p. 19.按文杜里[Lionello Venturi] (1885-1961)的說法,到了一九一二年,弗萊便提出了新畫家的理想:
現在,這些藝術家不想呈現出結果只是有關實際現象的蒼白影像[reflex],而是追求激起對新的和明確的現實深信不疑。他們不追求模仿形式,而是要創造形式;不追求模仿生活,而是要為生活找到一個對等物[equivalent]。……這種邏輯上極端的方法無疑會是放棄所有肖像似自然形式的一次嘗試,而且要創造出一種純粹的抽象形式語言—視覺音樂[visual music],以及……畢加索的作品十分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⑤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 308.
羅杰·弗萊清楚地看到這種新型的“創造出的”形式,其源頭便見于塞尚的作品中。到一九一七年,他計劃對塞尚的作品和地位作出闡釋。他以專著的形式完成了這一工作并于一九二七年出版。⑥即Cé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27.不了解立體派,弗萊也許不會理解塞尚作品中的“抽象”元素,但由于他了解立體派,所以他強調了這一點。無可否認,這種對抽象的認知使他能將對塞尚的決定性闡釋置于新的基礎之上。他在討論一幅風景畫時寫道:
呈現于塞尚視象中的那些實際物體首先都喪失了各自的具體特征,我們通常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特征才理解到它們的具體存在—它們被概括為純粹的空間與體積元素。在這個抽象的世界里,這些元素都由藝術家感覺的悟性而被完美地設計和組織起來,它們達到了邏輯上的一致。這些抽象元素然后又被帶回到真實事物的具體世界,不是通過賦予它們原來的具體特征,而是通過用一種不停變化和改變的協調統一[texture]來表現它們。⑦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 308.

文杜里《藝術批評史》
這種理解藝術作品形式創造過程的態度,羅杰·弗萊也與討論現代藝術一樣成功地用于討論喬托和弗拉·巴爾托洛梅奧[Fra Bartolommeo],討論倫勃朗和中國藝術,這種態度確立了弗萊藝術批評的重要地位。盡管弗萊有關畫家的上述理想幾乎是德尼與邁爾-格雷費觀點的翻版,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弗萊從形式主義角度討論中國藝術的文章,就需將中國藝術觀念在其理論乃至現代主義形成中的作用納入討論范圍。
事實上,弗萊早在一九○一年便表現出對中國藝術的興趣。已知的他第一篇有關中國藝術的文章,就是在參觀了白教堂畫廊[Whitechapel Gallery]的一個中國藝術展后,發表在倫敦最具影響力的文藝評論周刊《雅典娜神廟》(Athenaeum)上的“白教堂畫廊里的中國藝術”[Chinese Art at the Whitechapel Gallery]。弗萊在該文中表現出與十九世紀文化帝國主義完全不同的態度,認為中國藝術毫無之前歐洲人所以為的野蠻粗鄙之處。①Roger Fry, "Chinese Art at the Whitechapel Gallery", Athenaeum 3 (Aug. 1901), p. 165.之后,弗萊主要通過《伯林頓雜志》[Burlington Magazine]來宣傳中國藝術,而給這一重要期刊撰稿的既有英國的西方藝術批評家,也有研究中國藝術的英國學者。由此,弗萊便自然地將他所理解的中國藝術作為參照框架來評價西方藝術。與費諾羅薩相比,弗萊更像是在做東西方藝術的形式比較研究。例如,他一九○七年在一篇介紹法國十七世紀風景畫家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ain]的文章里寫道:此處我們發現克勞德不僅是十七世紀端莊的古典主義者,還是先于柯羅[Corot]而實踐柯羅后期主要觀念的浪漫主義者,更是先于惠斯勒[Whistler]發現中國山水畫的印象主義者。②Roger Fry, "Claude", Burlington Magazine 11 (1907), p. 272.這種評價表明,弗萊超越了早期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進而將自己所理解的中國藝術的形式觀念融進自己的理論中。
就在弗萊組織“馬內與后印象派展”(1910年11月)前的那個春季,有個日本-英國博覽會在倫敦的牧羊人叢林[Shepherd’s Bush]舉辦,該展覽有效地強調了當代藝術中純審美的意義。純審美原則讓人在東方藝術中更容易發現形式結構的重要性,這一標準便逐漸延伸到對待現代作品。有批評家還對計劃在大英博物館和牧羊人叢林舉辦的幾個中日藝術展作出預言:“值得考慮的是,下一代的歐洲藝術極有可能受到東方源泉的滋養。”③E. M.,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uly 2, 1910. p. 28.不過,弗萊對東方藝術具有獨特理解的形式主義批評觀,要待到兩年后(1912年12月)他組織另一次后印象派畫展時才趨于成熟。而在此過程中,作為畫家的弗萊對中國藝術的個人解讀有著不容忽略的作用。
一九一○年,弗萊在《每季評論》[Quarterly Review]上撰文評論著名詩人、時任大英博物館版畫與素描部助理館員的勞倫斯·賓雍④其最為人知的是《愿逝者安息》(For the Fallen)的那四行詩:英魂留韶華,萬世落塵埃,歲月荏苒記猶在,朝朝暮暮念人杰。(As the stars that shall be bright when we are dust, / Moving in marches upon the heavenly plain; / As the stars that are starry in the time of our darkness, / To the end, to the end, they remain.)[Laurence Binyon](1869~1943,又譯賓揚、比尼恩)的《遠東繪畫》[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1908)一書。弗萊夸贊賓雍先生對宋代山水畫的描述極為詳盡,這種描述對于任何一位哪怕初次見到復制品的歐洲人來講都是令人驚奇的,驚奇之處就是這些畫家所具有的極端現代性[Modernity]。弗萊不僅贊成賓雍對宋畫的現代性解讀,而且自己也尋求對整體的中國繪畫作現代性解讀的可能性。他堅稱,歐洲藝術家只是到了最近才開始擺脫明暗對照法而接受東方藝術家對明暗關系的排斥;中國和日本的藝術家之所以拒絕明暗關系是因為它主要是雕塑家的技藝,所以他們從未具有像歐洲藝術家那樣的明暗對照法概念;而他們六百年來在營造一些明暗的大氣效果,薄霧、黑夜和微光效果方面所表現出的手法,直到最近才為歐洲藝術所效仿。①Roger Fry, "Review of Four Books on Oriental Art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by Laurence Binyon, Medieval Sinhalese Art by Ananda K. Coomaraswamy, Indian Sculpture and Painting, by E. B. Havell, Manuel d’Art Musulman by Gaston Migeon)," Quarterly Review 212 (Jan. and Apr. 1910), pp. 225-39.第二年,弗萊又在《伯林頓雜志》上為佩初茲的名著《遠東藝術中的自然哲學》[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dans l’Art d’Extême Orient](1911)寫了書評。②Roger Fry, "Review of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dans l’Art d’Extême Orient, by Raphael Petrucci", Burlington Magazine 19 (1911), pp. 106-7.
線條是羅杰·弗萊所關心的形式問題之一。他根據“書寫性線條”[calligraphic linearity]而將漢代的墓室壁畫比作喬托、多納太羅、萊奧納爾多·達芬奇和倫勃朗的素描。③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London: Chatto, 1926, pp. 131, 68-73.他在“中國藝術的幾個方面”[Some Aspects of Chinese Art]一文里認為,中國人的設計[design]原則以及他們的韻律[rhythms]特征都絕非罕見,正如人們指出的,在這一方面,某些受歡迎的歐洲藝術家更近似于中國藝術家而非某些其他的歐洲大畫家。我們看中國藝術家線條的韻律當然毫不費力,我們在許多意大利的藝術中也常常見到它們。安布羅焦·洛倫澤蒂[Ambrogio Lorenzetti]的某些輪廓線描圖就非常近似我們能在那些中國重要時期的繪畫中發現的線條韻律;波蒂切利[Botticelli]也是另一位本質上的中國藝術家,他對設計的組織幾乎完全依賴線條的韻律,而他的韻律是那樣流暢整體,那樣圓潤自然,那都是我們在中國繪畫的典范中所見到的。甚至連安格爾[Ingres]或許也被人說成或是被痛斥為“中國”畫家,因為他也十分遵守自己的線性圖式,無論其結果是如何的有立體感,連這種立體感也是更多地來自其線條輪廓的精心布局,而不是靠著歐洲畫家所依賴的其他方式。④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London: Chatto, 1926, pp. 131, 68-73.
據此看來,羅杰·弗萊與費諾羅薩一樣同屬于“世界藝術”[World Art]的鼓吹者,因為他也認為中國藝術像希臘藝術一樣,都獲得了理性與感性的完美平衡,因而是世界文明兩個偉大的中心。⑤Roger Fry, Last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p. 97.
五
一九一三年的軍械庫展覽經在紐約、芝加哥和波士頓巡回展出之后,當代藝術有好幾年都未被絕大多數美國批評家或有影響的部分美國公眾接受,也沒有在博物館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這一展覽為歐洲與北美之間的藝術交流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此外,人們發現各種新的藝術形式在美國一般更容易被接受且甚少引起爭論,因為美學思想的傳統并非像在歐洲那樣得到普及或根深蒂固。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歐美尤其是英美的文人們出于對東方藝術觀念的共同興趣而多有交集。
費諾羅薩從一八九二年開始在美國作系列的公眾講座,他的第一個講座題目就是“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文學和藝術”[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s]。⑥Ernest F.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An Outline History of East Asiatic Design, vol. I, p. xix.他的這類不定期的講座持續到一九○八年。那年的整個夏天他都在倫敦做研究,而與賓雍在大不列顛博物館版畫部相見九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費諾羅薩突然病故于倫敦。之后,費氏的遺孀瑪麗·麥克尼爾·費諾羅薩[Mary McNeil Fenollosa]花了兩年時間編輯整理費氏的全部手稿。那部兩卷本的《中日美術的重要時期》,在佩初茲和賓雍尤其是在有賀長雄和狩野友信的幫助下得以于一九一二年出版。瑪麗還將費氏二十年來有關“日本能劇、中國詩歌和漢字體系”三方面約十六本筆記手稿,交由已移居英國但還未出大名的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這位同胞來整理和編輯。身為作家的瑪麗之前讀過龐德的詩歌并欣賞后者的藝術觀點,所以才作出如此決定。時正一九一三年。
埃茲拉·龐德一九○八年移居倫敦,一九○九年擔任學過繪畫的愛爾蘭詩人葉芝[W. B. Yeats]的秘書。葉芝對亞洲藝術與文學的興趣影響了龐德,于是兩人常常一道去不列顛博物館看亞洲的展覽,龐德由此也就結識了勞倫斯·賓雍。賓雍對他在理解中國藝術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可見于他一九一四年的一篇文章:上世紀重新發現了中世紀,而這一世紀有可能在中國發現一個新希臘。⑦Ezra Pound, Th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8, p. 215.其實,這種將中國比喻成新希臘的說法,我們在賓雍一九○八年的那部名著《遠東繪畫》里見到了它的源頭:
日本人看待中國就像我們看待意大利和希臘:對他們來講那是圣地和源泉,他們的藝術不僅從這一圣地和源泉獲得了方法、材料、設計的原則,而且還獲得了無盡的題材和母題。⑧Laurenc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8, p. 6.

賓雍《遠東繪畫》
一九一一年,賓雍出版了《龍翔:論中日藝術的理論與實踐》[Flight of the Dragons: An Essa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in China and Japan]一書。當年,形式主義理論的代言人、對現代主義的形成有重要影響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the bloomsbury group]①約形成于1905年的布魯姆斯伯里團體是一個松散的劍橋同學會,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弗萊于1910年與貝爾相識后加入了這個團體;中國詩人徐志摩1921年底進入這個圈子。徐志摩與弗萊有關中國青銅藝術的交談成就了后者的"Some Chinese Antiquities”, Burlington Magazine 44 (1923), pp. 276-81. 徐志摩后結識同門師兄、漢學家韋利,并介紹胡適與韋利相識。的主要成員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1881-1964)便為該書寫了書評。②Clive Bell, "Review of The Flight of the Dragon: An Essa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t in China and Japan, by Laurence Binyon," Athenaeum 7 (October 1911), pp. 428-29.有趣的是,龐德到了一九一五年也為該書寫作書評,并發表在畫家兼作家劉易斯[Wyndham Lewis]辦的那個短命的漩渦主義[Vorticism]雜志《疾風》[Blast]上。現在看來,龐德與這一論題毫無關系卻能在四年后的一九一五年七月寫出書評,一定是他在一九一三年收到費諾羅薩的一大摞手稿,并于當年至一九一四年對之做編輯校訂時學到許多有關中日藝術知識后的所為。③Noel Stock, The Life of Ezra Pound, London: Random House, 1970, p. 148.他對該書作出了如此評價:賓雍先生的反叛并不足夠。……他不是那個世界的人,但在讀他的書時我們始終覺得他受了所讀過的最糟糕的英語詩人的影響。④Ezra Pound, "Chronicles," Blast, 2 (July 1915), pp. 85-86.這種直言的批評,在今天應該被看成是一位受到漢詩英譯感染的英語詩人對另一位純粹英語詩人提出的批評。這種感覺無疑來自龐德那年四月從基于費諾羅薩的手稿編譯和改寫出版、包括有十九首中國古詩的《華夏集》[Cathy](又譯《國泰集》、《神州集》)⑤Ezra Pound, Cathy, London: Elkin Mathews, 1915.全集里收有李白詩十二首、樂府兩首,王維、陶淵明、盧照鄰、郭璞各一首,《詩經》一首。中所獲得的趣味判斷。的確,他在三年后的《中國詩歌》[Chinese Poetry](1918)一文中寫道:中國人的趣味與我們的趣味之間的首要差別就是,中國人喜歡那種讓他們回憶的詩,甚至喜歡那種讓他們苦苦思索的詩。⑥"The first great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taste and our own is that the Chinese like poetry that they have to think about, and even poetry that they have to puzzle over."全文見Ezra Pound, Early Writings, Poems and Prose, ed. Ira. B. Nadel. New York: Penguin, 2005, pp. 297-303.
其實,不通漢語的龐德能夠有如此的體會,都直接和間接地受到中國文學原有的歐語、尤其是英語文本的影響。龐德在一九一三年為了《詩章》[The Cantos]的寫作學過九種外語,但對于東方的文學他全部靠閱讀譯本。⑦Noel Stock, Poet in Exile,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64, p. 6.他熟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與中國學者王韜合作譯出的《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也閱讀過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編譯的《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3)和翟氏所著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還應當知道翟氏在賓雍幫助下編寫的《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1905)。就龐德的《華夏集》而言,我們可以將之視為作者對費諾羅薩有關中國詩的筆記作出的英詩解釋,因為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漢詩英譯。但對龐德來說,接下來更專業的“日本能劇”和“漢字體系”問題就得依靠專家。龐德幸運地得到了賓雍在不列顛博物館的助手、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的幫助。于是他在韋利的幫助下接著出版了《能劇研究》[Ernest Fenollosa & Ezra Pound, “Noh” or Accomplishment: A Study of the Classical Stage of Japan] (1916)和《作為詩歌媒介的漢字》[Ernest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ed. by Ezra Pound](1918)。⑧比較George A. Kennedy, "Fenollosa, Pound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Yale Literary Magazine 126.5 (1958), pp. 24-36.通過龐德的努力我們得知,費諾羅薩注意到漢字書寫的象形特征,由此進一步體察出在視覺文化方面與西方“建筑、繪畫、雕塑”體系迥然不同的中國“詩、書、畫”體系。
阿瑟·韋利一九○七年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學習古典學,一九一○年因眼疾影響學業而離校,也是布魯姆斯伯里團體里的外圍成員。他在學期間受其導師、《中國佬約翰信札》[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1901)的作者洛斯·迪金遜[G. Lowes Dickinson]的影響而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也是在這個時期,韋利對中國藝術的興趣還受到了羅杰·弗萊的影響。①詳見John de Gruchy, "Towards a Study of Arthur Waley and China", 《鹿児島純心女子短期大學研究紀要》第38號(2008),第247-254頁。韋利一九一三年進入不列顛博物館版畫與素描東方分部成為賓雍的助手。雖然韋利公開出版《百七十首中國古詩選譯》[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要比龐德的《華夏集》晚三年,可韋利在一九一六年便自費印刷了五十本《中國詩歌》[Chinese Poems],分贈給葉芝、弗萊、龐德和一九一四年才移居英格蘭的T. S. 艾略特等人。這表明韋利對中國詩歌的興趣至少是與龐德同時產生的,而韋利更是一個專業的譯者。之后直到二戰前,韋利出版有《中國古詩選譯續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1919)、《詩人李白》[The Poet Li po A. D. 701-762] (1919)、《日本能劇》[The Nō Plays of Japan](1921)、《中國繪畫研究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1923)、《道德經》[The Way and Its Powerer](1934)、《詩經》[The Book of Songs](1937)、《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等譯著和專著。對本文論題最為重要的是,韋利從一九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伯林頓雜志》上連載九期的長文“中國藝術哲學”[Chinese Philosophy of Art],全面介紹了“六法、王維與張彥遠、荊浩、郭熙和董其昌”。由此,韋利便與費諾羅薩的學生岡倉天心[1862-1913]、翟理思和瀧精一等前輩之前的工作聯系起來。②有關他們三位在介紹中國畫論方面的成就,參見邵宏“中日六位作家與中國畫論西傳”,《詩書畫》,2016年第3期,總第21期。也由于韋利的寫作,英語世界的讀者較為全面地了解到中國的藝術觀念。
英語世界對中國藝術較為全面的了解,應該始于中國政府一九三五年在倫敦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由于展品由英方選定,所以賓雍和韋利都與這次官方展覽有著極為主動的關系。③參見Fan Liya (范麗雅), "Laurence Binyon, Arthur Waley and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kyo: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o.94 (January 2010), pp. 99-101.由此可以斷定,賓雍與韋利對中國藝術的個人理解,對這次展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而在此之前,上述作家的努力已經激起了西方藝術家去追尋將東方藝術的觀念作為自己的靈感來源。
六
現代建筑產生的杰作雖然比起繪畫要少一些,但它卻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而一直是形式與功能之爭這一觀念運動的對象。而在這方面最成功的建筑師,無疑就是創作出具有詩意建筑的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1864-1959)。作為惠特曼詩歌的愛好者,賴特打心眼里厭惡具有古典和天主教傳統的歐洲。雖然他的大量寫作并不清晰也沒有丁點的理論訓練,但卻飽含著驅使建筑師去全力對付結構[structure]的一種沖動。他不倦地告誡美國人要提防歐洲的影響,謹防有關機器文明的工業神話以及機器文明的藝術,這種藝術是一種智力的說明而并未分享到基本的有機法則[organic laws]。他的努力、參與感和直接性,與畫家對付畫布或是雕塑家對付石塊完全一樣。他的所謂有機法則不是有關空間的抽象法則,而是支配萬物自然生長的法則。所以,它們不是有關形式的法則而是有關物質的法則。他教導說,學生應當從研究材料的性質開始并學會理解各種材料;學生接著就會開始認識到磚是磚、木是木、水泥是水泥、玻璃是玻璃、金屬是金屬,每一種材料都是自在的也是自為的。盡管這說法聽起來有些奇怪,但這樣做卻需要匯集極大的想象力。每種材料都要求不同的處理方式,也須具有諸多可能性以利用各自特有的性質。適合一種材料的設計對另一材料就不合適,因為理想的純樸就是有機的形式。④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p. 315-20.
對于“有機建筑”[organic architecture]這一概念的產生,賴特在一九三九年于倫敦的演講里回憶道:
自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的災難之后,我們美利堅大地[Usonia]就充斥著這種假“古典”、現在叫主義的建筑。……我則盡可能繼續前行,一點一點、一步一步、一年一年地,一個關于建筑的全新觀念便吸引了我。我現在叫它新,其實這個觀念比耶穌都要早至少五百年。盡管那時我不知道這點,如今處于現代運動中心的這一原則早由中國的哲學家老子十分清晰地闡述過。就我而言,我有意設計的第一件真誠之作以表現這一建筑“新”觀念的,就是1904年在橡樹園[Ork Park]建造的合一教堂[Unity Temple]。
這個建筑的新觀念是什么呢?……其原則的中心思想就是原創地賦予有機建筑這一理想以生命,讓其能堅定地抵抗世界各地對之大張旗鼓的模仿。①Frank Lloyd Wright, The Future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Horizon Press, 1953, pp. 242-43.
一般認為,賴特早在一九○八年便將“有機的”一詞引入他的建筑哲學。這一概念的根據是賴特老師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名言“形式服從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賴特將之演變成“形式與功能是一回事”[form and function are one]。對他而言,這種形式與功能的融合就是建筑與自然的融合,包含部分與整體的關系[relation of parts to the whole]。②Kimberly Elman, "Frank Lloyd Wright and the Principles of Organic Architecture,” Pbs.org. N.p., n.d. Web. 16 Apr. 2015.而他對老子觀點的理解,極有可能來自首位用英文寫作的東方藝術作家岡倉天心風靡美國的兩部著作—《東方的理想》[Ideals of the East](1903)和《茶之書》[The Book of Tea](1906)。③Kevin Nute, "Okakura and the Social and Aesthetic Ideals of the East”, in Frank Lloyd Wright and Japan :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Work of Frank Lloyd Wright,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93, pp. 121-42.岡倉在被美國中學選為教材的《茶之書》中便對老子有關“部分與整體”、“有與無”的觀點作過英文闡釋:
We must know the whole play in order to properly act our parts; the conception of totality must never be lost in that of the individual. This Laotse illustrates by his favourite metaphor of the Vacuum. He claimed that only in vacuum lay the truly essential. The reality of a room, for instance, was to be found in the vacant space enclosed by the roof and the walls, not in the roof and walls themselves. [我們要恰當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須懂得整場(人生)大戲;對整體的理解就絕不能在對個體的理解中喪失。老子用他喜歡的有關“無”的比喻來說明這一問題。他聲稱真正的“有”只存在于“無”之中。例如,人們只有在被屋頂和墻壁圍起來的虛空里,而不是在具體的屋頂和墻壁上才感受到實在的房間。]④這是岡倉天心對老子《道德經》第十一章中“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的解釋;另比較[日]岡倉天心《茶之書》,谷意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第53-54頁。
由于建筑在西方造型藝術體系中與雕塑所具有的天然聯系,使得賴特依據對老子觀點的解釋而提出“有機的”觀念,直接影響到雕塑家亨利·摩爾[Henry Moore] (1898-1986)。摩爾將現代主義中的歷史超現實主義和抽象派的前提作為自己的出發點, 從而獲得了對形式價值的清晰認識:“完全的圓雕沒有任何角度是相似的。想使形式得以完整實現的愿望與非對稱[asymmetry]有關。”“所有藝術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抽象:雕塑中單單是材料便迫使人們離開純粹的再現而朝向抽象。”藝術作品必須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而不依賴其所再現的對象。”藝術家一開始就應該懷有“實在的形狀[shape],可以說他在腦子里記得住它,無論大小他都仿佛正完全地捏在手心里。”因為他用這種方式使其作品視覺化,“所以他要實現作品的體積,如同形狀在空中所取代的空間”。藝術家工作程序中有意識的部分必須消除沖突、組織記憶中的印象,并使他“不要同時向兩個方向一起行動。”但形式必須被感知到是純粹、實在的形式,而非對形式的描述或聯想。由于這一原因,形式不屬于歷史而是純粹的存在。顯然,復雜的形式不能用這種方式來界定,因為它只有在混合的過程中才能匯聚起來。與混合的或構成的形式截然不同,基本的形式都是有機的(organic,這一釋義借自賴特的建筑學理論)。形式被稱作抽象的,但它仍是有機的且依據匯聚自現實的內在法則而成形,也就是說,它是具體的和極度寫實的。⑤Robert L. Herbert (ed.), Modern Artists on Art, pp. 138-49.這種有關抽象形式是絕對現實的理論,廓清了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理論的種種歧義,并擺脫了這些理論陷入與再現性形式持續作對比的邏輯困境。形式作為絕對的存在,不是憑借印象派意義上的直接性來實現的,而是用其直接性實現了真實意義[the spirit]的形式。所以,抽象形式又重新被并入印象派有關經驗主義感受的理論中,而歐洲藝術再次發現了這條將之與其各種傳統重新結合的道路,并通過這種方式來為自己辯解。而抽象派雕塑家像印象派畫家一樣,再一次認為戶外才是其作品的恰當環境也就絕非偶然。⑥Lionello Venturi, History of Art Criticism, pp. 310-11.
其實,待到約翰內斯·伊頓[Johannes Itten](1888-1967)任教于包豪斯學校(1919-1922),經常引用老子“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言論以幫助學生掌握建筑空間理論時,⑦Magdalena Droste, Bauhaus: 1919-1933, Berlin: Taschen, 2002. pp. 24-32; Yoshimasa Kaneko, “Japanese Painting and Johannes Itten’s Art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37, No. 4, 2003, pp. 93-101.已表明東方藝術觀念及其在東方藝術中的呈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已然進入到西方學院的現代藝術教學實驗里。直到二十一世紀的艾倫·派普斯,他在前文提到的教材《美術與設計基礎》的“序言:無”[Prologue: Nothingness]中,其篇首語仍然用的是:“‘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