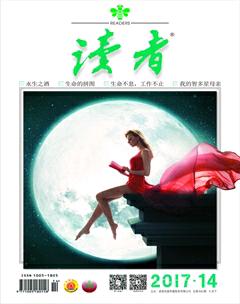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孫驍驥
無論在什么地方,如今關心養老金方案的人,都不可能只是老年人,還有繳納社保養老金的主力人群——正在為事業打拼、奮斗的中青年人群。大家關心的問題說起來無非是:按照現在的養老金繳納標準,等到我們退休的時候,社保退休金究竟能不能夠讓已經步入老年的我們繼續體面地生活?
我們大部分人或多或少有中國式贍養老人的經驗,這些經驗大部分是從父輩和祖父輩那里獲得的。比如我們祖父輩的養老,基本上是依靠他們的眾多子女共同負擔,似乎養老金并不是他們考慮的事,因為平日的大部分開銷由家庭成員負擔,即使生病住院,也有社保、醫保分減負擔。
但這種情況在我們父輩身上漸漸有所改變,他們開始關注養老福利金這件事。并且,由于生育子女的時候剛好受到計劃生育政策限制,因此依靠眾多子女共同負擔的策略完全行不通。而到了我們自己這一代,情況恐怕會比父輩更加堪憂。
“80后”一代人從工作的第一天開始就要繳納社保金,而要享受到社保金的切實福利,至少要等到65歲以后。以本科畢業23歲開始工作計算,要在42年以后才能拿到第一筆社保養老金。如此久遠的未來,確實讓人難以預料其間的各種變數。但無論如何,作為沒法指望子女養老,而只能依靠社會養老金來過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總難免憂心:假如交了多半輩子錢,到頭來這筆錢不能負擔自己年老時的生活,那么我們的未來將變成什么樣子?
顯然,當我們老了,我們的收入確實有從中層跌入底層的危險,或者說,我們都有成為“下流老人”的可能。
讓我們通過近鄰的經驗反觀自身。在“窮困者支援”非營利組織工作的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下流老人》一書里,提到日本普遍存在的老年人陷入貧困的情況。作者認為,所謂老年人的貧窮,是指個人收入未達到所在地區收入中位數一半的情況。“下流”二字,是指收入水平和社會階層從工作時候的中等水平向下層滑落,甚至滑落到貧困階層的事實。不僅收入變得極低,沒有足夠存款,而且在社會上沒有可依賴的人(社會性孤立)。因此,“下流老人”一詞,也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失去所有安全網絡的狀態”。
作者在書中說,日本年金(社會養老金)制度已經越來越無法有效發揮功能。《2014年高齡社會白皮書》顯示,全日本只有20%的人認為能領到10萬日元年金,19%的人認為能領到15萬日元年金,預計能領到30萬日元以上的只有2.8%的人,超過一半的人年金在10萬日元到20萬日元之間。不難看出,能夠獲得高額年金的人數非常少。然而,在普遍拿不到高額退休年金的情況下,人們退休后的生活將呈現何種面貌?
據日本總務省在2014年的統計,如果是夫妻兩名高齡者一起生活,那么包括衣食住行和社會保險等所有的費用,平均一個月需要27萬日元。也就是說,到了65歲,就算一個月有20萬日元的年金和其他收入,一個退休者即使有300萬日元存款,也會在大約4年時間內全部用完。哪怕存款達到1000萬日元,也撐不過14年,最終也會陷入貧窮。那些在退休前收入貌似不錯的白領,最后可能都無法幸免地“遇難”,陷入“下流老人”的境地。
情況確實不容樂觀。如果日本的老年人貧窮問題都已經如此嚴重,那么可以推知,在人均收入遠不及日本的中國,普通人因為養老問題而從中產向底層滑落,甚至陷入經濟崩潰的實際人數比例,將會遠高于日本。
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據,我國老年人口在2025年將達到3億。如此龐大的老年人口數量,要想維持基本體面的生活,需要耗費多少錢呢?假如取社會平均收入一半的算法,每月最少需要約2600元(2015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63241元)。一年下來,光是發放養老金就得花9.36萬億元。而且,這個粗略的計算法還沒考慮通脹和工資標準上調等增加養老成本的因素。
上哪里去弄這么多錢來發放?雖然現在對外宣稱社保金盈余超過4萬億元,但考慮到現在養老金標準每年上調6%左右的幅度以及與日俱增的老年人口數量,可預見,將來社保要么入不敷出,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要么像現在一樣,只能保障一部分人。
退休金實際上不足使用的現實,必然會促使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放棄閑散的退休生活,繼續工作。“工作到死”不僅是日本社會的現實,應該也會成為我們未來的常態。
藤田孝典在書中引用《2014年高齡社會白皮書》上的數據:年齡超過65歲卻迫于生計想要繼續工作的人數比例高達50.4%,超過總數的一半。在希望繼續工作的理由當中,約有76%是“可以得到生活費”。而根據日本總務省對65歲以上高齡者的調查,如果退休后不繼續工作,很多人的生活就無法繼續,這迫使他們成為就業市場上高齡的勞動者。每5個退休老人中,至少有2個人依然在工作。
關于退休人員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目前國內尚缺乏相關的統計數據。但是,從我們今天的日常經驗來看,有意愿將“活到老,干到老”的目標付諸實踐的人,今后會越來越多。若不如此,成為“下流老人”的可能性會增加很多。
如果想維持體面的退休生活,那么我們不能寄望于社保養老金。自己投資、自己養老,才是當下靠譜的自我贍養之道。雖然全民性的養老計劃對于每個人都有很強的吸引力,但實際上,在政府普遍差錢的今天,大部分國家的全民養老計劃,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拆東墻補西墻屬于常態。不僅僅是中國、日本面臨全民性養老問題,“環球同此涼熱”已成目前的共同趨勢。前幾年,經濟一度瀕于崩潰的希臘,計劃在未來把平均退休年齡由61歲提升至63歲;意大利政府宣布,公務員退休年齡從61歲提高至65歲;法國內閣則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逐漸提升至62歲;英國政府建議取消65歲退休的規定,5年內調高退休年齡至66歲……退休年齡提高,實際上是一種解決養老金不足的緩兵之計。而這種政策推行的直接后果便是,人們不得不工作更長的時間去供養老年人。社會福利資源也將進一步向老年人傾斜,例如,醫療資源的80%以上被老年人占據,年輕人反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助,工作人群需要繳納的養老金負擔越來越重。長此以往,年輕人群和退休高齡人群的矛盾和裂痕只會日益加深。
“如果長壽的人變成社會的包袱,生命的價值本身或許就會受到輕視。”藤田孝典不無憂慮地寫道。越來越多“下流老人”的出現,其最為惡劣的影響在于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崩潰,高齡者將不再受尊敬。高齡退休者是對社會或經濟發展有貢獻的人,在大部分文明社會中,高齡者受到敬重。但是,養老政策如果無法協調退休人群和工作人群之間的平衡,那么,高齡者耗盡全力對社會盡責卻無法得到尊敬的時代,或許很快就會到來。
最后我只能勸自己:別退休,接著打工吧!否則我們的結局就很可能印證了科恩兄弟那部絕世好片的名字——老無所依。
(蓉 兒摘自騰訊《大家》欄目,鄺 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