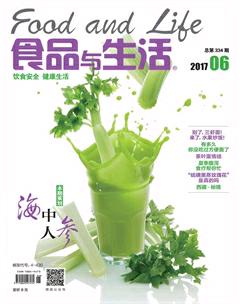滿天風露枇杷熟
楊忠明
舊聞、食事作家,上海作協會員,海派雕刻多面巧手。
端午前后,滬上枇杷樹金果燦燦,舒人眼目,讓人有身處山林的野趣,想起元人陳基句:“滿天風露枇杷熟,歸奉慈親取次嘗。”突發奇想,假如滬上行道樹、公園、綠地全部種上石榴、楊梅、銀杏、生梨、枇杷、蘋果、柚子、柿子,到了夏秋兩季,滿樹鮮果累累,街景更迷人。
到蘇州洞庭東山采枇杷是件開心事,太湖清風吹來,花迎鳥笑,溪水叮咚流淌,逸興遄飛,樹上的白玉枇杷皮色淺黃,剝開,果肉如雪似玉,晶瑩透潤,張口啖之,清芬含蜜的枇杷汁水涌出,甜得你口爽齒涼,飄飄欲仙,快哉快哉!有人說,從前蘇州只有白沙、紅沙(大紅袍)枇杷,近些年來白玉枇杷名氣大振。蘇州親戚告訴我,白玉枇杷原產洞庭東山白沙村,是村里農民湯永順從實生早黃白沙中選出。上世紀70 年代后期,專家對該品種與早黃白沙在果實形狀、大小及果肉厚度、花瓣形狀等方面進行分析,定名為“白玉枇杷”。白玉枇杷果形大,皮薄易剝,果肉厚而細潔,清甜多汁。
隨著種植擴大,白玉枇杷名氣越來越大。太湖邊的枇杷名種還有青種、照種、灰種、銅皮、和尚頭、雞蛋紅、荸薺種等。蘇州人說枇杷雖好吃,可惜核大肉薄,其實從清代文人朱彝尊(朱竹坨)和他道士朋友關于無核枇杷的故事中就可知,當時已經有人在研究無核枇杷啦!故事說道觀中有兩株枇杷樹,結出的果子竟然無核,那位道士透露了枇杷無核的秘密,原來是在枇杷剛剛開花時剪去了花蕊中某一根花須,結出的枇杷就會無核。當代科學家已經把研發小核、無核枇杷作為重點課題,用三倍體、花穗處理等先進科學技術試驗。據說,西南大學研究人員在重慶培育出一批無核枇杷 ,果核蛻變成小點軟核,這是枇杷老饕們的福音了。
白居易《山枇杷》詩:“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火樹風來翻絳艷,瓊枝日出曬紅紗。回看桃李都無色,映得芙蓉不是花。爭奈結根深石底,無因移得到人家。”枇杷除蘇州洞庭東西山出名外,還有浙江塘棲軟條枇杷,湖北宜都甜蜜大枇杷,據說剝一個能盛一小碗,還有福建漳州云霄枇杷、四川雅安石棉枇杷、安徽黃山三潭枇杷、四川文宮枇杷、浙江路橋枇杷、上海青浦滬香枇杷、廣東無核枇杷和臺灣臺東枇杷。初冬百花凋零,山間枇杷花開,朵朵潔白,玲瓏如玉。以前我隨舅舅去蘇州洞庭東山親戚家做客,冬日暖陽下的枇杷林里真熱鬧,蜜蜂忙忙碌碌地在枇杷樹間采蜜。枇杷蜜是蜜中珍品,養蜂者掀起蜂箱蓋子,一股枇杷濃香直沖口鼻,橙黃色的蜂蜜亮晶晶閃爍著,帶一瓶淺琥珀色的農家枇杷蜜回家沖牛奶喝,可清肺、化痰、止咳,那是兒時甜蜜的記憶。
上海老弄堂里枇杷樹結的果,黃黃的果子很好看,最后成了鳥雀的美食,為什么有些很酸?原來良種枇杷要嫁接才能保持優良品種。上海弄堂的枇杷樹大多是小孩吃了枇杷,把核隨地一扔長出來的枇杷樹。有位老人出國60 多年后最近從海外回滬探親,家鄉巨變,恍若隔世,當他找到西區老宅,發現自己種的枇杷樹依然結滿沉甸甸的黃果,感慨不已……
端午節在吳江“老鎮源”酒家飯桌上,有人問滬上古玩鑒賞家劉國斌先生,壽山田黃石何種顏色為好?劉國斌順手拿起桌上一只紅沙枇杷說:“呶,田黃石色最佳之一的就像這個東山大紅袍枇杷色,眼睛不要眨,仔細看看,黃若金,潤起沙,水靈靈,石中隱含蘿卜絲、桔瓤紋綿密者肯定是上品田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