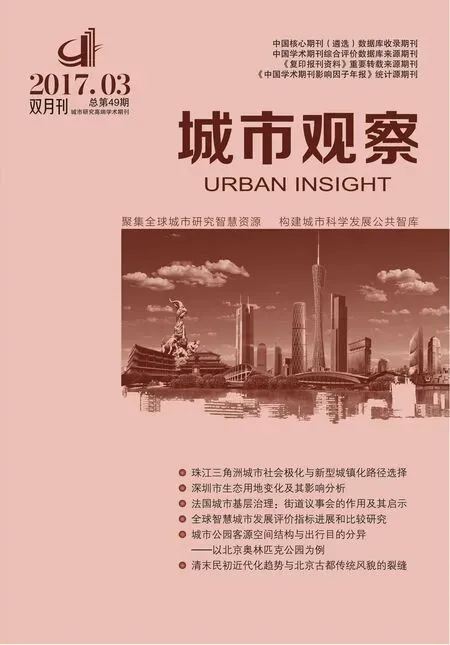深圳市生態用地變化及其影響分析
◎ 劉倩楠 易 琳 陳勁松 韓鵬鵬 韓 宇 王月如
深圳市生態用地變化及其影響分析
◎ 劉倩楠 易 琳 陳勁松 韓鵬鵬 韓 宇 王月如
本研究以2010年Landsat TM與2015年Landsat-oli數據為基礎,使用土地利用動態度與土地利用轉移矩陣作為研究方法,從土地利用變化幅度與變化面積方面,揭示五年間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方向。研究結果表明:林地、農田、濕地及其他地類為減少的土地利用類型,減少幅度最為劇烈的是其他地類,其次為農田,再次為濕地,最后為林地;增加面積的土地利用類型為草地與人工表面,增加的幅度都不大;從各地類變化的面積大小上看,人工表面增加18.29km2,林地面積減少9.03km2;這五年間林地轉化為人工表面的面積有12.84km2,而其他地類轉為林地面積的只有7.18km2,不足以抵消轉化為人工表面的這部分面積。控制生態紅線要以保護林地為基礎,當地林業管理部門要嚴格審批占用林地的項目,保護原本面積的森林,才能控制住深圳市的生態紅線,保證生態安全。
城市生態空間 土地利用分類 深圳市
一、引言
城市生態空間是保障城市生態安全、為城市提供生態服務、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重要空間。繼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1]又指出,要將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市發展,擴大城市生態空間,增加森林、湖泊、濕地面積,并合理劃定生態保護紅線。
為落實國家關于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劃定生態紅線的戰略部署,不同省市各自啟動不同形式推進生態紅線劃定工作。環境保護部已針對生態紅線劃定保護工作,發出有關技術指導[2](簡稱“指南”),并在各省市進行試點。江蘇、福建、廣東、山東等省份的“辦法”在國家要求基礎上,制定省級紅線工作計劃,地級市納入生態紅線劃定保護主戰場。由于各省份不同的地域差異和省市不同空間尺度的劃定需求,城市生態紅線劃定實施需要更高、更精確的標準和更細致的劃分方案。基于此,廣東省要求全省城市劃定城市生態控制線[3],成為全國第一個同時要求地市劃定生態保護紅線與生態控制線的省份。深圳率先提出了城市等級劃分方案,提出基礎生態控制線,隨后全國多個城市參照此方案開始了各自的生態控制線劃定。
伴隨快速城市化、城市擴張和城市郊區化的日益加快,生態紅線的劃定和堅守工作正承受著巨大壓力和挑戰。城鎮化,促使大量農地被非農業使用;城市農業和生態空間被大大的侵占和分離,生態環境越來越惡化,區域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嚴重挑戰。作為城市的天然載體,土地是城市生態安全的核心。而生態土地提供比其他土地更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成為保障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基礎。保護城市生態用地是保障城市生態安全,維護良好的生態環境,堅守生態紅線的根本保障。因此,研究一個城市的生態用地變化及其影響分析,對深入理解城市生態安全格局,了解城市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的健康狀況具有重要意義,更有助于更好的堅守生態紅線,保障城市及其居民繼續存在的綜合生態系統服務。
二、研究背景
(一)城市生態空間的概念與特點
國內外雖然在對生態空間(綠色空間)的概念界定上存在一定差異,但從生態功能與構成的生態要素視角來看并沒有本質區別。從國外的研究來看,一種觀點認為綠色空間包含了包括農地等在內的所有綠色植被覆蓋的土地類型[4],并具有開放性與享樂功能[5]。另一種觀點則將城市空間分為有植被覆蓋如開敞區域(公園等)和保護地(森林)的“綠色空間”,以及有被自然水體覆蓋的“藍色空間”[6]。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城市綠色空間應著重對于公眾的平等的可獲得性[7]。從國內的研究來看,雖然在界定城市生態空間覆蓋范圍上存在一些分歧,如以經濟產出為核心的農業生產用地是否應納入生態空間范疇[8],但在內涵上,大部分學者認為城市生態空間包括城市綠地、林地、園地、耕地、灘涂葦地、坑塘水面、未利用地等用地類型,在功能上能夠為城市提供生態系統服務[9], 并且能為城市土壤、水體、動植物等自然因子提供空間載體[10]。因此,本文在參考以往實證研究基礎上[11],將包括耕地在內的地表有植被覆蓋的土地利用類型,納入為城市生態空間的范圍。
從對城市生態空間(綠色空間)的界定上不難看出,城市生態空間具有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健康等多維功能,是一個自然、人工與半人工生態的合集,同時又是一個聯結生產、生活有著多重功能與價值的復合空間。
(二)我國大城市城市生態空間的演進
我國大城市的生態空間模式主要包括以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為代表的楔環放射模式,和以深圳、佛山等城市為代表的斑廊網絡模式[12]。在具體的基于土地利用與土地覆被變化研究城市生態空間演變中,不少城市都存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降低、建設用地侵占生態空間[13]、城市生態空間呈現破碎化、人工化[8]、總體減損以及空間演化不平衡等趨勢[14]。同時,城市生態空間演進受社會經濟政策、自然環境、歷史、與城市發展模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15][16],并且城市邊緣地區存在明顯的生態安全隱患與用地空間沖突[17]。
(三)城市生態空間規劃
城市生態空間規劃不僅是基于生態學方法對城市地表的規劃調控,更是結合了生物地球化學、社會經濟學等理論的綜合方法[18]。在具體的城市生態空間設計與規劃中,相關研究提出了城市群生態空間管制的四分模式[19]、地理模擬與二元空間協調優化系統[20]、生態空間重要性評價等理論方法[21]。此外,還要從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角度理解城市空間異質性,綜合考慮城市空間各要素的動態性,結合“人類生態系統”分析框架,從而營造一個有彈性的城市社會—生態空間[22]。

圖1 研究區范圍
三、研究區概況
深圳市位于廣東省東部沿海,北回歸線以南,陸域居東經113°46′至114°37′和北緯22°27′至22°52′之間,全境地勢東南高、西北低,低山、平緩臺地和階地丘陵是主要的地貌形態;東臨大亞灣和大鵬灣,與惠州市接壤;西及西南面連結伶仃洋和珠江口,與珠海、澳門隔水相望;南邊的深圳河、深圳灣與香港的新界相連,北部與東莞市為鄰[23]。
四、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研究所用數據為2010年Landsat-TM及2015年Landsat 8-OLI遙感影像,均由美國地質勘探局官方網站提供(http://glovis.usgs.gov/)。本文以ENVI 5.2軟件為平臺,對遙感影像進行預處理,包括輻射定標、影像融合和影像增強等操作。
本研究將基于多時相遙感影像數據,輔以搜集的研究區統計數據和相關資料,以RS、GIS集成技術為主要手段研究深圳市生態用地格局變化。根據深圳市的特點,參照《土地利用現狀分類及含義》,將研究區土地利用類型分為六類,分別是:林地、草地、濕地、農田、人工表面、其他。其中,濕地包括河流、湖泊、水庫、坑塘;耕地包括水田和旱地;草地分布較少,主要零星分布在山頂、河流邊緣以及城市的綠化草地,并沒有成片的大面積的牧草地分布;人工表面則包括城鎮和鄉村居民用地、交通用地和工礦用地;其他則包括裸巖(林地中表層巖石或石礫覆蓋面積>50%)、裸土地(表層為土質,基本無植被覆蓋的土地)。
本研究利用面向對象的分類方法對一期影像進行分類,再通過變化檢測,生成深圳市兩期土地利用遙感解譯數據集[24]。

圖2 深圳市2010、2015年用地
土地利用動態度。土地利用動態度反映了某個時間范圍內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變化情況,包括土地資源的數量變化;土地利用的空間變化及土地利用類型組合方式變化等,按照研究對象又可以分為綜合土地利用動態與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
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是指研究區域在一定時間范圍內整個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速度,是該畫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速度區域差異的指標,能夠反映區域內的社會經濟活動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綜合影響。其表達式為:

式中:Si為監測開始時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總面積;ΔSi-j為監測開始至監測結束時段內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轉換為其他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總和;t為時間段。土地利用動態度S反映了與t時段對應的研究樣區土地利用變化速率。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是指研究區在一定研究期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情況,用來表示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在一定時期內的變化速度和變化幅度。其表達式為:

式中:K為研究時段內某一土地利用類型動態度;Ua、Ub分別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種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能夠描述各種土地利用類型之間的轉換情況,它不僅可以反映研究期初、研究期末的土地利用類型結構,同時還可以反映研究時段內各土地利用類型的轉移變化情況,用來刻畫區域土地利用變化方向以及研究期末各土地利用類型的來源與構成。轉移矩陣中的變量可以為土地利用類型面積,還可以生成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的轉移概率矩陣,從而來推測一些特定情景下區域土地利用的變化趨勢。其數學形式為:

式中:S為土地面積;n為土地利用的類型數;i、j分別為研究期初與研究期末的土地利用類型。
五、研究結果與分析
深圳市在2010—2015年的五年間,林地縮減量達到近18km2,農田縮減量達到近5km2,草地總體基本沒有變動,濕地縮減量達到近8km2,人工表面增加量達到近8km2,呈現出城市發展空間面積規模的增長和生態空間面積規模的縮減。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通過對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的計算,可以揭示出當前社會經濟活動對深圳市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影響。結果表明:林地、農田、濕地及其他地類為減少的土地利用類型。減少最為劇烈的是其他類型,為81.08%;其次為農田,為6.81%;再次為濕地,為3.15%;林地減少1.95%。面積增加的地類為草地與人工表面,草地類型增加0.44%,人工表面增加0.9%。由于經濟活動,城市建筑面積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這是由于深圳國土面積小與深圳人工表面面積大雙重因素決定的。
2010—2015年,草地轉化為非草地類型為0.0036km2,非草地轉化為草地面積為0.0015km2,草地面積減少0.0021km2;林地類型減少9.0333km2,轉成人工表面的面積占絕大部分為12.8356km2,而其他類型用地轉入林地類型的面積只有6.5151km2;農田面積減少2.3868km2,轉出2.7195km2,轉入只有0.3327km2;濕地類型減少0.6732km2,基本保持不變;人工表面類型增加18.2897km2,轉入的主要是從林地如濕地類型中來,分別為12.8356km2和3.5324km2;其他類型減少6.1943km2。

圖3 深圳市生態空間類型的數量變化

表1 2010年-2015年深圳市土地類型轉移矩陣

圖3 深圳市生態空間類型單一土地利用變化度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土地覆被數據為基礎,綜合利用時序分析方法、土地利用動態度和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對深圳市2010年到2015年間的生態用地變化特征進行了分析。可見,深圳市將保護建設用地以外的所有土地作為生態控制區保護,成為了城市發展的邊界控制線。深圳市隨后采取了在這比例不降的前提下,進行局部調整的城市發展方案,對生態類型進行劃分并進行分類保護,未進行完全的分級控制和保護,增加了城市發展的管理難度。
新型城鎮化與生態文明的發展,對城市生態用地的規劃和管理提出了動態平衡,對生態用地需求量提出了更精確的要求。深圳未來城市生態用地的研究對象不僅局限于廣義的土地利用水平的生態土地,而需要更關注以生態土地類型較為詳細的特征為對象。對此,需要在今后的以土地生態功能為基礎的城市生態用地分類過程中加強城市生態用地需求量的測量和工作依據;加快實現土地生態分類和城市生態土地需求的研究從簡單計算量的分析向土地數量、綜合效益質量與空間格局的研究轉變。必須全面考慮不同生態功能的相互依賴性,即專注于多目標情景下的狀態函數,綜合權衡維護城市生態平衡后需要圍繞大量的農村地區的支持,根據生態利用供求平衡分析,確定由城市提供重要的農村腹地生態功能和清晰的階段相關生態補償策略,成為城市生態利用土方量計算的重要實際應用方向。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5/t20160505_800839.html
[2]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關于印發《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技術指南》的通知[EB/OL].(2016-07-09).http://www. zhb.gov.cn/gkml/hbb/bwj/201505/t20150518_301834.htm.
[3]茂名市城鄉規劃局.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關于印發《廣東省城市生態控制線劃定工作指引》的函[EB/OL].(2016-07-09).http://csgh.maoming.gov.cn/article.aspx?id=2454.
[4]Neuenschwander N, Hayek U W, Grêt-Regamey A. 2014. Integrating an urban green space typology into procedural 3D visualization for collaborative planning[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48: 99-110.
[5]Ngom R, Gosselin P, Blais C. 2016. Reduction of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green spaces: Their geographic insertion 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s matter[J]. Applied Geography, 66: 35-51.
[6]Nutsford D, Pearson A L, Kingham S, et al. 2016. Residential exposure to visible blue space (but not green space) associated with low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a capital city[J]. Health and Place, 39: 70-78.
[7]Dai D J. 2011.Racial/ethnic and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urban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Where to interven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2(4): 234-244.
[8]陳爽, 劉云霞, 彭立華. 2008. 城市生態空間演變規律及調控機制: 以南京市為例[J]. 生態學報, 28(5):2270- 2278.
[9]詹運洲, 李艷. 2011. 特大城市城鄉生態空間規劃方法及實施機制思考[J]. 城市規劃學刊, (2): 49-57.
[10]何梅, 汪云, 夏巍, 等. 2010. 特大城市生態空間體系規劃與管控研究[M].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1]潘影, 張茜, 甄霖, 等. 2011. 北京市平原區不同圈層綠色空間格局及生態服務變化[J]. 生態學雜志,30(4): 818-823.
[12]萬塵心,萬艷華,曹哲銘. 我國大城市理想生態空間網式結構模式解析及優化[J]. 規劃師,2015,(07):87-91.
[13]李鋒, 葉亞平, 宋博文, 等. 2011. 城市生態用地的空間結構及其生態系統服務動態演變: 以常州市為例[J]. 生態學報, 31(19): 5623- 5631.
[14]徐毅,彭震偉. 1980-2010年上海城市生態空間演進及動力機制研究[J]. 城市發展研究,2016,(11):1-10+59.
[15]郭榮朝, 苗長虹, 顧朝林, 等. 2008. 城市群生態空間結構演變機理研究[J]. 西北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38(4): 657-662.
[16]周銳, 胡遠滿, 王新軍, 等. 2015. 快速城鎮化地區生態用地演變及驅動力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4(6):1012- 1020.
[17]王海鷹, 秦奮, 張新長. 2015. 廣州市城市生態用地空間沖突與生態安全隱患情景分析[J]. 自然資源學報, 30(8):1304-1318.
[18]Pickett, S. T., Cadenasso, M. L., Grove, J. M., Nilon, C. H., Pouyat, R. V., Zipperer, W. C., &Costanza, R. (2001). Urban ecological systems: Linking terrestrial ecological, 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mponents of metropolitan areas 1.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32(1), 127-157.
[19]田嵩, 趙樹明, 劉穎. 2012. 我國城市群生態空間管制的“四分模式”[J]. 城市發展研究, 19(3):13-16.
[20]馬世發, 艾彬. 2015. 基于地理模型與優化的城市擴張與生態保護二元空間協調優化[J]. 生態學報,35(17): 5874-5883.
[21]關小克, 張鳳榮, 王秀麗, 等. 2013. 北京市生態用地空間演變與布局優化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32(3): 119-124.
[22]Pickett, S. T., Cadenasso, M. L., & Grove, J. M. (2004). Resilient cities: meaning, models, and metaphor for integrating the ecological, socio-economic, and planning realm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69(4),369-384.
[23]深圳市政府.深圳地理位置.人民網.2005-08-24[2011-10-22].
[24]深圳環境遙感信息網 http://www.shenzhenrs.com/
Changes of Ecological Land Use in Shenzhen and Its Impacts
Liu Qiannan, Yi Lin, Chen Jinsong, Han Pengpeng, Han Yu, Wang Yueru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Landsat TM in 2010 and Landsat-oli in 2015, with the land-use dynamic index and the land-use transfer matrix,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xtent and area of land-use changes, the paper reveals the direction of different land-use changes within a span of five years. Results show that woodland, arable land, wetland and others are reducing, while grassland and artificial surface are slightly increasing.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and-use change, artificial surface was up by 18.29km2, while woodland was down by 9.03km2.Only 7.18km2 of others has been turned into woodland, not enough to offset those turned into the artificial surface. Protecting woodl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controlling the ecological red line.Projects occupying woodlands must receive strict approval in order to hold the original forest and the ecological safty of Shenzhen.
urban ecological space; land-use classification; Shenzhen
F301.2
10.3969/j.issn.1674-7178.2017.03.003
劉倩楠,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空間信息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從事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及資源環境監測的研究。陳勁松(通訊作者),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空間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遙感圖像處理和微波定量遙感應用研究。易琳,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空間信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GIS與景觀生態學在海岸帶及沿海灘涂方面的應用研究。韓鵬鵬,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空間信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環境遙感與健康評價方面的研究。韓宇,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空間信息研究中心工程師,主要從事生態環境遙感監測研究。王月如,碩士研究生,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空間信息研究中心、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主要從事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及土地覆被監測的研究。
(責任編輯:李鈞)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子課題“華南地區土地覆被遙感監測”(2016YFC0500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