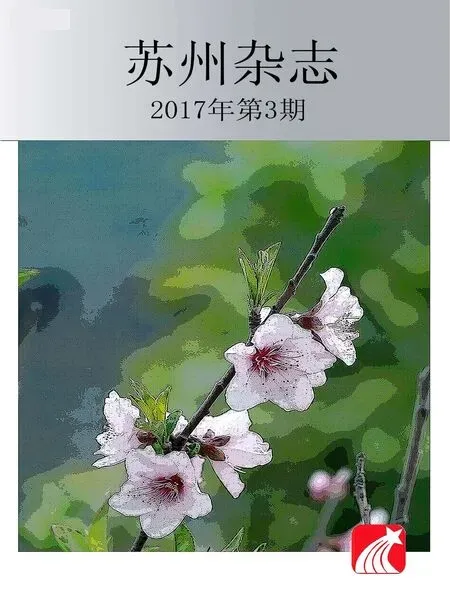在七都,這些地方這些人
尼楠
人與城
在七都,這些地方這些人
尼楠

很多年前,我甫出校門,回到七都。
我回到的七都只有一條街,有一個小小的車站,到吳江須坐上兩個小時的車。無論如何,我都不愿承認會在這里度過漫長歲月。雖然彼時我寫了一篇散文,叫做《小鎮生活》,在文章的最后我說,我這一生都將在這里度過,越來越自在,終于有一天愛上了這樣的生活。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那不是真的,我一直希望能夠離開。
然而后來,我最終做了自己的預言家,我一直生活在七都,從未離開。
在一個越來越像城市的小鎮上,摸索著領略小鎮生活的樂趣,感同身受著它的變化與成長,體會時而閃現的樸素與野趣,以及那些因為一些特殊的地方與人而涌動的氣息,就會水到渠成地覺得,一切就這樣吧。
時習堂·登琨艷
我怕登大師看到這篇文章。
第一次見他,穿著藏藍中式布袍目光炯炯的,他當時劈頭就說:“你不要寫我啊。”
果然,好幾年,我都沒有寫到他。
當時,我回來到網上搜他的資料,信息不多,但又都極有分量。是臺灣的著名建筑設計師,他設計的“舊情綿綿咖啡館”、現代啟示錄啤酒館,曾被譽為臺北最具特色與新意的建筑,與三毛似乎也是故交。之后到了上海,先后住過張愛玲、徐志摩、胡適、巴金的故居或鄰舍。后居住在蘇州河一帶,改造那里的舊廠房,蘇州河創意文化產業他是發起人。
另外,他脾氣暴烈,易怒。在跟隨南懷瑾老先生學習之后,仿佛還被稱為“憤怒金剛”。
后來,這個傳奇的人,也跟隨南老先生住到了七都。
第二次見到他,應該就是在南老先生2012 年初春的大課之上。在沿湖路上太湖大學堂7號樓暖黃的燈光下,我覺得他的面相與南老先生頗有相似之處,非常恍惚。
2012 年秋天,南老先生辭世后,登琨艷在七都廟港主持的時習堂開了一次課。他帶領著學生,一群人筆直地站在南公堤上,面湖臨風,布衣布鞋,神色肅穆清明,令人動容。
時習堂在沿湖路上,用的是廟港繅絲廠的舊廠房。
紀念活動結束后,我因工作便利,到了時習堂。彼時近午,結束了一上午功課的學生或走動或坐而交談。時習堂中間有個天井,圍著天井的大堂沒有門,廊下置著一排大蒲團,陽光就那樣直直地曬進來。
當時時習堂并沒有進行大動干戈的改造,完全是對舊廠房的順勢而為。是舊,卻并不是修舊如舊,這種舊就是它本來樣子最自然的呈現。我不懂建筑,然而也能感到它的狀態很放松。
在夜深人靜之時,人可以與這樣的房子對話。這座房子的靈魂仍然安在。
不過,后來,我又疑心,是不是大師并沒有使出十成的用心來做。
他當時又會突然跑去印度修廟,在七都在廟港的時間應該不會多。他就像一個世外高人,來無影去無蹤,我總覺得這里不會是他的羈絆。
沿湖路上的時習堂,我每每經過,總是會張望片刻。
這樣過了很久,不知道是哪一天,我經由車窗看向時習堂,卻驚覺它已起了變化。
外墻換上了青磚,種了幾叢竹子,煙青色與輕青色的搭配,統一低調,不經意間便要與人錯過。然而,卻也剛好能吸引有意者的關注。
你會覺得它帶著與七都不大相同的氣息,又或許,你會覺得,它是小鎮的另一面。
無論如何,我覺得放心了。
時習堂還在,登琨艷也還在。
廟里的如凈師父
老太廟其實不全是廟。外圓內方,三面環水,被水圍起來一字排開的三間大殿,分別供著代表道教的老太菩薩、佛祖和吳國的開國祖先吳泰伯。此外,隔著河水,左邊是個小小的四合院,右邊沿著河還有一幢廊形建筑。
粉墻黛瓦,水光滟滟,看起來,也不太像廟。
邊上就是一條主干道,由廟港通往震澤。車來車往,差不多相當于鬧市。
但是隔了一面水、一道墻,里面只覺得寧靜。
靜的地方,可以坐下來,喝一杯茶。
如凈師父的禪房在老太廟的后面,泰伯殿東邊的一個小院子里。院子里種著一些花草,有棵羅漢果樹。去年上半年,這棵樹結過果子,像一個個靜坐的佛。
禪房不大,窗明幾凈。靠墻放了幾張椅子,面西置著一張平時看書寫字用的桌子。桌子上堆著書,鋪著紙。墻的北邊掛著南懷瑾先生的字。此外,就是喝茶用的大桌子,放在禪房正中。
南北的窗戶對開著,直腸子的風穿來穿去,夏天也不大用得上空調。冬天呢,好像更是喝茶的季節,就著院子里的陽光,水稍微涼一點,就再續上。
平時沒有客人,如凈師父獨自看書寫字喝茶。
有客人來,他就坐在那里,煮水沏茶,偶爾說一兩句。
如凈師父是河南人,少年出家,師從成都文殊院方丈宗性大和尚。從文殊院那樣的名剎,只身一人,老遠跑到七都來,總該有些不適應,但是不大看得出來。
他看書不少,會寫書法,會畫畫。
有一回去的時候,看到他的書桌上放著《古文觀止》,書頁上空白的地方細細加了注釋。在這樣風白水清的地方,看看古書,念念佛經,如凈師父像是從另外一個時代來的。
其實他是85 后,會網購也會用微信,會在朋友圈里發動態,比如說老太廟的素食,冬天曬的丁香蘿卜,正在改造的書齋之類。
總之,他自由地在那些被標簽過的地方出入,一點也不勉強。
院子里有許多自動跑來乘風涼和曬太陽的小狗,夏天乘風涼,冬天曬太陽。
那樣陽光明媚的下午,也沒什么別的事,去老太廟走一圈,然后,坐下來喝個茶。也不拘喝什么茶,就是在那里坐坐,鼻間若有似無的香,窗外天井上方的天空出奇的凈藍,偶爾飄了幾縷云。
一切都是那樣整潔,茶香是整潔的,空氣是整潔的,心情是整潔的。
姜老師的飯店
老鎮源在七都沿湖路上,北邊是南公堤。天氣暖和的日子里,在堤上走一個來回,走到夕陽慢慢落到湖里,就去老鎮源吃飯。
開店的是姜老師。
很多外地的食客驅車前來,老鎮源聲名在外。
姜老師不是廚師,但應該是美食家。他講,店里的每一道菜,都是有戶口的。
戶口從書里來。
姜老師愛看書,看的當然不只是菜譜。比如最近店里頭新推的一道名叫水晶蝦餅的菜,便是根據梁實秋先生《雅室談吃》中的水晶蝦餅復制。這道文藝的菜,姜老師是花了很多的時間,才讓它得以從書里走出來。
姜老師似乎最不怕在做菜上花時間。
一道酥鯽魚,來自古譜,鯽魚要在麻油之中文火煨四五個小時。仿佛煮魚的不是文火,是時間。
另有一道魚頭湯,湯色濃白,入口潤滑,配以店里自制的胡椒及醋,魚鮮與調料配合默契十足,你不爭我不搶,主次分明又各顯千秋。這道湯,沒有五六個小時也是得不來。
最中意的雞肚魚粥,自然也同樣花時間。這道菜據說來自于明代,鰱魚肚一片片釘在墻上風干,只這一道工序便要兩三個月,之后的精煮慢燉自不需多言。
我有一個朋友,對農家菜頗有些異議,大概是恨鐵不成鋼,覺得有那么好的食材,農家樂們卻不思進取。在老鎮源,她頭一次對農家菜表示了肯定,她說,農家菜這樣做,就有意思了。當然,她也還有些這樣那樣的不甚滿意,就當作是對姜老師的鞭策吧。據我所知,她后來又帶著外地來的朋友去了老鎮源,看起來還是肯定的多。
食材都來自于七都廟港本地,菜種在湖邊的自留地里,魚蝦都是當天一早從漁民處購得。姜老師自己動手研制各種調味料,辣醬、胡蝦子醬,不一而足,即便是常用的醋,也要再經過一番加工方才上桌。
只是沒有味精或雞精。
老鎮源的菜里有一股清新之味,這種清新來自于食材,來自于太湖的水土,還有姜老師的百般打磨而又天然去雕飾的用心與巧思。
姜老師有些不大樂意被冠以農家樂的名號,他講自己做的是太湖農家菜。他說,到老鎮源來吃菜,最好不要喝酒,或者只喝少許,主要吃菜。
只需吃菜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