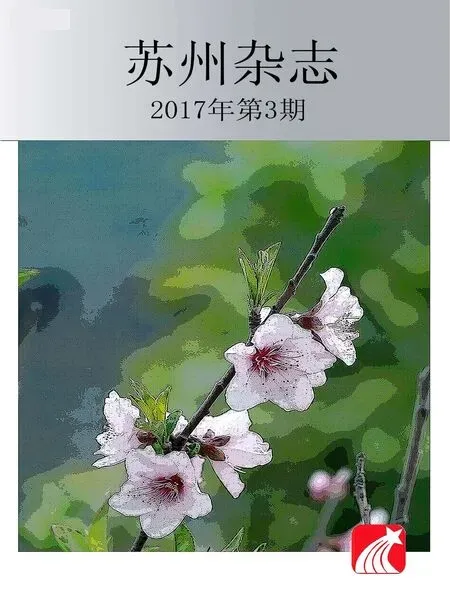石聽琴
張?zhí)V
石聽琴
張?zhí)V

陳設(shè)于石聽琴室內(nèi)的琴磚

石聽琴室
石頭與古琴,似乎天生就有一種相得。媧皇補天,煉五色之石,石自然具通靈之才,方堪任用。琴是原始巫祝的法器,當(dāng)然也是能夠絕地通天的了。兩者都那么遠(yuǎn)古而神玄,同樣被賦予了上天入地的無邊法力,那么石與琴,想必從一開始便是心意相通、惺惺相惜的吧。故琴能作松石間意,石能聽琴而頷首,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大多數(shù)石頭卻是冥頑不靈的,記憶中,除了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以及青埂峰下那枚外在文采富麗、內(nèi)質(zhì)癡頑愚絕的假的寶玉以外,勉強通靈的記錄著實也只是那么寥寥幾筆而已。至于琴,乃絲桐合成,雖說是中有太古之音,然而太古之音有誰聽過?我耳聽我音,我非太古之人,耳非太古之耳,又何辨太古之音呢?雖說如此,太古之音誰又未曾聽過?風(fēng)霜雨雪、流水高山,自然天籟之音哪一聲不聲自太古,又豈獨琴聲哉?我雖彈了數(shù)年琴,但是對于“石聽琴”抑或是“琴聽石”這個問題,至今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似的搞不清楚。難怪琴藝也如同拙石般冥頑不進(jìn),也真是怨不得天、尤不得人的事情啊!因此常自心生疑竇:這“琴中之音”“琴中之趣”可是這十個手指兒彈將出來的?抑或竟是生個耳朵聽出來的也未可知呢。
若是單說這手指兒的彈,我可毫不謙遜的是個行家里手啊!想當(dāng)年剛剛參加工作即進(jìn)了銀行,打電腦、打計算器可是經(jīng)過嚴(yán)格訓(xùn)練的。再笨的手,也經(jīng)不住這天天打、時時練,不下三月便已滾瓜爛熟了,蔥蔥玉指兒在鍵盤之上騰躍翻飛,大有嘈嘈切切、珠落玉盤之勢,很是美好啊。可是不知什么緣故,想是鹵菜吃多了,我們這幫小丫頭卻稱之為“發(fā)雞爪瘋”,因為在我們看來,這只是單純的熟練工而已,與學(xué)會騎腳踏車沒有區(qū)別,有啥美感可言?但是對于單項的技能,我們倒是信心滿滿的,乃至于多年以后,我的同事陪讀兒子的鋼琴課,這一學(xué)就會的聰明媽媽的指法竟然得到了鋼琴老師的高度贊揚。她回到銀行里,睥睨著對我們說:“啊呀,以為彈鋼琴有多難呢,不就是發(fā)發(fā)雞爪瘋嗎?我保證你們個個都能學(xué)會噢!”如果照此邏輯推理么,彈古琴豈不就是“發(fā)發(fā)中國古典雞爪瘋”而已嗎?在這個莫名的鼓舞下,不久以后我便信心滿滿地去學(xué)古琴了。
總算是手指兒還算靈活,學(xué)了幾年,竟也能夠像模像樣地彈下十幾支曲子了。正當(dāng)我自我感覺彈得“如鳴松風(fēng)”“陶陶欲醉”時,有一次,鄰居家常來看我練琴的小男孩忽閃著大眼睛對我說:“蘇蘇阿姨啊,你彈的琴真好聽,可是怎么每次都彈一樣的曲子呀?”我愕然道:“沒有哇,我彈了好幾曲的,應(yīng)該天天不同、時時不同的哇,難道你竟沒有聽出來嗎?”可是小男孩還是堅持他那“差不多一樣”之說。我真是無語!是呀,人家小耳朵沒有聽出來,我也沒有辦法硬叫人家聽出來吧!多說也無益,我只得悻悻作罷,不由得心下默然。彈的明明是《秋塞吟》《鳳求凰》《普安咒》,主題、內(nèi)容、情感個個不同、大相徑庭的,怎么就“差不多一樣”了呢?都說是“童子心、菩提智”,童子之心最單純,最近天趣,也最是無需刻意便能感知萬物。我怎么就碰到這么個“不聞秋聲、垂頭而睡”的童子呢?
遙想歐陽先生作《秋聲賦》,應(yīng)是心有秋聲而生發(fā)之,方能在這“星月皎潔,明河在天”的美好秋夜,悚然感應(yīng)到凜冽而肅殺的秋聲,頓生“人生短暫、大化無情”的悲涼,想是在他心境之中的秋聲,要遠(yuǎn)勝于他置身之環(huán)境中的秋聲吧!由此說來,秋聲當(dāng)不在樹間,琴聲也絕非在于指間。體察自然、感念萬象之心意不到,在聲韻上自然也絕難企及的!若是像我這樣熟練得如同騎腳踏車、打電腦一樣的去彈古琴,把那《秋塞吟》《鳳求凰》《普安咒》混為一彈、難分彼此的話,即便曠世才華的司馬相如不舍晝夜、堅持不懈地從漢代一直彈到現(xiàn)代,諒卓文君妹妹也斷不肯隨他去當(dāng)壚賣酒的吧!“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彈者所彈非琴也,聽者所聽非聲也,真正到了動情動心處,石自然能聽懂琴,琴也必能聽懂石的心事而融合于宮商之音。所以“彈琴、彈琴”重要的不是會彈而是會聽!想到這里,我不覺啞然失笑!看來,真正懂琴的,不是我這個彈琴的人,而是隔壁那個“不聞秋聲”的小童子。一言驚醒夢中人!抑或他竟是怡園石聽琴室外那個傴僂石丈派來點化我這塊小頑石的靈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