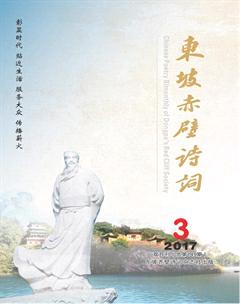難尋最是此中味
張金英
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卷一》曾說:“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此論對于評判不同體裁的作品亦不失為好的尺碼,形象貼切的語言、耀眼奪目的光彩、清香怡人的風格、和諧悅耳的音律,構成好作品的要素。正如鐘嶸在《詩品·序》所說:“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更是將詩味作為評判詩之境界的標準。
作品之味,既有形,又無形。其表現形式是有形可感的,表現結果則是無形虛渺的。如何運用有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無形之韻味呢?最近讀了林峰老師的《臨江仙·鳳凰城》一詞,為其中溢出的風味、韻味、情味所打動,現談談粗淺看法。
一、地域特色,獨具風味。
《臨江仙·鳳凰城》是一首描寫鳳凰古城風土人情的寫景之作。作者以曲岸、江樓、水閣、嵐光、漁火、暮云、宿鳥、花枝、風帆、笙歌、夜笛、煙汀等特有景物,凸顯了鳳凰古城的美麗,紛繁的意象呈現出光與色的交融、動與靜的相諧,將這座古城的風味展現無遺。
上片由近及遠,起筆于江樓、水閣,歇筆于漁火、暮云,精工細描,形象生動。“岸曲江樓浮翠,參差水閣疏明。”描繪了一幅詩情畫意的圖景,古韻濃郁,引人遐想。此處以“浮”字用得自然,“疏明”形容恰切,且為下文做了暗示:嵐光遙落鳳凰城。“遙落”似輕描淡寫,卻傳神地表現了傍晚的霞光映照在城市的美景,尤以“落”字煉得出味,將光彩這一無形的事物化為有形可感。“遙”字極富空間感,側面表現出天邊的遼闊。作者的筆法環環相扣,看著這如夢如幻的美景,不禁“夢隨漁火遠,思逐暮云生。”此結虛實相生,余味悠長。此夢,既是小城之夢,亦是作者之夢,隨著時間的推移,漁火的遠去而漸行漸遠。夢去了,一絲悵然之情頓生,隨著暮云裊裊而來。
下片由景及人,起筆于宿鳥、輕帆,收筆于孤月,動靜結合,情景交融。“鳥宿數枝花小,帆低一葉風輕。”展現了一幅生動的畫面,宿鳥、輕帆等物象并非此地特有,但作者善于將常見的事物,融入此時此地的場景,成為地域色彩的組成部分。最能體現此地特色的莫過于“笙歌夜笛滿煙汀”這一人文景觀了。歌聲與笛聲,流溢在整個夜空、彌漫在煙汀上,將鳳凰古城的詩意推向了高潮。今夜,誰與笙簫歌?人散之后,又是誰伴月兒行?作者以“今宵人去后,誰送月西行”的詩句,巧妙作結,詩意盎然,令人回味。
所以,寫景之作要善于抓住地方特色,極力表現其與眾不同之處,方能彰顯出景點的區域性,使景點散發出獨具風味的魅力。
二、靈動有序,饒有韻味
作品之韻味,寄托于貼切的語言表達。王安石也曾提出寫詩填詞要用“詩家語”。作品語言具有美感,方能生出韻味。袁枚亦提倡“作詩不貴用力,而貴有神韻”。這首詞下語平淡而不失靈動,用意卻是精深入味。
其一,巧用動詞,化無形為有形。
此詞的語言極具柔韌性與形象性:“浮翠”之“浮”,使翠色有了層次感;“遙落”之“落”,讓嵐光有了“歸宿”;“滿”使笙歌與夜笛,有了空間感;“隨”和“遠”,“逐”和“生”則使“夢”與“思”這些無形意念,得以寄托在有形可感的事物上。總之,化無形為有形,可使事物特征更加鮮明生動。
其二,妙在層次,井然有序。
全詞以時間為主線,有序地表現了鳳凰古城的風味。“岸曲江樓浮翠”,色彩簡明;“參差水閣疏明”,日漸明朗,原來是“嵐光遙落鳳凰城”,霞光一剎,如夢如幻,不禁“夢隨漁火遠,思逐暮云生”。一“遠”一“生”,對仗穩健,意蘊悠長。過片句“鳥宿數枝花小,帆低一葉風輕”,對仗工穩靈動,時間由黃昏進入夜晚,鳥兒歸巢,風帆微蕩。“笙歌夜笛滿煙汀”,由景及人,化靜為動。曲終人散后,又是一片寂靜:今宵人去后,誰送月西行?同時,“嵐光”“暮云”“宿鳥”“夜笛”這些詞語,也暗示了時間的流程,我們可以感受到鳳凰城在不同時間段的美麗。
三、有我之境,富于情味
袁枚有句經典的詩論:為人不可有我,作詩不可無我。也就是說,在作品中要融入“我”之感受與形象,亦是王國維所說的“有我之境”。這首詞的情味十足,還在于作者的感受真切地融入其中。上片結“夢隨漁火遠,思逐暮云生”,借景抒情,情景交融,達到無縫之境界。下片結“今宵人去后,誰送月西行”,最是出味!滿煙汀的笙歌夜笛之后,空留下一輪孤月,照著鳳凰城;“誰送月西行”,這輕輕一問,境界全出,情味濃郁。作者以心觀物,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王國維認為:只有洋溢著自然之美的、重在傳神的、有“味外之味”的作品,才能步入“有境界”的藝術殿堂中。這首寫景之作,獨具風味、饒有韻味、富于情味,將鳳凰古城的真味傳達了出來,余味悠長。如果我們在創作中處處留心,抓住不同景點之特色,用心體味,大膽想象,走進情境之中,就能創造出充滿靈性而令人回味的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