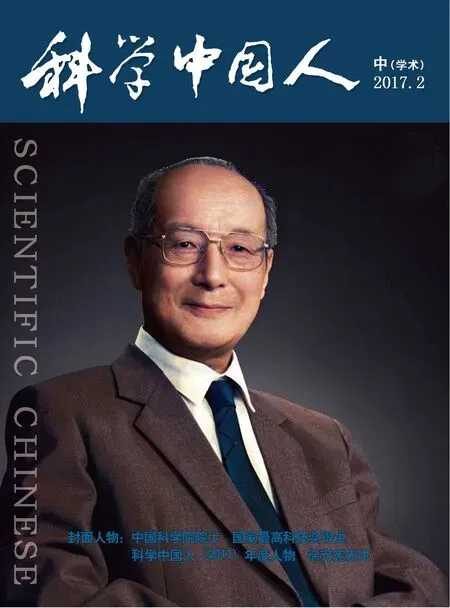更像哲學家的科學家
范國軒
“深刻的科學研究是在哲學層面上進行的。比如,達爾文研究物種起源的源動力是為了揭示道德的起源。”周強教授如是闡述科學研究。聽起來他更像是在談論哲學問題。
在周強看來,“思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科學上的重大突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曼哈頓工程,也不是大煉鋼鐵,而是長久孤獨求索與積累之后的Aha。”他認為真正有影響力的科學家應該可以開創一個本來不存在的領域,或是將一個原本不熱的領域變成熱門。所以,科學研究無需擠熱門,重要的是發現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做自己擅長的。“科學可以拓展人類的思維空間,給想象以物質的翅膀。科學研究的歷程就是一個無窮的、不斷否定并不斷更新的思考過程。”
海外篇——清醒的認識開啟全新的方向
神經生物學是近幾十年迅速發展的一門科學,依靠多學科的交叉、合作取得了諸多重大進展,是21世紀生命科學研究的領頭學科,具有引人入勝的非凡魅力。在清華大學進行本科學習期間,周強并沒有在神經科學方面修過很多課程,但他一直對神經生物學抱有濃厚的興趣,堪稱這一學科的忠實擁躉。
“相對于國內來說,美國在神經生物學方面的學科實力非常雄厚,相關研究人員是中國的10倍,學術水平也是世界頂尖的。”基于這樣的考慮,本科畢業之后,周強選擇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神經生理學,碩士畢業后又進入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在神經電生理方向攻讀博士。那時他的工作聚焦于神經信號在感覺系統中的傳導,先是在體的研究,后是在細胞層面的離體研究。“那時在整體動物上發現了很多有趣的現象,但是不知道在神經細胞的水平上如何解釋這些現象。于是我決定要深入學習神經細胞生理學。”周強如是說。
周強的一個長期的興趣,源于大學時代,就是學習與記憶的神經科學基礎。是什么讓記憶可以這么快形成又這么牢固?“從博士后時期起,我開始研究神經突觸的可塑性,就是探索神經細胞之間的連接是如何改變的。”周強說,他在神經突觸的生理機能和可塑性方面做了10多年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創新性成果。2003年,他在Science上發表的文章,在國際上率先提供了突觸可塑性是大腦感覺功能改變的生理學基礎的直接證據。他也是國際上率先結合電生理與熒光成像方法研究突觸改變的結構和功能的相關性,并在此領域做出了先導和突出貢獻的人。可以說,周強在神經突觸的可塑性、功能和神經環路方面取得了國際上具有前沿和先驅性的成果。
取得突破性成果后,周強并未按部就班,而是將目光轉向重大神經系統疾病的研究——一個他從未涉獵的領域。他說:“在神經突觸可塑性方面,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是時候開拓新領域了。相對于基礎研究,對疾病機制的理解和治療方法上都還有著大量未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科學上的重要進步,更將幫助人類擺脫疾病的痛苦。”
抱著對疾病研究的濃厚興趣,周強離開了美國西奈山醫學院,進入Genentech/Roche(羅氏),從事神經系統藥物的研發。談到選擇Genentech的原因,周強解釋道:“Genentech的突出優勢是科學研究,公司的理念是以優秀的科研來推動藥物研發。這個環境對于一直在學校從事學術研究的我來說十分契合。在實驗室工作的同時,與制藥界方方面面精英的密切接觸和深入交流,大大提升了我對新藥研發領域的了解與認識。”
在Genentech,周強作為新藥研發團隊的生物學主管,負責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方向的研究,也參與這些領域的商業開發與合作。他的團隊包含生物學家、化學家、病理/毒理分析師、臨床醫師、商業策劃等多方面的人才。
也是在公司工作時期,周強對于精神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興趣。“我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的本質。一個很簡單但同時很難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是正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就一定不正常嗎?還是說只是他們看問題的角度跟我們這些所謂的正常人不一樣?他們活在自己構建的世界里,是不是也可以活得很好?對于精神疾病的研究應該上升到哲學的層面,而不是單純地研究他們的大腦細胞為什么不一樣。”
隨著研究的推進,周強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新藥研發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新藥的發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相比于注重短期成果的工業界,在大學里更自由的時間支配與更寬容的科學探索,更有利于創新藥物的研發工作。因此,在業界5年之后,周強又回到了學校。而這一次,他的選擇不再局限于國外。
回國篇——“孔雀團隊”同風起
近年來,我國整體進入發展的快車道,不管是經濟層面還是意識層面都有利于開展科學研究,大環境的改善吸引了很多人才回國發展。對于周強來說,在大環境之外,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更有一個適合他的小環境。“北京大學是中國綜合性大學的王者,深圳特區是改革創新的先鋒。坐落在深圳的北京大學化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院,猶如一棵葉茂根深的古樹生出了未來的翅膀一一恰似其主樓群的設計,宛如一只展翅欲飛的大鵬,為百年北大探索國際化的創新之路。”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化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院(以下簡稱“化生學院”)院長楊震教授如此評價化生學院。
在周強眼中,深圳研究生院化生學院能夠將化學和生物有效地結合起來做新藥研發,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化學與生物學對于新藥研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沒有強大的化學支持,我們做的只是生物學研究,而不是新藥研發。”促使周強回國的一大因素是新藥研發工作需要綜合性大團隊的協同合作,包括基礎研究、臨床診斷、商業開發等諸多領域,目前在中國具有組織這種團隊的可行機制和實際可能性。
除此之外,周強還想在中醫中藥方面做些深入研究。“外國人對于中醫中藥一直不太相信,認為中醫無法證明其‘科學性。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本身是很相信中醫的。中醫在理念上有很深刻的東西,比如以一種系統的、動態的眼光來看待人的生理功能。中醫不認為人的狀況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根據身體狀況的改變不斷調理治療藥方。很多中藥也是經過千百年檢驗的。”周強說:“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的階段,仍然對包括癌癥在內的很多絕癥沒有良藥,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對于生命和健康的線性與黑白分明的認知理念。而中醫的動態、相互轉化的理念或許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找尋更加有效的治療方法。”
2014年,周強加入了化生學院。國內、國外、高校、企業,轉了一圈,兼具東西方文化的精髓,囊括學術企業界的理念,向著夢想,周強慷慨激昂地進發。
剛落戶到深圳,周強就馬不停蹄地主持了包括深圳市孔雀計劃在內的多個項目,聚焦重大神經系統疾病(包括老年癡呆癥和精神疾病)。孔雀計劃的主要目標是老年癡呆癥(AD)的機理研究和藥物研發。“老年癡呆癥,又稱阿爾茲海默癥,是威脅老年人健康的最主要的神經系統疾病。目前中國有近1000萬確診患者,約占世界總患者的四分之一。全球AD患者照護費用大于6000億美元,到2050年我國預計治療費用更是大于10000億美元,而目前國際上還沒有有效的治療藥物和方法,AD的診斷與治療中潛藏著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經過籌劃,周強的團隊將基本思路定為“新藥研發+老藥新用+中藥重用”。“我們的團隊里有AD研究領域的國際權威,將利用國際上最先進的研究方法和技術手段,在深入理解AD的生物機制的同時,發掘具有治療潛力的藥物。”盤點過團隊力量,作為項目帶頭人的周強對未來的進展充滿信心。
在精神疾病方向,周強團隊則側重于從神經發育的角度對疾病發生機制產生更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發現新藥靶點,特別關注其預防和早期干預的可行性。周強表示:“精神疾病的治療肯定是需要的。但從長遠來看,預防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期望能在5年內有所突破。”談到未來,周強信心十足地說:“我們將以卓越的基礎研究推動有效的成果轉化,為國內相應學科建立發展模式,并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團隊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對于建立實驗室和組建團隊,周強堅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在選人的階段會反復斟酌,慎重選擇,一旦把人才引進來了,就會盡力給他時間和機會,讓他充分發展。”在選人的標準上,周強更看重品格意志。受學生時期導師的影響,周強認為,一個優秀的科研人,必須具備創新精神和踏實精神。“一個科研人應該有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像孩童一般對于世界最初的好奇,這是科研的原動力。而在確定了研究方向之后,就要踏踏實實地尋找答案,有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嚴肅、嚴謹的態度。”
在周強的實驗室里,沒有什么“等級”區分,而是讓數據說話,堅持在科學上人人平等。周強很注重保護學生身上的創新精神,他認為學生是創新的源泉,學生對于知識的些許欠缺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們的優勢——少了固有思維的枷鎖和已有知識的限制,他們思考問題的角度可能更為新穎。正因為此,周強鼓勵學生多進行提問和討論。他從不會直接和學生說“Yes or No”。相反,他信奉蘇格拉底的啟發法。“我經常問學生,根據你的知識,發表的文章中的哪些東西有意思?哪些可能不對?哪些啟發了你?你所要做的實驗的新穎之處在哪里?”周強認為,只有當學生學會質疑,學會懷疑權威,他才會懂得如何自己去探索,才能真正學到東西并發現新東西。
其實周強知道,大部分學生將來不一定會從事科研。但是他認為,在實驗室做科學研究的經歷能夠培養一個人熱情、執著與認真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不論以后做不做科研,學生們都會終身受益。
在教導學生的過程中,周強特別注重學生的精神健康。他一直認為,在身體健康之外,我們應該給予心理層面更多的關懷。周強還提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在我國一直被歧視,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個人的品格問題。“我們應該認識到,精神疾病其實與心臟病、胃病等生理疾病并無差異,都是由一些生理上的改變而造成的。”
回首多年科研之路,周強深感責任重大。這種責任不只體現在研發治療疾病的新藥上,還體現在向大眾普及疾病的本質,提高民眾的科學意識和素質。“中國人要想在科學上有真正的、實質上的進步,首先需要提高國民的科學意識與科學精神。我們需要認識到:科學不是萬能的,它只能解決一些具體問題。科學家是人不是神,他們不是人生導師,也不是社會的醫生。社會需要做的,只是讓科學家可以更純粹地做他們擅長的事情,做純粹的科學。”所幸,這種責任讓他甘之如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