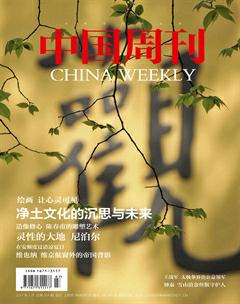無限時空中的新生命觀
歐陽蘭
在宇宙人間的一切疑問之中,唯有死亡最大!
可以想見:若無死亡,則無健康與否的問題,則無醫學的可能。若無死亡,則無想象的必要,人類就不會存在藝術。若無死亡,則無恐懼,則監獄不起作用,軍隊亦不必存在,國家也無意義,連帶著愛國者與叛國賊的概念也不復存在。若無死亡,則既不會有朋友,也不會有敵人,也不會與親人、愛人、路人與陌生人這些分別。若無死亡,人類完全不必要喜悅,也不必要悲傷,也沒有惆悵、迷惘、激動與失望這些種種情緒。可以說,人類一切種種,皆建立在“凡人必死”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基礎之上。
然而,在宇宙人間的一切期望之中,唯有“不死”最大!
上至帝王霸主,下至尋常百姓、販夫乞丐,無不怕死,恐懼死亡來臨,竭盡一切可能,來抵抗這一噩夢。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一生創立雄業,平六國,統天下,他認為自己的功業集三皇五帝于一身,高到了極點,因此自命名為“皇帝”。當晚年將近的時候,想起死亡的恐怖,不禁悚然,連續幾次派人到海島尋求長生不老之藥。歷代帝王,莫不如此。然而當我們看到秦始皇陵的時候,不禁升起感慨:縱然雄壯威武如秦始皇者,也無非是一抔黃土。看起來不死之想,畢竟茫然。
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圣經》對于死亡則有另一種明確的答案,那就是耶穌的信徒可以復活,而且得到永生。《圣經》里說:“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里,乃是永生。”又說:“論到死人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你們沒有念過嗎?”
“末日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教義。使徒保羅說:“你若口里認耶穌為主,心里信神叫他從死里復活,就必得救。”凡得救的人必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復活”一詞在《新約》提到115次之多,可見《新約》是以“復活”為題,首先復活的是耶穌基督,作了初熟的果子。他的復活見證了神的無限能力。
然而,隨著現代科學的昌明發達,使得《圣經》對死亡的解釋愈來愈不足以經得起細微的推敲,漸漸退守單純的信仰安慰。盡管如此,基督教以自己強大的社交形態,真誠負責的家庭觀念,道德自律的社會功用,仍然在很多國家地區起到社會文化中流砥柱的作用。
同樣,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道教也具有類似的情形。《道德經》本來是一本深邃博大的哲學著作,它和《莊子》一樣,被道教奉為經典之后,才慢慢成為一種性命修行的宗教經典。道教是一種極為浪漫、充滿瑰麗色彩的宗教,在幼稚的表象下,隱藏著達觀、釋然的人生思想。這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但道教對于人身修煉成神仙,能夠騰空飛升,長生不老的思想,可謂浪漫有余而實證不足,難以采信。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道教更多地向修心健體方面發展,并且在保持長壽方面取得豐富的實踐經驗,反而在當代社會找到了穩妥的立足之地。然而生死問題,確實非道教所能破解。
中國傳統佛教,尤其是禪宗,對于生死的解釋,有一套曲回周折、玄妙莫測的解釋。
試舉一個例子,出自《景德傳燈錄》。龐蘊居士一家四口,全都因為參禪而悟道。有一天他預言說,自己要在中午入滅(死亡),她女兒就走到外面觀看日頭,回來騙父親說,今天有日食,不知道是不是中午噢。龐蘊就奇怪,走出去看天色的時候,回來發現女兒搶先一步坐著入滅了(坐化)。龐蘊笑道:“這小姑娘比我還機靈。”龐蘊只好又活了七天,跟客人聊天的時候,枕著客人的膝蓋死了。龐蘊的妻子龐婆去將死訊告訴自己正在田間干活的兒子,兒子立即就拄著鋤頭死了。龐婆猶然覺得他們死得并不夠符合禪者的標準,沒有足夠的灑脫,她吟了一首偈子:
坐臥立化未為奇,不及龐婆撒手歸。雙手撥開無縫石,不留蹤跡與人知。
這種“想死就死,來去無蹤”的灑脫與自在,具有很強的戲劇性,也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然而,這距離人間煙火又是何其遙遠?與真實的痛徹骨髓的生死別離又是何其南轅北轍?這種詩意瀟灑的故事,不僅不能安慰世人的傷痛,反而增添了莫名的滑稽與荒誕。
當代佛教界受人敬重的星云大師說:“禪觀的世界是生死的,也是涅槃的。死亡朽壞的只是身體,我們的真如自性,法身慧命沒有生死。所以在禪者的境界里,生命是永恒不死的,永遠在涅槃里,永遠如如不動。”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真如自性、法身慧命”,這些玄妙而高深的詞藻,對于生死面前巨大的恐懼與困惑,當真能夠化而解之嗎?
一位來自西藏,并且在東南亞與澳大利亞皆有影響力的祈竹仁寶哲,對死亡過程有這樣的描述,這出自于他的著作《福慧明燈》。
“沒多久后,臨死者吐出一口濁氣,醫生便宣布此人斷氣了,家人也在此時哭聲四起。在這一剎那,亡者的意念是有取決性意義的。人在死時的意念,可以分為善心、不善心及無記心。善心是指皈依心、對三寶及上師的信心、慈心、悲心及菩提心等等。不善心是指貪、嗔、癡等等。無記心則是不善不惡的中性心態。這死時的一念,有極強的力量,亡者的下一生將善道或惡道,就是看這一念了。”
筆者引用這樣的一段話,并非是因為這是一份重要的文獻,而是這段話其實具有相當的普遍性。無論是傳統的漢傳佛教,還是藏傳佛教,都有類似的表述。且不說一個活得好好的人如此確鑿堅決地描述瀕死過程那么活靈活現是否具有可信度,即便具有可信度,那么,誰來對如此難以捕捉的“死時的一念”的性質進行分析和規定呢?
這種頗為流行的說法,使很多佛教徒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因為所謂的“慈心、悲心以及菩提心”是如此的不好把握,“對三寶的信心”也相對抽象,那么,最后能夠牢牢抓住的,就是“對上師的信心”了。將生死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歸結為眾人對自己的信心是否足夠虔誠,這不是一個坦蕩和真誠的答案。
佛教對于生死問題有自己明確、肯定、完整和理性的解答。如佛教的凈土思想在中國唐代以善導大師為集大成者,成為影響深遠的宗派之一,即凈土宗。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為極樂。”
在《阿彌陀經》中,釋迦牟尼佛講述了一個極樂世界的情形,極樂世界不是一個國度,而更像是一座風景宜人的學校,只有一位導師,導師給大家講法授課。這是一個生機盎然的所在,沒有苦惱,只有歡樂,所以叫做極樂。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圣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愿生彼國土。”
佛經中確認這樣一個事實,只要人聽說了阿彌陀佛這個名字,并且愿意稱念這個名字,不論多久(若一日……若七日),因為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就能夠“一心不亂”。當他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就會顯現在他的面前,使他“心不顛倒”,迅速得以“往生極樂國土”。釋迦牟尼說,因為這對于生命而言,是一件極大利益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所認識。
然而,即便對于佛教徒而言,這似乎都有點太簡單,太容易了。所以在很多情況下,關于這些美妙的描述,并沒有得到足夠認真的對待。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似乎更多地被看作一種類似譬喻,甚至是一種神話傳說。
一個彼世的國度,似乎聽起來有點基督教的意味。因為基督教就是這樣描述天國以及上帝的。很多佛教學者甚至不愿意過多談論關于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生怕自己沾上基督教的邊兒。他們更樂于討論“緣起性空”這種高度思辨的形而上的話題。
其實,凈土宗的極樂世界就是“緣起性空”最大的也是最終的體現。在《阿彌陀經》里的一段話,就透露了其中的玄機:
“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鵠、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
釋迦牟尼說,在極樂世界之所以沒有惡道,是因為根本沒有惡道的觀念,所以更不會有惡道的現實。反過來說,在極樂世界也沒有善道的觀念,所以也無所謂善惡的分別。這是一種極其深刻的闡述,它顯示了極樂世界極其復雜而精妙的構成與運作。簡而言之,極樂世界的凈土信仰,實際上建立在對觀念與現實、概念與實相、對立與統一的認識基礎上的。
據佛典,阿彌陀的含義,是“無量的光明與無量的壽命”,所以,阿彌陀佛也常常被稱為“無量光佛”或者“無量壽佛”。
當前天文學和宇宙學的發展,使我們已經能夠清晰地理解光的重要性。幾乎一切知識,都建立在“光速恒定”這一基本實驗結果的基礎之上。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我們的眼睛可以看得足夠遠,那么,看眼前的一朵花,和遠處的山峰,我們之所以會知道花朵比山峰更近,乃是因為光以同樣的速度折射到我們的眼睛里。從山峰折射的光線,抵達我們眼睛的時間,會比花朵折射的光線抵達我們眼睛更晚一些,而我們的視覺細胞會對此進行判斷。假如光具有無限的速度,無論什么距離,都是瞬間抵達,那么,我們會發現,那座遙遠的山峰與眼前的花朵,距離我們同樣近。
我們再假設一個有趣的實驗(當然,以現在的科學手段完全不能實現):在十光年外的太空放一面足夠大的鏡子,而我們在地球上放一個足夠精密的天文望遠鏡去觀察這面鏡子,你會看到什么?從理論上來說,假如你正好二十周歲的話,你可以從鏡子里看到自己正在出生。你會與剛剛出生的另外一個你,同時存在于這個世界上。
我們再將這個實驗繼續夸大一些。假如你乘坐一艘宇宙飛船,以光速在宇宙航行。而假如地球人也能看到你的軌跡。那么,地球人會記錄你在幾年、幾十年、幾百年也可能是億萬年(假如地球能夠存在那么久)的旅行生活,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你的故事。而你的感覺呢,只是坐進宇宙飛船一瞬間,然后立即就下船了,你什么也沒看到,只是覺得一瞬間。然后你踏上地球的土地,可以在圖書館里,找到一段記錄“在幾百萬億年前,曾經有一個喜歡冒險的年輕人,乘坐光速飛船,離開了地球……”。
這些有趣的實驗并非奇談怪論,而是根據科學可以清楚計算出來的推演,具有嚴密的邏輯。這些都提醒著人類,我們自以為龐大精密的知識體系,僅僅是局部的、狹隘的認知。而且科學也承認這一點。所以說,人的生命,它是受制于我們所處的這個經驗世界的。而一旦超越這個經驗世界,生命就會展示駭人的力量。人在某種條件、某種環境下、某種力量下,確實可以達到“無量壽”。這并非佛經里述說的神話故事,即便是在當今科學所推演的嚴密邏輯下,它也絕非聳人聽聞。
當人類在以恒定的光速為認知基礎的經驗世界里生存的時候,壽命則一定是有限的。而當光具有“無量”的特質,生命的度量則同時發生改變,從有限轉為“無量”。在凈土宗的理論中,恰指出了“無量光”與“無量壽”之間的密不可分的共生關系。
其實,在凈土宗的經典中,如果細致研究,會發現很多地方,都有重大的玄機,值得深入探究。比如《普賢菩薩行愿品》中說:“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我們知道在實際生活經驗中,事件都按照時間排序的。比如走近一個院子,然后走進屋子,然后看見一個人什么人,然后開始講話。然而在這一段描述中,“往生極樂世界”與“見阿彌陀佛”完全是同時發生的,這與現實經驗完全不符,要想透徹地理解,就需要明白事件順序、時間、光速與意識之間的互動關系。
我們知道在基督教里,神是具有人格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所以人和神之間,有密切的關系。神作為人的創造者和統治者,可以獎勵也可以懲罰人。而阿彌陀佛則不同。其實我們在寺廟中常常見到阿彌陀佛的形象,這種形象是中國佛像雕塑的產物。在顯宗或漢傳佛教中,阿彌陀佛的造像為右手下垂,掌心向前作與愿印,左手持蓮華。手作與愿印,表示眾生的往生之愿和阿彌陀佛的接引之愿相互攝引,阿彌陀佛能與愿眾生;手持蓮華,因為極樂世界的眾生不是胎生,而是蓮華化生。
然而阿彌陀佛的真實含義并不是這個形象。這個形象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了滿足心中的心理需求而由雕塑家創造出來的。阿彌陀佛真實的含義是代表了“無量光與無量壽”,具有徹底的、究竟的、無瑕的、無漏的慈悲,是為了解救苦惱的眾生而存在的一種境界。所以阿彌陀佛具有不可雕塑、不可臆想、不可形容的特征,它具有強烈的超越性和出世性。事實上,在佛教早期,都是不倡導,甚至禁止塑造佛的形象的,因為佛的形象不可塑造。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中國周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