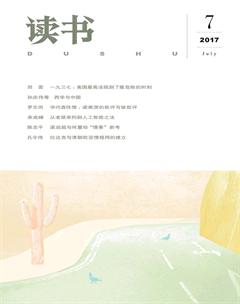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的傳統(tǒng)與反思
孫飛宇
社會(huì)學(xué)在中國(guó)的歷史并不算長(zhǎng),這當(dāng)然與社會(huì)學(xué)起源晚近有關(guān)。社會(huì)學(xué)本身可以算是一門(mén)現(xiàn)代性的學(xué)問(wèn),它的出現(xiàn)已經(jīng)是一種現(xiàn)代性現(xiàn)象,其研究的問(wèn)題意識(shí)和領(lǐng)域,自然也都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相關(guān)。而在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討論西學(xué),所面臨的問(wèn)題其實(shí)比較復(fù)雜:社會(huì)學(xué)這門(mén)學(xué)問(wèn)本身就是從西方傳播過(guò)來(lái)的,那么在社會(huì)學(xué)的領(lǐng)域內(nèi),何謂中,何謂西?
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的討論要回溯到何謂社會(huì)學(xué)的問(wèn)題。一方面,我們固然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圍內(nèi),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社會(huì)學(xué)理論和社會(huì)學(xué)研究方法論的類(lèi)似領(lǐng)域,例如經(jīng)典三大家,例如社會(huì)科學(xué)的定量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界定。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樣能在世界各地,都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社會(huì)學(xué)何為的困惑和爭(zhēng)論。因?yàn)榕c其他學(xué)科相比,社會(huì)學(xué)是最強(qiáng)調(diào)“扎根”于具體現(xiàn)實(shí)的一門(mén)學(xué)問(wèn)。沒(méi)有現(xiàn)實(shí)材料,沒(méi)有具體的時(shí)代和社會(huì)問(wèn)題,也就不會(huì)有社會(huì)學(xué)的研究本身。具體到中國(guó)而言,從嚴(yán)復(fù)翻譯《群學(xué)肄言》引入社會(huì)學(xué)的初衷,到費(fèi)孝通“志在富民”的理想,在近現(xiàn)代中國(guó),早期社會(huì)學(xué)學(xué)者們的杰出工作已經(jīng)對(duì)于這一“西學(xué)”之問(wèn)題給出了最典型的回答:在中國(guó),這門(mén)學(xué)問(wèn)必須要有最根本的中國(guó)問(wèn)題意識(shí)和最鮮明的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感。這是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早期傳統(tǒng)中最為珍貴之處。先賢們充分認(rèn)識(shí)到,社會(huì)學(xué)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固然都是外來(lái)的,而且社會(huì)學(xué)研究,正如其他學(xué)科一樣,也必然要保持著兼容并包的心胸,學(xué)習(xí)和借鑒西方文明中的杰出成果,然而具體到在中國(guó)進(jìn)行社會(huì)學(xué)研究,其核心卻必須要是中國(guó)的問(wèn)題意識(shí)與經(jīng)驗(yàn)感。在這一方面,從李景漢先生的“定縣調(diào)查”,到吳文藻先生有意識(shí)地培養(yǎng)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的人才并進(jìn)行學(xué)科建設(shè),到實(shí)踐的層面上梁漱溟先生和晏陽(yáng)初先生所代表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yùn)動(dòng),都是這種重要特征的具體體現(xiàn)。這一傳統(tǒng)在社會(huì)學(xué)恢復(fù)重建以后得到了繼承和發(fā)揚(yáng),并且已經(jīng)成為今天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界所公認(rèn)的最重要特征。這種“為己”的特征使得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界在面對(duì)中西問(wèn)題時(shí),有著鮮明的立場(chǎng)和態(tài)度。所以即便在面對(duì)西方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時(shí),早期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們的理解也都以鮮明的中國(guó)本土問(wèn)題意識(shí)為出發(fā)點(diǎn)。以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例,我們可以看到,費(fèi)孝通先生曾在魁閣時(shí)期寫(xiě)下了關(guān)于這本著作的長(zhǎng)篇讀書(shū)筆記,而該讀書(shū)筆記的核心問(wèn)題觀,則與費(fèi)先生從一九三三年進(jìn)入學(xué)術(shù)界以后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問(wèn)題觀如出一轍:關(guān)心在時(shí)代的劇烈變遷之際,一種有著悠久歷史與傳統(tǒng)的文化,如何才能與現(xiàn)代社會(huì)接軌,重塑其本身的社會(huì)平衡。這一態(tài)度所代表的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的典型傳統(tǒng),在此后得到了明確的發(fā)揚(yáng)。在八十年代,中國(guó)學(xué)界對(duì)于該書(shū)重新產(chǎn)生興趣,并且將其翻譯成中文的出發(fā)點(diǎn)也在于此。所以,中國(guó)的社會(huì)學(xué)界對(duì)于西方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典和現(xiàn)代理論的選擇和閱讀,以及閱讀的出發(fā)點(diǎn),或者說(shuō)我們對(duì)于何種理論有共鳴有啟發(fā),一方面固然是因?yàn)樵撟髌氛劦搅似毡榈默F(xiàn)代性問(wèn)題,然而另一方面,我們的出發(fā)點(diǎn)卻也都是中國(guó)本土的問(wèn)題,研究取向也一定會(huì)與中國(guó)的意義問(wèn)題相關(guān)聯(lián)。
不過(guò),這一傳統(tǒng)也有其局限之處。費(fèi)老晚年在對(duì)于自己早年工作的反思中,就提出了他的遺憾,或者毋寧說(shuō)這一社會(huì)學(xué)傳統(tǒng)需要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的地方。這一反思主要就在于:對(duì)于中國(guó)本土思想資源的傳承與重視并不充分,并且因此要予以加強(qiáng)。例如,在二○○三年的《試談擴(kuò)展社會(huì)學(xué)的傳統(tǒng)界限》一文中,他甚至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理學(xué)視為當(dāng)今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發(fā)展的關(guān)鍵所在。費(fèi)孝通畢生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歷堪稱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的代表。他早年受西方文化熏陶,并運(yùn)用社區(qū)研究的方法扎根中國(guó)社會(huì),然而在晚年的反思中,卻越來(lái)越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本土的思想傳統(tǒng)與本土文化,乃至提出“文化自覺(jué)”這樣的概念,這無(wú)疑是對(duì)于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早期傳統(tǒng)之反思與突破的典型代表。
這一反思特別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是因?yàn)樵缒曛袊?guó)社會(huì)學(xué)家的思想資源,包括費(fèi)孝通本人,大部分都來(lái)自西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試圖運(yùn)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來(lái)研究中國(guó);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重建之后,這一早期特征仍然存在,并且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時(shí)至今日,這一趨勢(shì)卻又有越來(lái)越狹隘,往往僅以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中最為形式化和最狹隘的那部分為準(zhǔn)則,同時(shí)也存在著越來(lái)越走向極端化的趨勢(shì)。這一趨勢(shì)往往令我們無(wú)法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社會(huì)的真正實(shí)質(zhì)。研究方法往往預(yù)設(shè)著方法論,方法論則預(yù)設(shè)著社會(huì)學(xué)是什么的假定,而這一假定又以對(duì)于社會(huì)和政治的理解為前提,所以僅以某種片面“科學(xué)的”方法論為圭臬,既無(wú)法讓我們真正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社會(huì)的面貌,也未免會(huì)令我們將中國(guó)社會(huì)中的實(shí)質(zhì)部分,視為多余的、落后的、不規(guī)范的和需要淘汰的。這反而是不科學(xué)的。所以費(fèi)孝通在晚年的這一反思,對(duì)于今天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的發(fā)展尤其具有針對(duì)性,不啻為洪鐘大呂,有振聾發(fā)聵之效。
總之,雖然社會(huì)學(xué)本身是一門(mén)外來(lái)的學(xué)問(wèn),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wú)法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學(xué)問(wèn)之中找到它的思想資源與研究方法。中國(guó)的社會(huì)學(xué)如果要獲得持久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和長(zhǎng)足的發(fā)展,就必須要做到在開(kāi)放胸懷、兼容并包的同時(shí),與本土傳統(tǒng)有著實(shí)質(zhì)性的傳承關(guān)系。這一傳承關(guān)系既體現(xiàn)在治學(xué)態(tài)度和治學(xué)理念方面,也體現(xiàn)在問(wèn)題意識(shí)、理論資源與治學(xué)方法上面。尤其是在今天,國(guó)內(nèi)社會(huì)學(xué)的建設(shè)如果僅僅強(qiáng)調(diào)方法取向和國(guó)際化取向,例如僅僅強(qiáng)調(diào)英文寫(xiě)作和發(fā)表,僅僅強(qiáng)調(diào)純粹的職業(yè)取向和規(guī)范制度建設(shè),而沒(méi)有對(duì)于中西問(wèn)題的深刻反思,沒(méi)有對(duì)于本土資源(無(wú)論是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資源還是社會(huì)資源)的學(xué)習(xí)和滋養(yǎng),不僅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學(xué)科的發(fā)展,甚至這門(mén)學(xué)科本身都會(huì)面臨著生存的危機(jī),更不必談繼承、建立和發(fā)揚(yáng)中國(guó)本土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