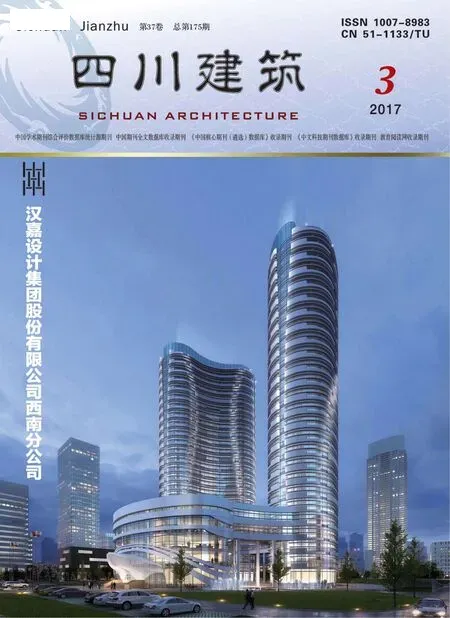帶墻體RC框架結構抗震性能研究現狀及展望
費 愷, 劉 嘯, 陳 盈, 張文學, 謝全懿
(1.北京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北京 100124; 2.北京城建亞泰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
帶墻體RC框架結構抗震性能研究現狀及展望
費 愷1,2, 劉 嘯1, 陳 盈1, 張文學1, 謝全懿1
(1.北京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北京 100124; 2.北京城建亞泰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13)
文章針對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常見破壞形態,分析了震害形式產生的原因。介紹了帶墻體框架結構抗震性能的研究成果及進展,闡述了框架結構中墻體的改造思路和方法。結合框架結構的震害,提出了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并對這種結構的減震機理進行了分析,指出利用預制墻體擺動耗能是有效減小整體結構地震響應的途徑之一。
框架結構; 預制混凝土; 填充墻; 掛板; 減震
框架結構采用梁、柱組成的結構體系作為豎向承重結構,并同時承受水平荷載,是一種空間剛性連接的桿系結構,結構形式簡單、建筑布局靈活,多用于多層辦公樓、醫院、學校、旅館等的結構體系。在框架結構設計中,填充墻被視為“非結構”構件,僅起到圍護和分隔作用。而近年來國內外幾次強烈的震害表明[1-5],砌體填充墻對整體結構的剛度效應和約束效應導致了大量的框架結構震害的發生。盡管填充墻在設計中被視為“非結構”構件,但在橫向荷載作用下,仍參與了剪力的分配,并與框架結構有著復雜的相互作用,因此,墻體與框架主體之間的連接構造對結構的抗震性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學者們對框架結構的減震措施及抗震性能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使得框架結構的設計方法和圍護墻的形式得到了不斷的改善。
1 RC框架結構震害及原因分析
近年來,國內外發生了幾次比較大的地震,總結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震害主要有結構整體破壞和構件破壞兩種形態。結構整體破壞形態主要表現為整體傾斜甚至倒塌、結構產生薄弱層導致的破壞等;構件破壞形態主要表現為框架梁柱及其節點區的破壞、圍護結構和填充墻的破壞等。
1.1 整體破壞形態
1.1.1 整體傾斜甚至倒塌
填充墻普遍損毀或倒塌,結構的部分底層失穩,柱子損壞嚴重,使得結構整體傾倒,嚴重者框架柱全部破壞折斷,各層全部坍塌,房屋整體徹底倒塌。圖1所示為北川縣城曲山鎮新城區某一框架房屋,底部框架的變形集中,框架柱破壞,造成房屋整體嚴重傾斜。圖2所示為都江堰市某框架結構住宅的整體倒塌情況,框架柱幾乎全部折斷,各樓層破碎疊落在一起,結構整體失穩,完全倒塌。

圖1 結構整體傾斜

圖2 結構整體倒塌
1.1.2 結構產生薄弱層破壞
在汶川地震中,框架破壞較多的一種形式是結構產生薄弱層導致的破壞。當結構沿高度方向的剛度或強度突然發生較大變化時,在剛度或強度較小的樓層形成薄弱層,該層框架柱的端部率先屈服形成塑性鉸,成為整個結構的主要耗能部位。
圖3為都江堰市某小區的一個6層框架結構,該建筑底層作為停車場,比較空曠,而上部樓層設置了大量的填充墻,由于結構上部樓層的剛度較底層顯著增大,導致底層局部屈服機制,所有底層框架柱上下端都出現塑性鉸。

圖3 都江堰市某框架結構底部
1.2 整體破壞形態
1.2.1 框架梁柱及其節點區的破壞
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梁柱及其節點區的破壞極為普遍,震害規律一般為:柱的震害重于梁;柱頂的震害重于柱底;角柱震害重于內柱;短柱震害重于一般柱。震害特征主要表現為柱端混凝土產生剪切開裂,而梁端破壞的“強柱弱梁”式結構震害形式較為罕見。
圖4分別為框架柱破壞發生在柱頂、柱身、柱底的情況。有些框架柱出現水平裂縫或斜裂縫、局部鋼筋保護層脫落主筋外露的現象,有些出現混凝土脫落、壓碎、壓酥、主筋壓曲外露、箍筋崩落等破壞現象。框架梁破壞情況如圖5所示,其震害相對框架柱較為輕微,主要表現在兩端和節點區附近產生的豎向裂縫或斜裂縫,在梁負彎矩鋼筋折斷處由于抗彎能力削弱也容易產生裂縫,造成剪切破壞。個別框架梁會由于主筋屈服、混凝土壓碎而出現彎曲破壞形態,形成塑性鉸。框架梁柱節點的破壞一般多由與之相連的框架柱端部破壞引起,主要表現為剪切破壞,核心區產生斜向對角的貫通裂縫,節點區內箍筋屈服,甚至崩斷。破壞情況如圖6所示。

(a)柱頂水平裂縫

(b)柱底混凝土壓碎

(c)柱身斜裂縫

(a)梁端豎向裂縫

(b)梁端形成塑性鉸

圖6 梁柱節點區破壞
1.2.2 圍護結構和填充墻破壞。
在地震作用下,框架的層間位移較大,圍護結構和填充墻阻止其側移,但砌體填充墻剛度大而承載力低、變形能力差,地震中首先承受地震力而遭受破壞。如圖7所示,圍護結構和填充墻的震害主要表現在水平或豎向墻體與框架的界面裂縫(圖7a)、單斜裂縫(圖7b)、交叉“X”型斜裂縫(圖7c),以及墻體由于缺乏可靠的連接而出現錯位甚至倒塌(圖7d)。在整體結構中,填充墻震害多呈現“下重上輕”的特點,如圖8所示,這是由于框架結構發生剪切變形造成的。盡管這些部位的破壞暫不影響主體結構的使用,但會對人們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并加快主體結構的破壞。

(a)界面裂縫

(b)單斜裂縫

(c)“X”型裂縫

(d)填充墻倒塌

圖8 填充墻震害
1.3 震害原因分析
結合幾次大震的震害現象,造成框架結構出現上述破壞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結構設計缺陷。早期建造的框架結構抗震構造措施較為薄弱,設計多追求底層大開間來滿足商業、停車等建筑功能的需要,使得砌體填充墻沿豎向分布不均勻、立面布置不規則導致結構存在薄弱層和應力集中區域。
(2)破壞機制喪失。由于現澆框架結構的整體性,樓板對框架梁有加強作用[6],另外,箍筋間距過大,對混凝土和縱筋的約束能力不足,導致框架不能滿足“強柱弱梁”的設計準則。地震中框架結構的整體倒塌、整體傾斜、整層壓扁等破壞幾乎均由柱的破壞引起[7]。
(3)填充墻的作用。填充墻可以作為結構的第一道抗震防線,分擔部分地震剪力,其破壞也可以消耗地震能量;然而墻體具有一定的剛度和強度,對柱頂端產生偏心支撐作用,可引起框架柱或節點的剪切破壞。早期對框架結構的設計,往往將填充墻簡單地作為質量加在結構中,不考慮其對結構的剛度作用,但是砌體填充墻等非結構構件對主體結構的作用和影響非常復雜。雖然國內外對此己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8-10],但在實際工程中如何平衡填充墻的有利作用和不利作用,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
2 帶墻體框架結構抗震減震研究現狀
從填充墻的剛度和強度對結構影響的角度出發,許多學者將墻體的構造方法作為解決框架結構抗震問題的主要切入點。20世紀70~80年代到本世紀初,國外學者為加強砌體內嵌的需要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研究[11-13],各種技術被用于加強或加固砌體填充墻。
唐興榮[14]等為研究設置拉結鋼筋、構造柱、水平系梁等不同構造措施的砌體填充墻對框架結構抗震性能的影響,進行了填充墻框架結構和純框架結構在低周反復荷載作用下的模型試驗,對比了各試件的抗震性能。結果表明,砌體填充墻有效地提高了框架結構的抗側剛度和承載力,但結構的初始剛度和承載力基本相同;分別設置構造柱、水平系梁和同時設置構造柱和水平系梁的填充墻框架結構的位移延性和耗能能力得到明顯的改善。
郭猛[15]等對密肋復合墻新型抗震結構體系進行了抗震性能與設計計算方法的研究,通過低周反復荷載試驗分析了外框密肋復合墻的破壞形態、承載能力、剛度、延性以及耗能等。試驗表明,外框密肋復合墻的抗剪承載力、彈塑性剛度均優于同等條件下的空框格框架,墻體后期的延性、耗能和抗倒塌能力較好,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墻體各組成部分的抗剪耗能作用。
除此之外,國內外學者也對設置阻尼裝置或元件的措施進行了研究。如,Riddington等[16]提出在填充墻與上部框架梁之間設置具有粘彈性性質的鉛層來消除因為柱子縮短而造成的荷載轉移,低周反復荷載試驗表明,鉛層的設置不會改變結構的側向剛度,并且結構的受力狀態會更加明確。Sahota等[17]通過長周期蠕變試驗驗證了上述方法的有效性;擬靜力試驗數據表明,設置鉛層后,填充墻的開裂荷載提高了75 %,但試件的極限荷載變化不大。
周云[18]等針對一種新型框架阻尼填充墻進行研究,將整塊砌體填充墻分成若干砌體單元,在單元之間和砌體單元與梁之間填充粘彈性材料層,砌體單元一端與框架柱通過拉結鋼筋進行固定連接,另一端與框架柱之間預留縫隙,其縫隙采用柔性材料填充形成柔性連接。對某工程動力特性及彈塑性地震響應的有限元分析表明,阻尼填充墻可耗散輸入結構的部分地震能量,減小結構構件的非線性耗能,減輕結構構件在地震中的損傷,可有效避免普通填充墻對結構破壞機制的不利影響,有助于框架結構實現“強柱弱梁”的屈服機制。
蔣歡軍[19]、姜俊銘[20]和周曉潔[21]分別對砌體填充墻框架結構進行低周反復荷載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試驗,分析了不同填充墻構造形式對框架結構抗震性能的影響。結果表明:與剛性連接的結構相比,采用柔性連接的填充墻框架結構的延性和耗能能力均有提高,填充墻的損傷程度則大幅降低。
雖然內嵌砌筑式墻體框架結構的研究成果頗豐,但砌筑式的墻體砌筑及搬運都較費時費工,很難縮短工期。預制裝配式結構采用在工廠里預制結構構件,在現場拼接安裝形成整體結構的施工方式,則可以有效減少現場濕作業,便于縮短工期。其中外墻與主體的連接主要可以分為外掛式和側連式。外掛式即預制外墻的上邊與梁連接,側邊和底邊僅做限位連接;側連式的表現形式為預制外墻上邊與梁連接,墻側邊與柱或剪力墻連接,墻下邊與梁僅做限位連接。許多學者也對墻體的連接方式和抗震性能進行了研究。
Loo等[22]對PCI手冊中的兩種柱與預制墻板節點進行了靜力荷裁和單向重復荷載作用下的強度和延性試驗研究,與現澆節點相比較,這兩種連接節點的抗彎強度都高于現澆節點,而且其延性和能量吸收能力一般都比現澆節點好。Michael等[23]通過對三層預制墻板結構體系進行了模擬地震振動臺試驗,結果表明裝配板縫逐漸松動后,底部水平板縫裂開,結構在底部裂通的水平縫以上形成的一個整體質量塊沿水平通縫做搖擺振動,質量塊的擺動耗能削弱了結構的整體地震反應,使上部結構不再繼續被破壞。黃宇星等[24]通過有限元分析得到基底剪力、頂點位移以及應力時程曲線,表明懸掛式預制混凝土墻板框架比純鋼筋混凝土框架和普通砌體填充墻框架具有更好的抗震性能。于敬海[25]為分析采用摩擦滑移連接件連接的外掛墻板對結構的減震效果,對一個12層的框架結構進行了動力彈塑性時程分析。結果表明,外掛墻板使得結構的整體地震反應呈下降趨勢,但結構的基底剪力和傾覆力矩均有所增加。
此外,外掛墻板也適用于鋼框架結構,研究表明,外掛墻板對整體結構有不可忽視的減震作用,可有效降低結構的頂部位移和層間位移[26-28]。綜上可知,對于框架結構中填充墻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思路:一種是“以強御強”,通過加強構造措施來提高結構的整體性,以抵御地震作用;另一種是“以柔克剛”,通過改變墻體的構造形式,在結構的某些部位設置阻尼裝置或元件,耗散部分輸入結構或者構件的地震能量。由于墻體具有一定的剛度和強度,地震時若首先遭遇破壞,隨即將成為結構中簡單的自重,對抗震不利。
3 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
3.1 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的提出
盡管國內外學者已針對外掛墻板對結構的影響作了許多的研究工作,但仍有一些問題尚待解決。如:(1)試驗結果表明外掛墻板對結構的整體剛度和強度有一定的影響,但如何在設計中考慮這些影響,還沒有相關結論;(2)國內外目前普遍對外掛墻板采取柔性連接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墻板有一定的適應結構變形的能力,同時減少外掛墻板的受力,但這也同時降低了外掛墻板對結構剛度的貢獻,使圍護結構的剛度儲備不能充分發揮;(3)外掛墻板一般都用連接件與主體結構相連,常見連接件大都構造形式復雜,且雖然其自身特性對整個外掛墻板體系的剛度和強度的影響均不可忽視,但相關的研究中對連接件定量的研究很少等。
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采用一種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如圖9所示,將掛板墻體(工廠預制墻板)通過連接掛件懸掛于上方框架梁之下,并在掛板墻體與主體結構之間采用發泡混凝土或石膏等脆性材料作為嵌縫連接構造進行固定,以保障圍護結構的正常使用功能。在常遇地震作用下,掛板墻體、主體結構及二者之間的連接保持相對完好,如圖9(a)所示。在強震作用下嵌縫連接構造達到極限抗剪強度而破碎,掛板墻體與主體結構脫離開來,只通過連接掛件與框架梁形成鉸接,并在地震作用下繞框架梁發生擺動,從而消耗地震輸入結構的能量,達到降低主體結構地震響應的目的,如圖9(b)所示。

(a)正常連接狀態

(b)擺開狀態圖9 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示意
這種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具有降低了現場勞動強度,減少施工能耗、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環境、縮短建設工程等優點,而且構造簡單,受力明確,可有效改善結構的整體抗震性能。
3.2 減震原理分析

圖10 結構動力計算模型
在大震作用下,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模型可以視為懸掛結構進行分析[29],將每一層掛板墻體的質量(mi)通過吊桿懸掛于主體結構質量(M0i)上形成復合結構形式,其動力計算模型可簡化為圖10所示,吊桿的長度(li)按照掛板墻體的質心位置選取,結構頻率如下式(1)所示。
(1)



圖11 ω與的關系
表1為一個單跨單榀五層框架結構的基頻分析結果,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的基頻比對應的純框架主體結構降低了28.9 %,比傳統框架填充墻結構降低了32.4 %,可見通過控制掛板墻體的特征頻率與主體框架結構頻率的相互關系,能夠有效延長掛板式維護結構的自振周期,從而降低結構地震響應,起到減震作用。

表1 頻率計算結果 rad/s
4 結論
通過對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震害分析發現,填充墻是其常見破損部位。一方面,可以通過加強構造措施來提高結構的整體性,以抵御地震作用;另一方面,可通過改變墻體的構造形式,利用墻體或設置于墻體的元件耗散部分輸入結構或者構件的地震能量。結合建筑產業化的需求,本文提出一種預制掛板式維護結構,并給出了自振頻率計算方法,該結構在強震作用下可以有效延長結構自振周期、減小結構地震響應。
[1] 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結構專家組, 葉列平, 陸新征. 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分析[J]. 建筑結構學報, 2008, 29(4): 1-9.
[2] 王亞勇. 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啟示——抗震概念設計[J]. 建筑結構學報, 2008,29(4): 20-25.
[3] 溫增平, 徐超, 陸鳴, 等. 汶川地震重災區典型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震害現象[J]. 北京工業大學學報, 2009, 35(6): 753-760.
[4] 譚皓, 李杰, 張電吉. 玉樹地震框架結構建筑震害調查[J]. 浙江建筑, 2012, 29(3): 21-25.
[5] 公茂盛, 楊永強, 謝禮立. 蘆山7.0級地震中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震害分析[J]. 地震工程與工程振動, 2013, 33(3): 20-26.
[6] 李永梅, 郭磊, 周錫元, 等. 現澆樓板對RC框架梁抗彎承載力的增強作用[J]. 土木工程與管理學報, 2012, 29(4): 20-24.
[7] 劉海卿, 倪鎮國, 張穎, 等. 多層框架結構地震倒塌過程仿真分析[J]. 科學技術與工程, 2009, 9(2): 472-475.
[8] Mehrabi A B, Shing P B, Schuller M P,etal.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masonry-infilled RC frames[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996, 122(3): 228-237.
[9] Al-Chaar G, Issa M, Sweeney S. Behavior of Masonry-Infilled Nonductile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s[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02, 128(8): 1055-1063.
[10] 閆帥平,夏文娟,朱文靜, 等. 輕質填充墻框架自振周期折減系數的取值研究[J]. 土木工程與管理學報, 2012, 29(2): 103-107.
[11] Zarnic R, Tomazevic M, Velvechovsky T. Experimental study of methods for repair and strengthening of masonry infilled reinforced concrete frames[M]. The 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Lisbon: 1986.
[12] Dow J L, Mcbride R T.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hear resistance of masonry panels in steel frames[M]. The 7th International Brick/Block Masonry Conference. 1985.
[13] Moghaddam H A. Lateral Load Behavior of Masonry Infilled Steel Frames with Repair and Retrofit[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04, 130(1): 56-63.
[14] 唐興榮,楊亮,劉利花,等. 不同構造措施的砌體填充墻框架結構抗震性能試驗研究[J]. 建筑結構學報, 2012,33(10): 75-83.
[15] 郭猛. 框架-密肋復合墻結構抗震性能與設計計算方法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學, 2011.
[16] Riddington J R, Bolourchi M. Use of lead to reduce vertical load transfer in infilled frame structures[J]. Proc. lnstn Civ. Engrs, Part 2, 1989, 87(Dec): 627-640.
[17] Sahota M K, Riddington J R.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using lead to reduce vertical load transfer in infilled frames[J].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001, 23(1): 94-101.
[18] 周云,郭陽照,楊冠男,等. 框架阻尼填充墻減震效果分析[J]. 建筑結構, 2015,45(10): 74-80.
[19] 蔣歡軍,毛俊杰,劉小娟. 不同連接方式砌體填充墻鋼筋混凝土框架抗震性能試驗研究[J]. 建筑結構學報, 2014,35(3): 60-67.
[20] 姜俊銘,馬建勛,付靚, 等. 柔性連接的配筋砌體墻混凝土框架抗震性能理論研究[J]. 科學技術與工程, 2015, 15(8): 103-110.
[21] 周曉潔,李忠獻,續丹丹,等. 柔性連接填充墻框架結構抗震性能試驗[J]. 天津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版, 2015,48(2): 155-166
[22] Loo Y C, Yao B Z. Static and Repeated Load Tests on Precast Concrete Beam-to-Column Connections[J]. Journal of precast/prestressed Concrete lnstitude, 1995, March-April(2): 106-115.
[23] Oliva M, Gavrilovic P, Clough R W. Seismic testing of large panel precast walls: Comparison of pseudostatic and shaking table tests[J].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dynamics, 1990, 19: 859-875.
[24] 黃宇星,祝磊,王元清,等. 懸掛式預制混凝土墻板框架抗震性能分析[J]. 建筑結構學報, 2014,35(S1): 137-142.
[25] 于敬海,丁永君,李久鵬,等. 設置耗能外掛墻板結構的抗震性能[J]. 天津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版, 2015,48(S1): 122-126.
[26] 王立忠,羅健. 高層鋼結構房屋中鋼筋混凝土外掛板的減振作用[J]. 建筑結構學報, 1995, 16(2): 70-76.
[27] 羅健. 鋼筋混凝土外掛板摩擦恢復力特性試驗及減震效果[J]. 北京建筑工程學院學報, 1997,13(2): 44-54.
[28] 李國強,方明霽,劉宜靖,等. 鋼結構住宅體系加氣混凝土外墻板抗震性能試驗研究[J]. 土木工程學報, 2005,38(10): 31-35.
[29] 謝全懿. 框架結構掛板式圍護結構掛板式圍護結構減震性能試驗研究[D]. 北京: 北京工業大學, 2016.
費愷(1976~),教授級高工,碩士研究生校外導師,研究方向為預制裝配式結構。
劉嘯(1990~),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預制裝配式結構。
TU375.4
A
[定稿日期]2017-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