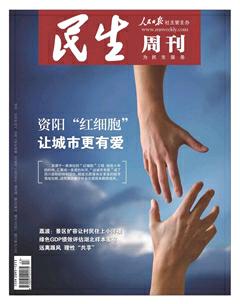氣候治理合作共贏
趙慧
6月1日,不顧各方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將退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盡管業界分析認為,此次不大可能出現當年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時多國跟風的情況,但這無疑已給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再次“添了堵”。
6月18日,在生態文明試驗區貴陽國際研討會期間召開的氣候治理與低碳發展專題研討會上,多位中外專家表示,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對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使得應對氣候變化進程面臨巨大的減排、資金缺口。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巴黎協定》的最終生效起了關鍵促進作用,始終致力于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不少國際氣候專家及分析人士就此認為,在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中國完全可以填補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帶來的空白。
對此,中國的態度一如既往,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初在瑞士達沃斯論壇演講時所言,“《巴黎協定》符合全球發展大方向,成果來之不易,應該共同堅守,不能輕言放棄。這是我們對子孫后代必須擔負的責任。”
“無論其他國家政府態度發生了怎樣變化,中國都會堅定推進氣候變化全球合作,推進合作共贏、公平正義、共同發展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建設。” 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方寧在專題研討會上表示。
強調共贏的中國態度
去年11月4日,《巴黎協定》正式生效,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當時輿論普遍贊揚,《巴黎協定》展現了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將在人類氣候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然而僅僅過去半年,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就宣布退出,無疑給這一努力進程帶來負面影響。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分析,美國宣布不再履行原來的自主減排承諾,一方面可能會影響相當多的國家,減少他們加大減排力度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美國也宣布不再對發展中國家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這使得《巴黎協定》提出的到2020年由發達國家負責籌集每年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目標難以實現。
“這樣就會影響發展中國家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就會使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受到阻礙。”何建坤說。
據分析,美國退出將使全球各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面對3個巨大缺口。一是減排缺口,要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2攝氏度溫升目標,目前各國自下而上確定的自主貢獻目標并不夠;二是資金缺口,美國退出后,要實現2020年1000億美元綠色氣候資金將面臨巨大缺口;三是領導力缺口。
在貴陽國際論壇期間,多位與會國際氣候變化專家表達了對特朗普政府退出舉措的失望甚至憤慨,指出美國退出后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將出現領導力真空。其中不少人士表示,期待中國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
在當日的專題研討會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副主席、巴基斯坦環保部原部長馬利克·阿明·阿斯蘭·汗表示,中國和很多其他國家都實現了合作,通過這些國際合作可以有效填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所帶來的空白,“我們將會看到,不僅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方面,而且在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方面中國將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對此,中國政府的態度則是決不輕言放棄,將一如既往地推動落實《巴黎協定》。
國務院參事室原副主任方寧說:“無論其他國家政府態度發生了怎樣變化,中國都會堅定推進氣候變化全球合作,推進合作共贏、公平正義、共同發展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建設。”
何建坤則表示,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主要出于兩個共贏的考量。一是每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要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走上低碳的發展路徑,實現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贏。
二是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全球合作,必須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責任義務的分擔方式,以實現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框架下的合作和共贏,共同發展。
生態文明中國行動
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以及由此展開的一系列減排、低碳、治污行動引起國際普遍關注。
在國內,中國不斷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開始努力探索一條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徑。
在國際上,中國則展現了作為發展中大國的責任擔當,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在《巴黎協定》的框架下,中國提出了強有力的自主減排目標:到2030年,單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2005年下降60%到65%,非化石能源比例達到20%,并努力爭取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爭取盡早達峰。
目前,調整和轉型已經初見成效。2010年到2015年,中國單位GDP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強度分別下降18.1%和21.6%,超額完成了“十二五”規劃的16%和17.%的目標。
“到2016年底,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42%,已基本實現了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承諾的到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目標。”萬寧說。
2005年到2013年,中國能源消費每年的增長率約6%,2013年到2016年,由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和GDP增速的放緩,能源消費年增長率降至1.5%。
“由于在此期間能源結構快速調整,總能源需求放緩,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仍然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這就使得能源結構調整加速,二氧化碳的排放在這3年之內基本持平,而且還有可能略有下降。”何建坤說。
中國出臺了2016年到2030年的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確立了未來大比例非化石能源的發展目標,提出到2030年發電中50%的電量來自非化石能源,到2050年,總能源供應中超過一半來自非化石能源。
何建坤表示,2030年和2050年兩個50%的目標對我們能源結構調整起到積極的引領作用。
過去幾年,中國新能源發展速度空前。2010年以來,水電實現年均10%左右增長,核電年均增長20%,風電年均增長接近30%,光電增長190%多,生物質發電增長27.8%。
與此同時,中國煤炭消費增長速度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本世紀初,中國能源和煤炭消費均為兩位數增速,但“十一五”期間就降至7%左右,“十二五”期間只有3%左右,到2016年,僅增長了1.4%。
此外,今年中國將啟動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市場手段促進溫室氣體減排。
綠色低碳不可逆轉
盡管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阻礙不斷,與會專家們仍普遍認為,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廣泛共識和強烈的政治意愿,能源變革和低碳發展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
何建坤觀察到,雖然特朗普政府作出了退出《巴黎協定》的決定,但“新的自下而上,包含美國的各個州、城市、企業、社會團體層面的自愿行動也會促進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進程”。
可盡管如此,《巴黎協定》提出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硬性指標,即控制全球的溫升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2攝氏度,并努力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對各國經濟發展而言的確是十分嚴峻的挑戰。
這意味著,到本世紀下半葉要實現溫室氣體近零排放。“對能源系統而言,就要結束化石能源時代。能源體系要基本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這種不含碳的能源為主體,來實現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低碳轉型。”何建坤說。
他認為,新能源的發展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并提供新的就業機會,綠色發展已經實現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人民生活改善等多方面的紅利分享。
而對于中國的能源發展趨勢,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吳吟則給出兩個初步判斷。其一,中國可能由煤炭時代跨越油氣時代直接進入可再生能源時代。“現在煤炭占的比重較高,新能源發展又較快,因此中國有可能跨過油氣時代,直接進入可再生能源時代。”
其二,中國有可能以較低人均能源消費實現工業化。吳吟談道,美國、加拿大等國人均消費10噸標煤后開始出現下降,德國、日本大概是人均消費5噸標煤后實現下降。
“我們去年是人均消費3.15噸標煤,而且現在這個曲線變得比較平緩,所以我們可能會以低于歐盟、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費完成工業化。”
那么,如何做到綠色低碳發展?吳吟預測,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的出現,能源智能化應用將成為可能。根據初步保守核算,實現智能化后將節約能源至少15%。除此之外,能源技術領域的一系列突破也不容忽視,如生物質燃料、可燃冰、石墨烯電池等技術研發已經起步且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