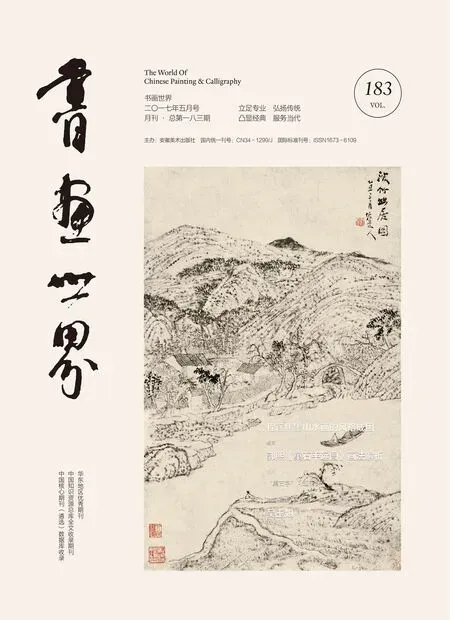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石濤《苦瓜和尚書畫冊》考釋
羅春輝
贛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石濤《苦瓜和尚書畫冊》考釋
羅春輝
贛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石濤是中國繪畫史研究的熱點,本文將對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石濤《苦瓜和尚書畫冊》進行考釋,結合石濤的遺民身份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對石濤的藝術風格進行解讀。本文認為,石濤在《苦瓜和尚書畫冊》中通過圖像不斷暗示其宗室遺孤的身份,以適應市場對“遺民繪畫”的需求。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明末清初以來藝術商品化的審美趣味以及畫家為適應這種趣味所做出的策略性選擇。
石濤;苦瓜和尚書畫冊;藝術風格;遺民;徽商
石濤(1642—1708),清初畫家,廣西桂林人,原名朱若極,別號有苦瓜和尚等。石濤是中國繪畫史研究的熱點。《苦瓜和尚書畫冊》,紙本冊頁,設色或水墨,尺寸為16.5厘米×10.5厘米,共12幅,右圖左詩。為日本桑名鐵城舊藏,富岡鐵齋題書名“石濤道人書畫神品”,現為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苦瓜和尚書畫冊》除少數學者偶有引用外,并未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與系統全面的研究。本文將以《苦瓜和尚書畫冊》為中心,結合石濤的遺民身份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對石濤的藝術風格進行解讀。
一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一,此頁描繪了一位士人乘船過小橋,周圍環境幽遠迷離,左側賦詩道:“落葉隨風下,殘煙蕩水歸。小亭依碧澗,寒襯白云肥。石濤。”鈐印:石濤、原濟、釋元濟印。
此頁以干淡而短粗的筆觸勾勒山石形體,繪出一片沒有清晰輪廓線的陸地,再加上云霧橫隔,從而模糊了山峰、叢林的界限,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不真實感。中國文人自古有“托喻”的傳統,將風景、時事融入人情經驗中。從渡江初克神州的愿景,對故都的遙望,到國破山河在的無奈,深植于石濤孤寂心靈的這些“殘山剩水”,正是歷經戰亂蹂躪后的山河景象。而這種荒疏氛圍的營造,正是明遺民畫家與清朝統治者之間政治對抗的情感表現。“落葉隨風下,殘煙蕩水歸”,世風日下,作為宗室遺孤的石濤,將何去何從?“小亭依碧澗,寒襯白云肥”,只有在那幽遠迷離的幻境中,才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從而與歷史對話,為因明清易鼎而受創的心靈尋求一個慰藉的場所。冊頁的開篇即以亦幻亦真的山水來引發對個人身世的感慨,沉浸于回憶與思念之中。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二,此頁描繪梅竹雙清,左側賦詩曰:“初試一朵兩朵,漸看十田五田。落日霞明遠映,與余筆墨爭先。石道人。”鈐印:釋元濟印、苦瓜和尚濟畫法。
梅花作為史可法從容就義的象征物,被遺民們視為對清廷毫不妥協的標志與符號。石濤所繪梅竹雙清有別于時風,講求“野逸”的趣味,可視為對清廷的不妥協。石濤背負著文化重建的使命感,在異族統治下,希望通過“野逸”“怪異”的繪畫風格來反思大明帝國的潰敗,希望以此來傳承漢族傳統文化。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三,此頁描繪圓錐形的山峰,高山仰止。左側題詩曰:“山高秀色寒,白云飛不白。清湘道人濟。”鈐印:原濟、石濤、釋元濟印。
石濤所描繪的圓錐形的山峰與桂林一帶的喀斯特地貌相似。眾所周知,石濤所出身的靖江王府就坐落在桂林城內喀斯特地貌最突出的獨秀峰下,這一事實也加強了這種山形對他的獨特意義。由此可見,此畫仍是他作為宗室遺孤對前朝的體認和追憶。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四,此頁為幽蘭圖,左側題詩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蘭之意,其合永歡。子宜佩之,保護春寒。春風寒兮,誰謂乎安。苦瓜老人濟。”鈐印:原濟、石濤、前有龍眠濟。
自屈原不見用于楚王,作《離騷》以見志,文中便提及蘭花。宋末遺民鄭思肖,借繪畫來表達他與元朝統治者的勢不兩立,以“無根蘭”來寄托其故國之思。“蘭花”在石濤眼里,不僅是堅貞、清正與不群,更是宗室遺孤的節操。此頁蘭花用筆秀勁清潤,姿態蹁躚,別具一格。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五,此頁描繪雅士渡江,左側題詩曰:“潦倒清湘客,因尋故舊過。買山無力住,就枕宿拳寧。放眼江天外,賒心寸草亭。扁舟偕子顧,而且不鴻丁。停書之過登舟故爾。白沙江村留別。枝下人濟。”鈐印:石濤、元濟、釋元濟印。

石濤 苦瓜和尚書畫冊(一 至四)10.5cm×16.5cm×41695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5-12石濤 苦瓜和尚書畫冊(五至十二)10.5cm×16.5cm×8 1695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此頁是整本冊頁的關鍵所在,文中所稱“白沙江村”,即安徽富商鄭肇新的儀征別業“白沙翠竹江村”。據石濤生平年表可知,石濤于1695年夏日拜訪了鄭肇新,秋天返回揚州。由此可斷定整本冊頁應作于1695年前后。“買山”典故出自《世說新語》,以“買山隱”暗指賢士歸隱。“買山無力住,就枕宿拳寧”,畫家此詩贈予鄭肇新,無疑可當作門客書畫家對于藝術贊助人的禮貌性贊揚,同時也是畫家向鄭肇新尋求支持的見證。另外,“枝下人”的落款,是以懷念南京一枝閣的歲月。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六,此頁為荷花圖,左側題詩曰:“花葉田田水滿溝,香風時擊采蓮舟。一聲歌韻一聲槳,驚起白云幾片浮。白沙江村采蓮舟中寫意。瞎尊者,濟。”鈐印:原濟(二次)、石濤(二次)。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荷花具有天然之美,而“蓮之出淤泥而不染”,又賦予荷花潔身自好的高貴品質。除此之外,荷花在禪宗中被譽為神圣凈潔之花,常常作為開悟的視覺隱喻。石濤身為臨濟宗弟子,通過荷花將禪學與質疑傳統的精神徹底地圖像化。石濤把自己放在與古抗衡的位置上,用堅定不移的態度破除偶像迷信,追尋古代真理的頓悟和傳統的再創造。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七,此頁山水繪荒亭江邊之景。左側題詩曰:“荒亭岑寂荒山里,老樹無花傍水磯。飯后尋幽偶到此,十分寒苦慘斜暉。石濤濟。”鈐印:原濟、石濤、頭白真然不識字。
此頁山水畫眼居于畫面上面的三分之一處,構圖新奇,意境蒼莽野逸。山石部分濕筆點苔繁密,下面江水大面積留白,形成強烈的視覺對比,石濤以這種頗不尋常的視覺圖像來組織畫面,可視為抗拒清朝俗世的象征。“頭白真然不識字”的印文,透露出自己未曾讀書,天性粗莽,不事修飾,也表達一種禪宗的情感。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八,此頁為菊花圖。左側題詩曰:“九月寒香露太真,東籬晚節可為鄰。從來天地無私運,梅菊同開一樣春。九月梅花二首之一。瞎尊者,原濟。”鈐印:頭白真然不識字、苦瓜和尚濟畫法。
此頁以濕筆描繪菊花,包含著隱隱的哀傷,效仿陶淵明隱居之心躍于紙上。菊花作為“寒香”,一直被傳統文人視為“殘存”的象征,在這里可以對照石濤最后一代殘存的明遺民。這種借菊花來寄托隱居的哀傷是這一代畫家所特有的視覺圖像標志。石濤此畫是藝術與思想和諧深化而趨完美的典范,寄托著石濤的文人理想和重建文化的使命感。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九,此頁為高士圖。左側題詩曰:“新長龍絲過屋檐,曉云深處露峰尖。山中四月如十月,衣帽憑欄冷翠沾。清湘小乘客濟。”鈐印:石濤(二次)、原濟。
明朝以“孝”治天下,士人們把蓄發當作孝行。明清鼎革所帶來的剃發留辮,讓士人們感到恥辱和無法接受,石濤也借助僧服隱姓埋名。透過此頁,我們可以看到畫中人物的衣著和發型,都與清廷規定的服飾有所區別。在石濤身處的遺民畫家世界中,以這種不合作的姿態來對抗清廷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做法。“山中四月如十月,衣帽憑欄冷翠沾”,在山中效仿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飽含深情的詩文使得畫境異常凄清。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十,此頁為疏竹圖。左側題跋道:“此幀擬李營丘而有別意。美人素質,淡妝流麗。漫爾效顰,不免氣縮。濟。”鈐印:原濟、石濤、釋元濟印。
李成畫法簡練,好用淡墨,氣象蕭疏。此頁仿李成所作竹子,得其神韻。筆調看似稀松平常,卻并非完全脫離“形”而專求“意”,而是在“形”的基礎上去表達內在的意趣。從竹干、竹枝到竹葉的刻畫,毫無麻、蘆之感,使人感受到的是實實在在的竹子和畫家胸次超逸的性情。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十一,此頁為設色山水。左側題跋道:“山色蒼蒼樹色秋,黃云欲碎背溪流。苦瓜客舍消閑筆,畫法應愧老貫休。瞎尊者,原濟。”鈐印:原濟、石濤、苦瓜和尚。
此頁即是石濤山水畫風格的典型。在此幀作品中,高聳的峭壁與瀑布之間的動態轉換,不禁讓人想起荊浩的畫風。石濤以清新的色彩、不規矩的墨色效果和非傳統的構圖,造成對傳統的挑戰。這種對乾元伊始、萬象更新的渴望,正是石濤生活、藝術和繪畫理論的核心。從某種角度而言,這種繪畫上的返璞歸真和推倒重建包含著他對明朝復辟的期待。
《苦瓜和尚書畫冊》之十二,此頁為水仙圖。左側題跋道:“君與梅花同賞,歲寒時許爭夸。暖日晴窗拈筆,幾回清思無涯。小乘客,濟。”鈐印:原濟、石濤、頭白真然不識字。
冊頁的最后以水仙花作為結束,不禁讓人想起南宋皇室遺民趙孟堅,趙氏在宋代亡國之后以水仙作為國破家亡的忠貞圖像,石濤在畫中也多少保留有這種象征含意。畫中一簇冰清玉潔的水仙,蘊含著石濤貴族身份與遺民角色的隱喻。
二
石濤是明室胄裔,幼習禪宗。然他始終未能安心隱居,而是四處云游,主動尋求社會的承認與藝術上的突破。在這套冊頁完成之前,石濤已經在南京、北京、揚州這三個重要的城市及書畫商業中心建立起一定的影響力。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七月中下旬,石濤與先著、顧惺等友人共游白沙翠竹江村。康熙初年,安徽富商鄭肇新新建“白沙翠竹江村”,園內有十三景。石濤在此創作并題《白沙翠竹江村十三景》,傳為美談。
石濤在《苦瓜和尚書畫冊》的每一幀中,從主題的選擇到形式的處理,都不斷暗示其宗室遺孤的身份。那么,石濤到白沙翠竹江村休閑度假,為什么要繪制這樣一套充滿遺民象征氣氛的冊頁呢?事實上,徽商與清朝士紳是對遺民繪畫有強烈需求的兩個群體。徽州地區風氣保守,恪守傳統儒家觀念,衍生出對遺民的強烈同情。同時,由于“士農工商”的階級制度,社會對商人存在著偏見,于是徽商大力推行文化教育。而當時清朝士紳對遺民繪畫的贊助,恰恰滿足了他們在文化上忠于漢室的心理需求。因此,遺民繪畫除了相互酬唱的社會功用外,還涉及士大夫內部的政治立場、民族認同等問題。徽商是石濤在揚州時期交往最多的一個群體,除了鄭肇新,石濤還跟徽商中的許、汪、江、吳諸家保持長期的友誼。這本《苦瓜和尚書畫冊》是石濤與徽商之間交往的見證,更為重要的是,“遺民”這一特殊的道德立場,是石濤等畫家進入揚州這類藝術市場的基礎與優勢。石濤對自我身份的強調,尋求徽商與清朝士紳的民族認同,不單是知己之間精神的互動,也是為了適應藝術市場對“遺民繪畫”的需求。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明末清初以來藝術商品化的審美趣味以及畫家為適應這種趣味所做出的策略性方案。
結 語
這套《苦瓜和尚書畫冊》,無論是筆墨語言,還是格調畫境,都是石濤精心之作,絕不同于那些隨意涂抹的應酬之作中。同時,該冊頁是石濤與徽商(畫家與贊助人)之間關系的見證,也是遺民繪畫在揚州這個商業城市中深具魅力的表征,從中可以看到石濤為適應這種趣味所做出的策略性選擇。因此,這套《苦瓜和尚書畫冊》是研究石濤書畫藝術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品。
約稿:金水畫廊 責編:徐琳祺、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