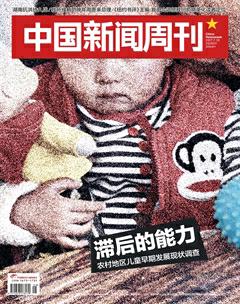全球秩序再思考
哈維爾·索拉納
前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北約前秘書長,西班牙前外交部長,現任ESADE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中心主席,布魯金斯學會杰出研究員
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所觀察的那樣,近幾十年來“美國治下的和平”已經岌岌可危。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更準確地說是“美國孤立”政策。在此政策出臺后,美國扮演的傳統的穩定角色已經無法被視為理所當然了。
由于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首要地位以及因此而享有的世界“不可或缺國家”地位遭到了動搖,因而其他國家乃至非國家行動者都紛紛開始聚斂勢力。而這對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
不斷增加的多極化,不一定就與包容性和互惠互利的全球體系相抵觸。例如,中國這樣新崛起的大國就擁有足夠的條件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而似乎正在重建自身信心的歐盟也仍然可以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在國際關系理論中,自由國際主義的特點就是對開放和秩序的推動,這也成為了各國際性多邊組織的信條。二戰結束后,這些原則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隨后發展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等眾多條約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
冷戰極大地阻礙了自由國際主義的全球化雄心。1989年11月柏林墻的倒塌,開啟了美國無可爭議的霸權時代,為西方治理結構的推廣擴散鋪平了道路。但是,這種擴散卻并未像預期的那樣迅速而廣泛地打開局面。
如今,世界依然呈現碎片化的狀況。2001年的“9·11”襲擊事件使得許多國家紛紛向美國靠攏。但這些襲擊也揭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發展趨勢,這一趨勢向著那些由意料之外的行為者觸發的破壞行為發展,而且在隨后的15年中愈發被強化。
國家之間的分歧同時也是經濟上的。就連2007~2009年的經濟衰退也并不像發達國家過往所認為的具有那樣大的全球影響——當全球GDP在2009年出現下跌時,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卻都實現了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
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當選反映出人們對全球化的一些經濟和社會影響的沮喪,例如離岸外包行為。這種失望重新激起了一種基于排斥心理的民族主義形式。重振威斯特伐利亞式主權的論調正在四處蔓延,導致一些人預測大國競爭將再次成為當今秩序。這個思想流派的支持者經常將美中關系視為最可能的導致摩擦的根源。
但是這一觀點有點神經過敏了。雖然中國的上升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激起了極大的不信任感,但是中國力量的顛覆性可能不會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強大。比如,中國最近就與特朗普政府劃清界限,重申本國對美國計劃撤出的巴黎氣候協議的支持。
而在今年1月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標志性演講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成功地樹立了其作為全球化堅定捍衛者的形象。習近平指出,各國不應“犧牲別人來為自己謀利益”。
中國政府很清楚自己的國家通過與全球經濟的深度整合獲益良多,也沒打算拿自身國內的經濟增長去冒險。習近平“一帶一路”的倡議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加強與歐亞大陸及非洲地區各國商業聯系的戰略選擇,也意欲借此機會積累軟實力。
即便如此,中國也沒有去公開質疑自由秩序的根基。通過今年5月參加“一帶一路”峰會的世界各國領導人共同發表的標志性的公報,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承諾致力于“維護和平正義,加強社會凝聚力和包容性,促進民主、良政、法治、人權,推動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
但單從字面上理解這個公報,而忽視中國的新重商主義傾向也許是有失偏頗的,但另一方面,把中國視為一個與西方價值觀完全不符的孤立整體也是不正確的。過度簡化的解讀對于中國而言并不準確,正如美國雖然是特朗普當選,但其實希拉里·克林頓贏得的民眾選票更多;又如英國雖然公投脫歐通過,但其實還有很多人想留在歐盟,他們僅僅是以最微弱的劣勢敗北而已。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和沖突的時期,歐盟有能力擔當起主導作用。伊曼紐爾·馬克龍在法國總統大選中的勝利應該讓那些自由秩序的維護者們感到鼓舞,因為他們的事業盡管存在種種缺陷,卻依然是國際關系中最具吸引力和靈活性的范式。
一個團結的歐盟也可以幫助催化改革,振興那些當前舉步維艱的多邊機構并為它們注入新的動力。如果我們能與新興國家聯手,那么,建立真正的全球秩序還為時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