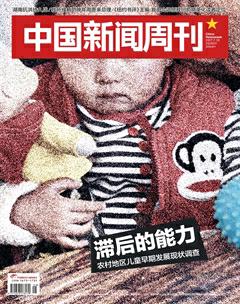古典自由主義的延續:《紐約書評》迎來新主編
康慨
相較其他美國名刊,更具全球視野的《紐約書評》一向較多地
關注中國事務。新主編布魯瑪就任后,由于自身的東方學背景,
也由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不斷增強,可以預見的是,
《紐約書評》關于中國的文章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54年前的一天,小說家伊麗莎白·哈德威克與道布爾戴出版社的文學編輯芭芭拉·愛潑斯坦在紐約的哥倫布街不期而遇,于是約了飯。當晚,哈德威克帶上詩人丈夫羅伯特·洛厄爾,來到同住西六十七街的芭芭拉和賈森·愛潑斯坦夫婦家串門。正是這頓即興的晚餐,催生出一份享譽全球的知識分子名刊。
席間,兩對夫婦不可避免地談到了仍在進行中的紐約印刷工人大罷工,《紐約時報》及《時報書評》已被迫停刊,知識分子突然斷了精神食糧,出版社也沒地方刊登圖書廣告,積攢下了大筆的營銷預算。賈森·愛潑斯坦不無揶揄地說,這樣也好,總算告別了《時報書評》帶來的沮喪,因為就在不久之前,哈德威克在《哈潑斯》雜志上痛斥《時報書評》充滿了“千篇一律的贊揚和模糊無力的異議,風格闕如,輕描淡寫,一帶而過,不投入,沒熱情,無性格,也不反常,總之就是沒有文采。”由于嚴肅書評的衰落,“一本書生下來便掉進了蜜罐”。
“我們四人看到了罷工帶來的天賜良機:創辦一份莉齊(指伊麗莎白·哈德威克)想要的那種書評媒體,不然就永遠別再抱怨。”賈森·愛潑斯坦在50年后回憶,“機會——其實是責任——已經擺在了面前,我們沒有視而不見。”
《紐約書評》就此創刊,宗旨很清楚,就是“莉齊想要的那種書評媒體”。四君子從《哈潑斯》挖來羅伯特·西爾弗斯(正是他向哈德威克約了那篇名作《書評的衰落》),與芭芭拉·愛潑斯坦擔任聯合主編。1963年2月1日創刊號上的45位作者不僅大名鼎鼎,文風亦極具個性。以喬納森·米勒評約翰·厄普代克的小說新作《馬人》為例,文章第一句話寫道:“這是一部糟糕的小說,卻被某些很好的特色惱人地玷污了。”
1998年,大作家諾曼·梅勒在《紐約書評》刊出長文,評論湯姆·沃爾夫厚達750頁的新作《完美的人》:“閱讀此作,甚至可以說,這就像和一個三百磅重的女人做愛。一旦她到了上面,房事就結束了。不是墜入愛河,就是窒息身亡。所以你讀啊,抓啊,你甚至在這堆疊的素材/肉體的某些地方發現了樂趣。可你一直在抵抗——你拼命抵抗!——不肯讓三百磅把你壓服。”
另一位大作家約翰·厄普代克也就《完美的人》寫了書評,刊于《紐約客》雜志,題為《好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Awriiiiighhhhhhhhht!),但畢竟不像梅勒那樣,用活色生香的文字將讀者帶進一個泰山壓卵、氣若游絲的境地。
不間斷的批評
西爾弗斯與愛潑斯坦同為主編,但各有分工,前者長于政治和歷史,后者偏重文學和文化。《紐約書評》關心政治,放眼世界,珍重文化,拒斥油滑、媚俗的形象很快贏得了知識階層的厚愛。
如果細看《紐約書評》的刊頭(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人人都能注意到“書”字(of Books)被有意縮小了字號。的確,如西爾弗斯所說,該刊每期都會發表兩三篇不是書評的評論,以進一步拓展本已十分寬泛的主題。
“此前當然有過偉大的雜志,尤其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西爾弗斯編過一段時間的《巴黎評論》。”愛爾蘭作家和布克獎得主約翰·班維爾說,“但《紐約書評》是個獨一無二的現象:不留余地的知識分子化,政治上的激進,以高調的紐約風尚表現出的與眾不同,以及對文明價值的全身心投入。”

1963年,芭芭拉·愛潑斯坦(左)和羅伯托·希爾弗斯在《紐約書評》最早的辦公室里。
創刊54年來,《紐約書評》總是及時地參與、甚至發動對最緊要議題的爭論。大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和大衛·泰代斯基在2014年拍攝的紀錄片《五十年辯論》(The 50 Year Argument )中,回溯了《紐約書評》歷史上的多次重大論爭:埃德蒙·威爾遜就俄文翻譯與納博科夫辯論,愛德華·賽義德就東方主義與伯納德·劉易斯辯論,諾曼·梅勒就婦女解放與戈爾·維達爾辯論,戈爾·維達爾則就任何事情與整個世界辯論。
旅美荷蘭作家和東方學家伊恩·布魯瑪曾贊揚西爾弗斯在緊要關頭往往表現出色。例如,布什發動反恐戰爭之初,《紐約書評》便抱以懷疑的態度,而當時即便《紐約時報》這樣的自由派媒體,也不敢這樣發聲,唯恐被人說成不夠愛國。
《紐約書評》的懷疑態度在越戰期間表現得格外鮮明。諾姆·喬姆斯基曾在該刊寫下名言:“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相,揭露謊言。”瑪麗·麥卡錫1967年發回報道,公然聲稱:“我坦白我在2月初去越南就是要尋找損害美國利益的素材,我找到了。”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希特勒的御用導演萊妮·里芬施塔爾到了美國,準備以攝影家的身份東山再起,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直到蘇珊·桑塔格以“道德上的迫切”發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將里芬施塔爾新拍的非洲土著攝影集與她30年代用紀錄片為納粹效命時的政治美學聯系在一起,直言她對健美人體和生命活力的迷人呈現暗藏著對秩序、暴力和奴役的渴望。
桑塔格早在浪跡巴黎期間便與西爾弗斯結識,后來成了《紐約書評》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從創刊號上關于法國作家西蒙娜·韋伊的書評開始,到她2004年底去世,桑塔格共為該刊撰文57篇,其中包括《論攝影》(1973)、《作為隱喻的疾病》(1978)在內的多篇名作。這些文章后來都另行出版了單行本,成為20世紀美國文化批評史上的經典之作。
《紐約書評》鼓勵作者撰寫長文,讓形式服從于主題和深度,五十年來發表書評一萬篇,散文七千篇、信函四千封、詩歌六百五十首和報告文學二百篇,作者隊伍中還包括WH·奧登、索爾·貝婁、威廉·斯蒂倫、歐文·豪、以賽亞·柏林、杜魯門·卡波特、瓦斯拉夫·哈韋爾、JM·庫切、林培瑞、讓-保爾·薩特、瓊·迪迪翁、德里克·沃爾科特、瑪格麗特·阿特伍德、VS·奈保爾、羅納德·德沃金、謝默斯·希尼、蒂莫西·加頓·阿什和托尼·朱特等。
“我們都認為,”賈森·愛潑斯坦說,“書籍就是不間斷的批評,是文明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我們想辦一份與其宗旨相配的書評雜志,讓我們欣賞的作者有這樣一個地方,用充足的篇幅,來為像他們和我們這樣的讀者寫作。”
布魯瑪將帶來什么
自創刊之日起,芭芭拉·愛潑斯坦和羅伯托·西爾弗斯便一直擔任《紐約書評》主編。愛潑斯坦于2006年6月、西爾弗斯于今年3月先后去世后,《紐約書評》終于任命伊恩·布魯瑪為該刊54年歷史上的第二代和第三位主編。
65歲的布魯瑪生于荷蘭海牙,曾在萊頓大學著名的中文系學習中國文學,后赴日本求學,還在唐十郎的狀況劇場和麿赤兒的舞踏團大駱駝艦里做過演員,現任紐約巴德學院保羅·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被視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捍衛者。
2008年,布魯瑪獲得了聲名顯赫的伊拉斯謨獎,為他頒獎的是奧蘭治親王威廉-亞歷山大(現荷蘭國王)。
他是《紐約書評》的老作者了,為該刊撰稿的時間長逾30年,與愛潑斯坦和西爾弗斯保持著密切交往,熟悉《紐約書評》的風格和取向,因此,他出任主編是個相對平穩的選擇。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時,布魯瑪說,他肯定會引入年輕一代的作家,“不是拿走老作家們的陣地,而是逐漸接納年輕的作家,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不同的遠景。”
相較其他美國名刊,更具全球視野的《紐約書評》一向較多地關注中國事務。布魯瑪就任后,由于自身的東方學背景,也由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不斷增強,可以預見的是,《紐約書評》關于中國的文章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事實上,就在今年6月19日的《紐約客》雜志上,布魯瑪發表了一篇長達6頁的文章,以《與龍共舞》為題,評論近期在美國出版的中國主題圖書,并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今年夏天出版的新作《必有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稱為一系列壞書中“最壞的一部……盡管也是影響最大的”。
布魯瑪所著《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面具下的日本人》《伏爾泰的椰子:歐洲的英國文化熱》《罪孽的報應: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和《零年:1945 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已見中譯本,但他兼具新聞調查和政治隨筆特色的重要著作《阿姆斯特丹的謀殺:特奧·凡·高之死和寬容之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他關于中國的多部著作不在其中。他甚至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小說《愛中國的人》(The China Lover),主人公是生于偽滿洲國的日本演員山口淑子,即李香蘭或雪莉·山口。
至于執掌《紐約書評》后的工作風格,我們也看不出布魯瑪會主動推行過于激進的改變。事實上,在2014年的紀錄片《五十年辯論》中,他對西爾弗斯一人主事且事必躬親的風格頗為贊賞。
“很多雜志的問題在于它們往往由編委會來編輯,”以作者身份出鏡的布魯瑪說,“你會得到這樣的反饋:‘嗯,感覺這個開頭放到最后更好。然后他們回過頭來又說:‘嗯,我們開了個會,我們認為也許我們不要這個開頭也行。這種事情過于頻繁地發生,就會對你產生抑制,因為你下一次寫東西的時候,就會開始預測他們要干什么。你說:‘嗯,我是要這么寫的,但我相信他們肯定會答復說:嗯,我們覺得……鮑勃(西爾弗斯)從來不這么干。因為就他一個人。就一個主編,而你信任他。他也信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