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他們很孤獨
何映宇
盡管孤獨,但至少他們孤獨的堅持證明,在被流行文化籠罩的東方之珠香港,也并非鐵板一塊,與強大的流行文化一起,各種思潮各種文化的沖撞融合,發(fā)出耀眼的火花,它的名字,叫香港。
2008年2月,香港“青文書屋”老板羅志華在大角咀合桃街貨倉整理書籍期間,疑遭20多箱塌下的書本壓困,失救致死,尸體一直藏于貨倉無人得知。直至大廈保安聞到惡臭報警,才發(fā)現(xiàn)羅志華死在書叢中。
消息傳來,香港文化界同仁一片哀聲,賣書者死于書堆中,是一種黑色幽默?還是死得很有文學性的表現(xiàn)?
與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熱銷相對應的,是香港嚴肅文化的整體衰微,就像羅志華螺螄殼里做道場的“青文書屋”,在香港喧囂的都市夾縫中求生存,而終于被這座城池所吞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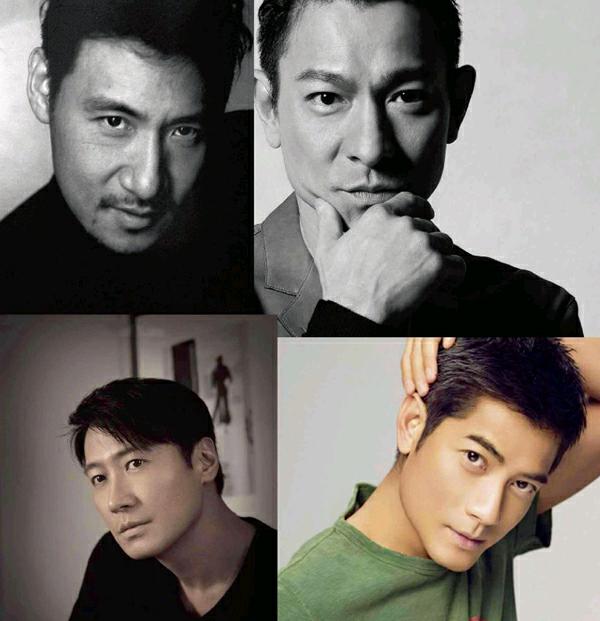
香港出版,何去何從?
在彈丸之地的香港,書店是奢侈的存在。
香港有所謂二樓書店,二樓書店多躋身于鬧市中的二樓,圖個鋪租便宜,卻成全了鬧中取靜的愿望。無論在旺角或銅鑼灣,抬頭就能在霓虹燈中找到書店招牌。狹窄的樓道口通往二樓——這就是具有濃郁香港文化特色的二樓書店。以出售流行讀物、文藝書籍為主的田園書屋、以藝術、劇場、設計、當代文化研究圖書為主的阿麥書房就是其中的代表。20多平方米的狹小空間成了香港文化的一個坐標,在如此狹小的空間里堆滿了書,就像這座城市的人口一樣,如此高密度的壓迫感,而阿麥書房居然還能在這樣的空間里舉辦文化活動,陳綺貞還在那面橙色墻下唱《花的姿態(tài)》,讓很多文藝界人士在這里聚集,天馬行空,高談闊論,也實在要佩服他們高效的空間利用能力了。
青文書屋也是香港著名的二樓書店。45歲的羅志華由1988年開始接手青文書屋,跟出版行業(yè)有關的范疇,他幾乎都做過。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文化視野系列”,從找作者、編輯出版以至發(fā)行,他都一手包辦。而青文書屋可說是文藝青年及作家的聚集地,但因為租約問題,于2006年8月31日結業(yè)。
愛書如命的羅志華遂把數以千計書籍暫時搬到合桃街2號一個約100平尺的分租貨倉,繼續(xù)經營等候機會再次開店,不料到貨倉收拾時死于書堆中。
但這并不表示香港的出版業(yè)不發(fā)達。香港現(xiàn)已成為世界出版中心之一,由香港貿易發(fā)展局主辦的香港書展,是亞洲最大型書展之一,是香港每年夏天的一項盛事,吸引近百萬讀者前來參觀購書。而香港出版及印刷業(yè)已經成為香港四大支柱產業(yè)之一。本土的圖書銷售額已占香港圖書銷售總量的50%。在數字出版方面,香港出版業(yè)呈現(xiàn)出三大特色:電子出版走內容為主體的軟件開發(fā)道路;在數字技術和營銷平臺的搭建方面與世界保持同步發(fā)展水平;數字出版在教育領域發(fā)展迅猛,已成功進入中小學日常教學領域,近1/3教材用書實現(xiàn)了數字化應用。
以兩岸三地來說,香港的出版空間最小,圖書出版公司數來數去也只有十多家,市場需求偏低,讀者群的口味狹窄,出版社處于被動的狀態(tài),因而可以看到一個趨勢:出版社以出版童書、生活類圖書迎合讀者口味,純文學或翻譯小說主要還是倚賴內地、臺灣出版社發(fā)力,版權競爭激烈。香港出版最大的問題可以用三個詞語涵蓋——讀者、作者、市場。
香港的出版社,一切都是從無到有的,就像天地。
1976年正式成立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最初出版一些時事評論方面的著作,部份當代西方思想普及讀物﹙如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弗洛伊德等﹚,紹介新思潮﹔也出版一些翻譯文學作品,如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政壇要人的回憶錄﹙戴高樂《希望回憶錄》等﹚﹔后來有於梨華的留學生文學,有亦舒、梁羽生的愛情和武俠小說,巴金的《家》《春》《秋》﹙后又出版《巴金小說全集》﹚,然后是李碧華和蔡瀾加入,于是一年年發(fā)展壯大。
這些年來,天地圖書公司的宗旨基本上是兩條腿走路,一是流行讀物,出暢銷作家的暢銷書,另一條是人文學科的著作,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心理、文學等。流行讀物方面,亦舒的愛情小說系列已出到220多部、武俠名家梁羽生共有作品35部、古龍的系列有60部。李碧華的小說和散文迄今也有五六十部之多,而蔡瀾的散文集積累下來,也高達60余部。另外一位值得重視的愛情小說作家李敏,她的作品由人間社出版,天地圖書發(fā)行,李敏的作品也累積了30余部。
《明報》是金庸創(chuàng)辦的,他的小說自然成為明報出版社的吸金法寶。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是臺灣皇冠出版社在香港的分支機構,皇冠出版社社長平鑫濤即瓊瑤的先生,旗下?lián)碛斜姸嘀骷遥绛偓帯垚哿帷⑷⒛呖铩⒏哧枴埪辍⒑钗脑仭堑纭埿埂⒗畋倘A等等,再加上翻譯引進的米蘭·昆德拉、彼得·梅爾、艾柯等作家的暢銷書,足以使它們成為港臺出版界的代表性機構。
和內地一樣,近年來香港傳統(tǒng)出版社也受到互聯(lián)網的沖擊,香港出版從業(yè)者也為何去何從感到彷徨。一方面他們也在積極謀求轉型,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堅守著香港出版的傳統(tǒng),當然,這不容易,在旁人看來熱鬧風光的出版業(yè)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艱苦付出。
陳冠中的雙城記
曾經創(chuàng)辦《號外》雜志的陳冠中從香港搬到了北京居住了,覺得北京的文化氛圍更適合他。
他是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著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后來創(chuàng)辦《號外》雜志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后來他寫電影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
也許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游歷豐富,但卻不太張揚,無論干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yè),最后都總是好像甚么事都沒有發(fā)生過一樣。
但自從2000年陳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tǒng)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顏,開啟了香港集體反思的精神運動。
也許正是因為身處兩地的關系,在兩邊,他都是個旁觀者,這樣才更能看出其中的端倪。他覺得兩岸三地的中文大同小異,只是各自表述而已。
當然其中差異性還是存在的:“香港在1949年之前廣東以外的外省人并不多。太平洋戰(zhàn)爭前,這里才是一個100多萬人的城市。1949年之后,廣東以外大量的外省人來到香港,而且他們大都是文化界的人,香港的文化氛圍就不一樣了。這一批‘南來文人對于建立香港的文化有很大功勞,他們把上海帶到了香港,幫助了香港的建設。臺灣也是這樣,1949年有軍隊有政府過去,他們各省的文化就更強一點。臺灣人對大陸的省份比香港人更清楚,香港主體還是廣東人,他們一說上海就說他們是北方人,像我小時候就一直以為上海是北方,我們分不出省份的。臺灣人對四川人、東北人他們都分得很清。香港人不太能分得出來,他們眼中只有廣東人、非廣東人,再就是外國人。”
而現(xiàn)在,改革開放之后,兩岸三地的文化差異在慢慢縮小,香港在變化,而中國內地也受到港臺文化的影響,北京在創(chuàng)新,在吸收外來文化,而所有創(chuàng)新都是混雜的結果。陳冠中說所以現(xiàn)在北京的情況一定和外來文化、改革開放有關。1980年代之后的歷史背景,在北京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波希米亞文化,北京聚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為了理想來到北京。他覺得這有點像西方的波希米亞文化,像19世紀的巴黎。他看到的北京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族群——波希米亞北京。
這其中,就有香港文化的影響,不論是大眾流行文化,還是小眾波希米亞文化,兩座城市,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不能說誰強誰弱,更多的,是交流增多后必然的產物。
前衛(wèi)文化逆襲主流市場
正因為有陳冠中這樣善于冷靜反省的作者的存在,所以才讓梁文道覺得:“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并不是它沒有文化。不只有,而且很厲害。”
文化沙漠是這樣一種狀態(tài):一片沙子,但其中有寶石,拿起來看,很漂亮,但是沙形成不了土壤,不會長出樹來,而香港不是。
“香港是個典型的大眾社會。700萬人,和一個北歐的國家差不多,說這個地方是彈丸之地所以搞不了文化是錯誤的。”梁文道對記者說,在梁文道看來,從廣義上來說,流行文化當然也是文化:“文化雅俗的區(qū)分在后現(xiàn)代時期已經被顛覆。我們今天面對的情況是,大家都很同情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特別是在文化研究興起之后,大家都認為雅俗的區(qū)分是一種霸權的產物,我們不應該瞧不起流行文化。但現(xiàn)在有這樣一種傾向,反過來流行文化成為一種霸權了。任何人一搞小眾的高雅的藝術就被人批評你是精英,你是古代的恐龍,會被人罵,脫離社會脫離大眾。我認為你可以不歧視大眾文化,但不能反過來就可以說精英文化是毫無價值的。大眾文化我感興趣的不是它的審美價值,而是它的工業(yè)運作。真正良性的運作,大眾文化是會促進非主流文化的生存的。比如好萊塢的電影工業(yè),大學畢業(yè)生一開始只能做獨立電影,搞這樣的電影是賺不到錢的,那么怎么辦?你會發(fā)現(xiàn)會有一些基金會愿意投資,它們這樣做是希望有一天你不會那么另類,你會變成大導演,它們覺得這個投資是值得的。為什么它們會有這種感覺。因為好萊塢有這樣一個隱形的樓梯,從獨立電影起步,然后去圣丹斯這樣的電影節(jié)參展,電影界的大亨就在那兒看片,看到有潛質的導演,就會給他機會。但香港不是這樣,它沒有階梯。”
盡管如此,在香港強大的流行文化之下,還是有一些小眾的藝術團體能夠存活,并且發(fā)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榮念曾擔任藝術總監(jiān)的前衛(wèi)文化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ZuniIcosahedron)。
“榮念曾是實驗藝術的祖師爺,”梁文道對記者說,“香港有兩岸三地最早的實驗劇場、獨立錄像、新媒體、行為藝術。裝置藝術這個詞是香港人翻譯的,‘同志這個名詞是林奕華翻譯的。在香港,有很多人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被大眾認同。饒宗頤也在香港,但他們很孤獨。”
“進念·二十面體”成立于1982年,主要成員有榮念曾、李歐梵、林奕華、胡恩威、靳埭強、劉小康等人,其中有詩人、小說家、先鋒戲劇導演、設計師,活躍于兩岸三地藝文圈的漫畫家歐陽應霽是“進念”成員,還有奪走多個填詞大獎、與林夕不相伯仲的詞人黃偉文,同為“進念”成員,不同行業(yè)的前衛(wèi)之士聚集起來,一同逆襲主流市場,也成為不可小覷的一支力量,30多年屹立不倒,堪稱香港文化的奇跡。
跨界是他們最大的特征。1987年,林奕華與達明一派合作的舞臺劇《石頭記》成為進念發(fā)展史上的里程碑,不僅觀眾人數創(chuàng)紀錄,也首開請流行歌手加盟前衛(wèi)藝術的先河。此后,不少進念成員相繼參與了達明一派音樂創(chuàng)作,包括何秀萍、周耀輝、于逸堯、梁基爵等,他們之后亦成為楊千嬅、陳奕迅、盧巧音等新一代香港流行歌手的幕后功臣。還有“進念”的編劇魏紹恩也是電影《越快樂越墮落》、《藍宇》的編劇,自《阿飛正傳》起一直參與王家衛(wèi)電影的制作。
盡管孤獨,但至少他們孤獨的堅持證明,在被流行文化籠罩的東方之珠香港,也并非鐵板一塊,與強大的流行文化一起,各種思潮各種文化的沖撞融合,發(fā)出耀眼的火花,它的名字,叫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