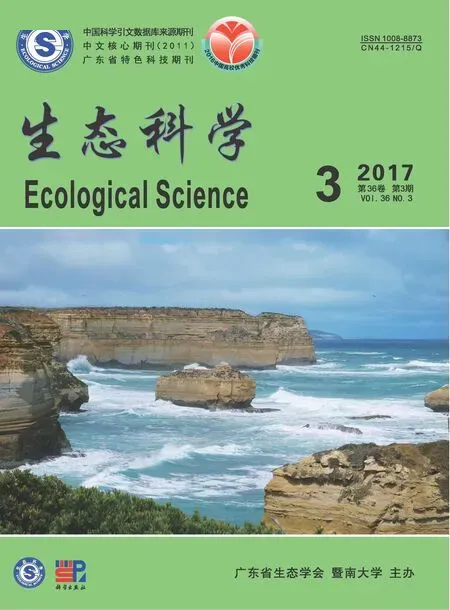儲存溫度與時間對市售飲用礦泉水和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王雪平, 閔敏, 孫雅婷, 范漪, 余在旺, 賀美,2,*
1. 長江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 武漢 430100
2. 油氣資源與勘探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長江大學), 武漢 430100
儲存溫度與時間對市售飲用礦泉水和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王雪平1, 閔敏1, 孫雅婷1, 范漪1, 余在旺1, 賀美1,2,*
1. 長江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 武漢 430100
2. 油氣資源與勘探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長江大學), 武漢 430100
由于飲用便捷、水質潔凈、富含微量元素等優點, 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深廣大消費者的青睞。但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并非任何情況下都適宜飲用。例如, 飲用時應以不加熱、冷飲或稍加溫為宜, 不宜煮沸飲用; 儲存時應置于干燥陰涼通風處,避免陽光直射。文章以兩種市售飲用礦泉水與兩種市售飲用純凈水為研究對象, 采用礦泉水或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作為評價指標, 主要針對炎熱的夏天汽車內高溫與暴曬的儲存條件, 研究了儲存溫度與儲存時間對市售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結果表明, 兩種礦泉水與兩種純凈水儲存于 50—70 ℃的大部分條件下, 均呈現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均釋放出有毒物質。且隨著儲存溫度的升高, 它們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增強, 說明釋放出的有毒物質含量更高、毒性更大。而儲存時間為1—5 d時, 對兩種礦泉水與兩種純凈水有毒物質的釋放影響不明顯。這為人們選擇合適的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儲存條件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對于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安全飲用具有重要意義。
礦泉水; 純凈水; 塑料; 儲存溫度; 儲存時間; 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1 前言
水與人體健康的關系非常密切, 是人體必須的六大營養物質之一。其中, 礦泉水與純凈水由于具有飲用便捷、水質潔凈、富含多種微量元素、價格優惠等特點, 深受廣大消費者的青睞。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們消費水平和保健意識的提高, 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的產量越來越大, 人們對市售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消費量也越來越大。但是, 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并非任何情況下都適合飲用的。例如,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時, 應以不加熱、冷飲或稍加溫為宜, 不宜煮沸飲用。另外, 對于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的儲存也是有講究的, 一般而言, 應儲存于干燥陰涼通風處, 避免陽光直射。若飲用礦泉水或純凈水儲存不當, 在飲用過程中可能會存在潛在的安全風險。
飲用礦泉水中含有一定量的礦物鹽, 富含微量元素或者二氧化碳氣體, 在通常情況下, 其化學成分相對穩定。但是當它們的儲存溫度發生變化或儲存時間過長時, 飲用礦泉水可能會釋放出有毒物質。研究表明, 礦泉水反復加熱后, 會產生亞硝酸鹽。亞硝酸鹽是強致癌物質, 與人類健康有直接關系。它可以將血紅蛋白中的亞鐵氧化為高價鐵, 從而使血紅蛋白失去輸氧能力, 造成人體缺氧中毒等[1–2]。新鮮桶裝礦泉水亞硝酸鹽含量為零, 加熱一次后含量依然為零, 第二次加熱后生成亞硝酸鹽, 并且隨著加熱次數的增多而亞硝酸鹽含量升高。在24 h內,第52 次加熱后, 檢測其亞硝酸鹽含量已經接近國家規定標準含量的一半, 與冷水中亞硝酸鹽的零含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
飲用純凈水是純潔、干凈, 不含有雜質或細菌的水, 是以符合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的水為原水,通過電滲析器法、離子交換器法、反滲透法、蒸餾法及其他適當的加工方法制得而成的水, 不含任何添加物, 無色透明, 可直接飲用。市售純凈水瓶或礦泉水瓶多采用PET、PE、PP材料制成, 含有微量的催化劑、增塑劑、阻燃劑、熱穩定劑、抗氧劑等塑料添加劑成分[4]。通常情況下, 這些成分相對溫度。但當環境溫度發生變化或放置時間過長時, 礦泉水瓶或純凈水瓶可能會釋放出有毒有害物質。一般而言, PET、PE、PP材料制成的瓶子只能耐受一定的溫度, 加熱后易變形, 可能會釋放出增塑劑、阻燃劑等對人體有毒的成分[4–5]。另外, 塑料瓶包裝易受外界因素的影響, 在環境儲存條件發生變化時, 其內部殘留的揮發性有機物(VOCs)可能向礦泉水或純凈水遷移, 在人們不慎飲用時給人體健康帶來潛在的危害[6]。研究表明, 飲用瓶裝水在長時間儲存溫度高于70 ℃時, 塑料瓶會發生變形并釋放出銻和雙酚A等有毒物質[7]。總之, 市售飲用礦泉水或純凈水若儲存時間過長、儲存溫度反復變化, 可能會導致水體本身或者純凈水瓶與礦泉水瓶釋放出對人體有害的有毒物質。
本研究選取了兩種市售飲用礦泉水與兩種市售飲用純凈水為研究對象, 主要針對炎熱的夏天汽車內高溫與暴曬的儲存條件, 研究了不同高溫儲存溫度(50—70 °C)與不同儲存時間(1—5 d)對市售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本研究中, 飲用礦泉水、飲用純凈水及礦泉水瓶、純凈水瓶在儲存溫度變化或儲存時間過長時, 可能會釋放有毒有害物質, 但這些有毒物質并非單一的毒物。本研究將礦泉水或純凈水中的所有有毒物質看成一個整體,通過混合體系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來評價它們有毒物質的釋放, 比直接分析儲存條件變化后各種有毒物質成分的變化更有意義, 更直接地反映了儲存溫度與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也更直接地反映了有毒物質釋放后的礦泉水或純凈水對人類健康的影響。總之, 該研究結果可為人們選擇合適的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儲存條件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對于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安全飲用具有重要意義。
2 材料與方法
2.1 實驗材料
兩種市售飲用礦泉水與兩種市售飲用純凈水,購自武漢中百超市, 均為國內銷售量較大的品牌。購買的飲用礦泉水符合瓶裝飲用天然礦泉水衛生標準GB 8537–2008[8], 購買的飲用純凈水符合飲用純凈水衛生標準GB 17324–1998[9]。
藻類生態毒性試驗生物采用斜生柵藻(Scenedesmus obliquus), 由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提供。藻類培養基與藻類測試液的試劑主要有: 氯化銨(NH4Cl)、氯化鎂(MgCl2·6H2O)、氯化鈣(CaCl2·2H2O)、磷 酸 二 氫 鉀 (KH4PO4)、硫 酸 鎂 (MgSO4·7H2O)、FeCl3·6H2O、Na2EDTA·2H2O、硼酸(H3BO3)、氯化錳(MnCl2·4H2O)、氯化鋅(ZnCl2)、氯化鈷(CoCl2·6H2O)、氯 化 銅 (CuCl2·2H2O)、鉬 酸 鈉 (Na2MoO4·2H2O)、NaHCO3, 均為分析純。
2.2 實驗方法
2.2.1 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測定
本研究主要采用藻類生態毒性試驗, 通過測定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來研究并比較不同儲存溫度與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具體過程如下:
2.2.1.1 受試藻類的準備與培養
參照《化學品測試方法》及OECD(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推薦的生態毒理測試方法[10–11], 如表1所示, 將貯備液1、貯備液2、貯備液3、貯備液4配制成藻類培養基, 用0.22 μm的濾膜過濾除菌后, 接種4 ℃冰箱中保存于瓊脂糖固體培養基的斜生柵藻,置于光照培養箱中培養, 培養條件為溫度(20 ± 2 ) ℃、光照強度8000 lx、光暗比光照為12: 12, 每天振蕩若干次。斜生柵藻經過反復活化后, 7—10 d轉接一次, 以保持藻類生長良好, 隨時有足夠的數量可用于試驗。
2.2.1.2 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的測定
(1) 斜生柵藻的藻細胞數量與光密度的關系
反復活化后的斜生柵藻, 利用藻類培養基進行培養后, 鏡檢其生長狀況, 用血球計數板進行藻細胞數量計數, 用分光光度計(上海元析儀器有限公司UV—5500PC)測定650 nm波長下的藻類光密度(OD值), 確定藻細胞數量與光密度(650 nm波長)的線性關系。
(2) 藻試驗液的配制
藻試驗液即用于藻類生態毒性測試的藻培養物,對藻類進行預培養后, 鏡檢其生長情況, 用分光光度計測定650 nm波長下藻類的光密度, 利用藻細胞數量與光密度(OD值)的線性關系, 推算預培養的藻細胞數量。
(3) 礦泉水或純凈水測試液的配制
測試液是用于測試礦泉水或純凈水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的液體。參照藻細胞數量與光密度的線性關系, 以蒸餾水作為對照, 先在每個三角瓶中加入合適體積的處于對數生長期的藻試驗液, 使礦泉水、純凈水測試液、對照中藻細胞數量的終濃度均約為104個·mL–1(±25%), 且測試液與對照中的藻細胞濃度保持一致。再往每個三角瓶中分別加入1 mL貯備液1、100 μL貯備液2、100 μL貯備液3、100 μL貯備液4(表1), 并在每個三角瓶中分別加入適量的待測試的礦泉水或純凈水樣品, 使測試液的終體積均為100 mL。每個測試液樣品準備3個平行樣。

表1 藻類培養基Tab.1 The algae medium
(4) 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的測定
測試液配置好后, 將測試液置于光照培養箱,培養條件為溫度(20 ± 2) ℃、光照強度8000 lx、光暗比光照為12: 12, 試驗開始計時。每天振蕩若干次。分別于試驗開始后的0 h、24 h、48 h、72 h及96 h, 從每個三角瓶中取樣, 用分光光度計測定各組藻液在650 nm波長下的光密度(OD值)。礦泉水或純凈水測試液在測定OD值時, 以未加藻試驗液的礦泉水或純凈水作為空白對照, 扣除測試液的本底吸光值, 測定的OD值即為藻液的OD值[12–13]。
2.2.2 儲存溫度對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將同批購置的兩種飲用礦泉水分別準備18 瓶,共分為6個組, 每組3 瓶礦泉水平行樣。第一組礦泉水不經任何加溫處理, 放置在室內常溫條件下(25 ℃),作為對照組。另外的各組礦泉水分別放置于50 ℃、55 ℃、60 ℃、65 ℃、70 ℃的烘箱中加熱處理5 天。處理后的礦泉水樣常溫冷卻后, 采用藻類生態毒理方法測試并比較不同礦泉水樣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來研究50—70 ℃溫度范圍內儲存溫度對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飲用純凈水的加溫處理過程同飲用礦泉水。
2.2.3 高溫下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將同批購置的兩種飲用礦泉水分別準備18 瓶,共分為6個組, 每組3 瓶礦泉水平行樣。第一組礦泉水不經任何加溫處理, 放置在室內常溫條件下(25 ℃),作為對照組。另外的各組礦泉水放置于70 ℃的烘箱分別加熱處理1 d、2 d、3 d、4 d、5 d。處理后的礦泉水樣常溫冷卻后, 采用藻類生態毒理方法測試并比較不同礦泉水樣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來研究高溫條件下1—5 d內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飲用純凈水的加溫處理過程同飲用礦泉水。
2.2.4 數據處理
試驗數據均為3次重復的平均值±標準差。本研究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數據采用SPSS1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用Sigmaplot10.0作圖。
3 結果與討論
3.1 斜生柵藻的藻細胞數量與光密度的相關性
反復活化后培養的斜生柵藻, 采用Sigmaplot10.0對藻細胞數量與650 nm波長下的藻細胞OD值進行相關性分析, 結果表明藻細胞數量與光密度呈線性正關系, 相關性系數為0.99, 線性關系式如下所示:

式中, y表示OD值, x表示藻細胞濃度。
3.2 儲存溫度對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將飲用礦泉水或純凈水置于烘箱內, 儲存于不同溫度5 天。以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或純凈水作為對照, 測定不同儲存溫度下的礦泉水或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每隔24 h記錄各樣品的藻細胞OD值, 來研究不同儲存溫度對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3.2.1 不同儲存溫度對飲用礦泉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本文研究了常見的儲存溫度條件(50—70 ℃)下對飲用礦泉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及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如圖1-a與圖1-b所示, 以蒸餾水作為對照,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1與礦泉水2(not-treated water)在不同時間的藻細胞OD值均大于對照組(control)。這說明這兩種飲用礦泉水本身就對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具有促進作用, 且促進作用非常明顯。這可能主要與礦泉水中富含K、Na、Ca、Mg、Zn等微量元素有關[14–15]。有研究表明, K、Na、Ca、Mg、Zn等微量元素是藻類生長繁殖的重要營養元素, 也是藻類培養基中常見的營養鹽類, 如氯化鎂(MgC12·6H2O)、氯化鈣(CaCl2·2H2O)、氯化鋅(ZnC12)等是多種藻類培養基的重要成分。礦泉水中這些微量元素的存在促進了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16–18]。
如圖1-a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not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當礦泉水1在50 ℃、65 ℃、70 ℃的儲存溫度下儲存5 天后, 礦泉水1的這三組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的OD值均比對照低, 說明在這三個儲存溫度下, 礦泉水1釋放出有毒物質, 從而表現出一定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而在55 ℃、60 ℃的儲存溫度下儲存5 天后, 礦泉水1的這兩組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的OD值均比對照高, 說明在這兩個儲存溫度下, 礦泉水1非但沒有釋放出有毒物質, 反而使一些可能促進藻類生長繁殖的營養物質從礦泉水瓶或礦泉水中釋放出來, 反而促進了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 未呈現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圖1 不同儲存溫度對兩種市售礦泉水和純凈水中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的影響Fig. 1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on the algal toxicity of two commercial mineral water and two commercial purified water
如圖1-b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not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當礦泉水2在50 ℃、55 ℃、60 ℃、65 ℃、70 ℃的儲存溫度下儲存5 天后, 礦泉水2的這五組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的OD值均比對照低, 且隨著儲存溫度的升高, 斜生柵藻的OD值降低得越多, 對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抑制作用越強。這說明礦泉水2在儲存溫度升高后, 礦泉水2釋放出大量的有毒物質, 從而表現出較強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且儲存溫度越高, 礦泉水2釋放的有毒物質含量越高, 呈現越強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綜上所述, 兩種礦泉水儲存于50—70 ℃的大部分條件下, 均會產生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均會釋放出有毒物質。且兩種礦泉水的儲存溫度對其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呈現一定的差異。礦泉水1儲存于50 ℃、60 ℃、65 ℃時釋放有毒物質, 而礦泉水2儲存于50 ℃、55 ℃、60 ℃、65 ℃、70 ℃時均會釋放有毒物質。這種差異的產生原因可能是: (1)兩種礦泉水的成分不同, 且不同成分如鉀、鈉、鈣、鎂等元素離子在礦泉水中的含量也不同[14–15,19]。某些組分如重碳酸鹽、硝酸鹽、硅酸、鍶等的性質和含量在加溫儲存過程中可能發生了不同的變化[20]; (2)兩種礦泉水瓶的塑料材質不同, 在加熱儲存過程中, 可能釋放出來并遷移至礦泉水中的有毒物質也不同[7,21]。
3.2.2 不同儲存溫度對飲用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本文研究了常見的儲存溫度條件(50—70 ℃)下對飲用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及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如圖1-c與圖1-d所示, 以蒸餾水作為對照, 未置于烘箱的純凈水1與純凈水2(not-treated water)在不同時間的藻細胞OD值均大于對照組(control)。這說明這兩種飲用純凈水本身就對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具有促進作用, 且促進作用比較明顯。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飲用純凈水大多采用臭氧滅菌, 臭氧在空氣中的半衰期一般為20—50 min, 純凈水與空氣接觸后臭氧被分解成氧氣[22–23], 從而促進了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
如圖1-c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純凈水(not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當純凈水1在50 ℃、60 ℃、65 ℃、70 ℃的儲存溫度下儲存5 天后, 純凈水1的這四組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的OD值均比對照低, 說明在這四個儲存溫度下, 純凈水1釋放出有毒物質, 從而表現出一定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且在60—70 ℃儲存溫度條件下, 隨著溫度的升高, 斜生柵藻OD值呈下降的趨勢, 說明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強。由此可見, 隨著儲存溫度的升高, 純凈水1釋放出的有毒物質越多, 從而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增強。
如圖1-d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純凈水(no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當純凈水2在50 ℃、55 ℃、60 ℃、65 ℃、70 ℃的儲存溫度下儲存5 天后, 純凈水2的所有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OD值均比對照低,說明在50—70 ℃的儲存溫度下, 純凈水2均釋放出有毒物質, 表現出一定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且隨著溫度的升高, 斜生柵藻OD值呈下降的趨勢, 說明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受到的抑制作用增強。由此可見, 隨著儲存溫度的升高, 純凈水2釋放出的有毒物質越多, 從而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增強。
綜上所述, 兩種純凈水儲存于50—70 ℃條件下,均呈現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說明均釋放了有毒物質。且兩種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隨著儲存溫度的升高呈增強趨勢, 說明這兩種純凈水在儲存溫度升高的情況下加速了有毒物質的釋放。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的增加與有毒物質的釋放可能來源于兩個方面: (1)飲用純凈水大多采用臭氧消毒殺菌, 但臭氧消毒過程中常常會產生副產物如溴酸鹽、亞硝酸鹽等, 這些副產物具有一定的毒性[24–25]。研究表明,溫度超過50 ℃時會加速臭氧的分解, 導致更多有毒副產物的產生[26–27]。因此, 隨著純凈水儲存溫度的升高, 副產物的增多而對藻類的生長繁殖產生抑制作用, 增強了礦泉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2)瓶裝純凈水瓶均由PET、PP等塑料材質加工而成, 當純凈水的儲存溫度升高時, 塑料材質可能因為溫度的升高釋放出銣、雙酚A、正己烷、鄰苯二甲酸酯等有毒物質, 且溫度越高, 釋放出來并遷移至瓶裝純凈水的有毒物質含量越高、毒性越大[7,28–30]。
3.3 高溫下不同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將飲用礦泉水或純凈水儲存于高溫條件下, 置于70 ℃烘箱內。以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或純凈水作為對照, 測定不同儲存時間條件(1—5 天)的礦泉水或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每隔24 h記錄各樣品的藻細胞OD值, 來研究不同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3.3.1 高溫下不同儲存時間對飲用礦泉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本文研究了高溫儲存溫度條件下不同儲存時間(1—5 d)對飲用礦泉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及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如圖2-a與圖2-b所示, 以蒸餾水作為對照, 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1與礦泉水2(nottreated water)在不同時間的藻細胞OD值均大于對照組(control)。這說明這兩種飲用礦泉水本身就對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具有促進作用, 且促進作用非常明顯。這可能主要與礦泉水中富含K、Na、Ca、Mg、Zn等微量元素有關[14–15], 這些微量元素是促進藻類生長繁殖的重要營養元素[16–18]。

圖2 高溫下不同儲存時間對兩種市售礦泉水和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的影響Fig.2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duration on the algal toxicity of two commercial mineral water and two commercial purified water under high temperature
如圖2-a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not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當礦泉水1在70 ℃的儲存溫度下分別儲存1 d、2 d、4 d、5 d后, 礦泉水1的這四組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OD值均比對照低, 說明在高溫儲存條件下儲存時間為1 d、2 d、4 d、5 d時, 礦泉水1釋放出有毒物質, 從而表現出一定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而在70 ℃的儲存溫度下儲存3 天后,礦泉水1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OD值均比對照高, 說明高溫儲存3天, 礦泉水1非但沒有釋放出有毒物質,反而使一些可能促進藻類生長繁殖的營養物質從礦泉水瓶或礦泉水中釋放出來, 反而促進了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 未呈現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如圖2-b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礦泉水(not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當礦泉水2在70 ℃的儲存溫度下分別儲存1 d、2 d、3 d、4 d、5 d后, 礦泉水2的這五組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OD值均比對照低。這說明礦泉水2在高溫下儲存時間增長時, 礦泉水2釋放出大量的有毒物質, 從而表現出較強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綜上所述, 兩種礦泉水儲存于70 ℃的高溫條件下, 隨著儲存時間的增加, 會產生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釋放出有毒物質。但隨著儲存時間延長, 礦泉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并未增強, 可見儲存時間對這兩種礦泉水有毒物質的釋放影響不明顯。
3.3.2 高溫下不同儲存時間對飲用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本文研究了高溫儲存溫度條件下不同儲存時間(1—5 d)對飲用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及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如圖2-c與圖2-d所示, 以蒸餾水作為對照, 未置于烘箱的純凈水1與純凈水2(nottreated water)在不同時間的藻細胞OD值均大于對照組(control)。這說明這兩種飲用純凈水本身就對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具有促進作用, 且促進作用比較明顯。這可能是因為飲用純凈水大多采用臭氧滅菌, 純凈水中的臭氧與空氣接觸后被分解成氧氣[22–23], 促進了斜生柵藻的生長繁殖。
如圖2-c與2-d所示, 以未置于烘箱的純凈水(not-treated water)作為對照, 純凈水1與純凈水2在70 ℃的儲存溫度下分別儲存1—5 d后, 純凈水1與純凈水2測試液中的斜生柵藻OD值均比對照低, 說明在高溫條件下儲存1—5 d, 純凈水1與純凈水2均釋放出有毒物質, 表現出一定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但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并未隨著儲存時間延長而變大, 可見儲存時間對純凈水釋放有毒物質并無明顯影響。
4 結論與展望
本文以兩種市售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為研究對象, 采用藻類生態毒性試驗, 通過測定并比較不同市售飲用礦泉水與市售飲用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研究了儲存溫度(50—70 ℃)與儲存時間(1—5 d)對飲用礦泉水及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
1) 儲存溫度在50—70 ℃范圍內, 對兩種飲用礦泉水及兩種飲用純凈水有毒物質的釋放均產生較大的影響, 有毒物質可能是水體產生或是裝水的塑料瓶產生并遷移至礦泉水或純凈水, 使它們均產生了藻類生態毒性效應。
2) 50—70 ℃范圍內, 隨著儲存溫度的升高, 兩種飲用礦泉水及兩種飲用純凈水的藻類生態毒性效應增大, 釋放出含量更高、毒性更大的有毒物質。
3) 高溫儲存溫度70 ℃條件下, 儲存時間為1—5 d時, 對兩種飲用礦泉水與兩種飲用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無明顯影響, 藻類生態毒性效應無明顯變化。
本文的研究結果可為人們選擇合適的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儲存條件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對于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安全飲用具有重要意義。結果表明儲存溫度對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的安全至關重要, 但具體的影響機制尚不清楚, 還有待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另外, 飲用礦泉水與純凈水也常被置于一些高溫密閉空間如汽車內高溫暴曬, 影響是否與本文結果一致尚不清楚, 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1] 黃閩燕, 莫建芳. 離子色譜法測定飲用礦泉水中硝酸鹽的不確定性分析[J]. 職業與健康, 2011, 27(15):1729–1731.
[2] 蔡欣欣. 瓶裝飲用水中亞硝酸鹽污染的初步研究[J]. 化工時刊, 2002, 16(5): 51–52.
[3] 梁成可, 陳華. 飲水機反復加熱對桶裝礦泉水中亞硝酸鹽含量的影響[J]. 上海預防醫學雜志, 2007, 19(7):343–344.
[4] 張敏, 吳素芳, 邱建輝. 幾種主要塑料添加劑的毒性規律[J]. 應用化工, 2006, 35(9): 712–715.
[5] 張蘊暉. 鄰苯二甲酸二乙基己酯對環境和生物體的危害[J]. 國外醫學(衛生學分冊), 2002, 29(2): 73–77.
6] 謝利, 賈大鵬, 慈繼豪, 等. 可加熱塑料食品包裝中VOCs分析[J]. 包裝工程, 2014(1): 34–37.
7] FAN Yingying, ZHENG Jianlun.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n release of antimony and bisphenol A from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drinking water bottles of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4, 192:113–120.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飲用天然礦泉水[S]. GB 8537–2008, 北京, 中國.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瓶裝飲用純凈水衛生標準[S].GB 17324–1998, 北京, 中國.
10]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化學品測試方法[M].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4: 188–193.
11]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201 Alga Growth Inhibition Test[J]. Paris, 1984.
12] 閻雷生. 國家環境保護局化學品測試準則[M]. 北京: 化學工業出版社, 1990: 168–610.
13] ISO. 8692 Water quality – Fresh water algal growth inhibition test with Scenedesmus subspicatus and Selenastrum capriconutum[J]. 1989.
14] 苑連菊. 盤陀天然礦泉水特征及水化學成分形成的研究[J]. 太原工業大學學報, 1995, 26(4): 100–105.
15] 周林. 伊犁地區礦泉水中無機成分分析[J]. 干旱環境監測, 1992, 6(3): 139–146.
16] 程青. 城市景觀水體中微量元素的分布規律及其對藻類生長的影響研究[D]. 陜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2015:41–59.
17] 張鐵明. 微量元素-鋅、鐵、錳對淡水浮游藻類增殖的影響[D]. 北京: 首都師范大學, 2006: 13–34.
18] 黃振芳, 劉昌明, 劉波, 等. 鐵錳微量元素對淡水藻類的生長影響研究[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2009, Z1:607–611.
[19] 呂琳. 吉林省礦泉水區域與非礦泉水區域環境中礦物質元素含量分析[D]. 吉林: 吉林大學, 2015: 18–26.
[20] 邢大榮, 蘇豪浩, 徐賀榮, 等. 瓶裝天然礦泉水在保存期間某些成分變化的研究[J]. 環境與健康雜志, 2001, 3:145.
[21] 吳淑燕, 許茜, 陳天舒, 等. 尼龍6納米纖維膜固相膜萃取-高效液相色譜法測定塑料瓶裝礦泉水中雙酚A[J]. 分析化學, 2010, 38(4): 503–507.
[22] 朱居泉. 純凈水生產工藝技術[J]. 食品工業, 2003, 1:39–43.
[23] 韓鐵軍, 朱焰, 熊燕, 等. 純凈水臭氧消毒技術應用和衛生標準的探討[J]. 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 2006, 4:106–107.
[24] 張書芬, 王全林, 沈堅, 等. 飲用水中臭氧消毒副產物溴酸鹽含量的控制技術探討[J]. 水處理技術, 2011, 37(1):28–32.
[25] 魏蘭芬, 許激, 林軍明. 水中臭氧殺菌效果及產生亞硝酸鹽量的檢測[J]. 中國消毒學雜志, 2002, 37(1): 48–50.
[26] 薛峰峰. 飲用水水質變化規律和機理的研究[D]. 河北:華北電力大學, 2004: 18–47.
[27] 張暉, 楊卓如, 陳煥欽. 水中臭氧分解動力學研究[J].環境科學研究, 1999, 12(1): 17–19.
[28] 曹雪慧. 聚碳酸酯包裝材料中雙酚A遷移研究[D]. 遼寧:沈陽農業大學, 2013: 27–85.
[29] 閆楊娟. 長沙市液態食品塑料包裝安全性評價[D]. 湖南: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2013: 43–51.
[30] 徐宏景. 塑料食品包裝材料中鄰苯二甲酸酯的含量與遷移因素的研究[D]. 上海: 復旦大學, 2013: 21–34.
The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n release of toxic substances from commercial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
WANG Xueping1, MIN Min1, SUN Yating1, FAN Yi1, YU Zaiwang1, HE Mei1,2,*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Yangtze University, Wuhan 4301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for Oil and Gas Resources (Yangtze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Wuhan 430100, China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 are very popular because they are convenient and clean for drinking,and rich in trace elements. However, the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 are not suitable for drinking in any cases.For example, they are appropriate for drinking when they are cold or a little warmer, but not suitable for drinking after boiled.They should be stored in a cool, dry and ventilated place, avoiding direct sunlight. In this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n the release of toxic substances from two commercial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two commercial purified water were investiga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high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n the bottled water in hot summer, using the algal toxicity of the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release of the toxic substa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of the two mineral water and two purified water presented algal toxicities and released toxic substances under most of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50-70 ℃). And the algal toxicities of these water sampleswer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and the toxicities of the released oxic substances had raised resulting from the increase of the storage temperature. However, there was no obvious influence of he storage duration (1-5 day) on the release of toxic substances from two commercial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two commercial purified water.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people to choose suitable storage condition of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afe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
mineral water; purified water; plastic; storage temperature; storage duration; algal toxicity
10.14108/j.cnki.1008-8873.2017.03.003
X91
A
1008-8873(2017)03-015-08
王雪平, 閔敏, 孫雅婷, 等. 儲存溫度與時間對市售飲用礦泉水和純凈水有毒物質釋放的影響[J]. 生態科學, 2017, 36(3): 15-22.
WANG Xueping, MIN Min, SUN Yating, et al. The effects of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duration on release of toxic substances from commercial drinking mineral water and purified water[J]. Ecological Science, 2017, 36(3): 15-22.
2016-07-19;
2016-09-0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1472124); 中國石油科技創新基金研究項目(2015D–5006–0210); 湖北省自然科學基金(2016CFB178); 長江大學長江青年人才基金項目(2016cqr14)
王雪平(1993—), 女, 湖北恩施人, 本科在讀, 從事水文與環境相關研究, E-mail: wxuep18@163.com
*通信作者:賀美, 女, 博士, 副教授, 從事污染物生態毒理學研究, E-mail: hemei-5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