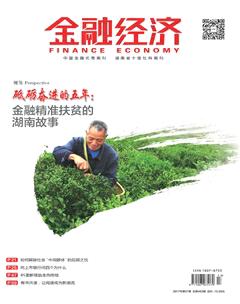如何解除社會“中間群體”的后顧之憂
蔡昉
我國提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xù)擴大”的要求,并將其作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高速經(jīng)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政府實施的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政策,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不斷擴大,標志著越來越多的群眾得以同步、均等地分享改革開放發(fā)展的成果。與此同時,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仍然存在著異質(zhì)性,對公共服務(wù)有著不盡相同的需求。為了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社會結(jié)構(gòu),在繼續(xù)依靠經(jīng)濟增長做大蛋糕、勞動力市場發(fā)育以改善收入分配作用的同時,也應(yīng)該思考如何分好蛋糕。
有缺陷的“中間群體”
關(guān)于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者,或者國際上所稱中產(chǎn)階級的人數(shù)和比例的估計,其實從來都只是一個定義的問題,使用不同定義進行估計,通常導(dǎo)致大相徑庭的數(shù)量結(jié)果。從學(xué)術(shù)界來看,有人嘗試依據(jù)人口的主觀感受來定義中等收入者,而更多學(xué)者則按照客觀收入或消費水平定義中等收入者,后者之中又有以相對水平定義的中等收入者概念,以及以絕對收入水平定義的中等收入者概念。應(yīng)該說,不同的定義分別來自不同的研究框架,有不盡相同的學(xué)術(shù)意圖和政策指向,當然也就對應(yīng)著不同的數(shù)字估計。
宏觀層面的數(shù)字像是森林,每一個個人或家庭則像是樹木。研究收入問題,關(guān)注的應(yīng)該是人本身及其在社會發(fā)展中的獲得感,所以不能只見森林、不見樹木。
嚴格來說,前述按照不同定義所做的各種界定,主要還是人口學(xué)意義上的中間群體。從我們意圖培育的、能夠幫助形成橄欖型社會結(jié)構(gòu)的中等收入群體來看,就業(yè)的安全性、收入水平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步性、享受基本公共服務(wù)的均等化程度、生育意愿與生育政策的一致性、對消費升級換代的支撐能力等維度,需要得到特別關(guān)注。換句話說,人口學(xué)意義上的中間群體,如果不能真正轉(zhuǎn)化為經(jīng)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一方面尚不能發(fā)揮橄欖型社會的功能,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其中的一些群體還會成為新的貧困人口。
例如,一個值得關(guān)注且與人口變化趨勢相關(guān)的中間群體是農(nóng)民工。以其為典型,可以分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間群體,揭示什么樣的改革和政策調(diào)整有助于把他們培養(yǎng)成中等收入群體。當下,普通勞動者工資加速提高,農(nóng)民工是主要的受益者。2015年,外出農(nóng)民工的平均月工資已經(jīng)達到3072元,按照購買力平價美元估算,平攤到每月30天中,每天工資收入已達29美元,即使按照一定的家庭贍養(yǎng)比來修正,折合成家庭人均收入,平均而言農(nóng)民工家庭也成為了中間群體。然而,以上述經(jīng)濟社會標準看,他們還是一個有缺陷的中等收入群體。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進行的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調(diào)查,與城鎮(zhèn)戶籍居民相比,外出農(nóng)民工的就業(yè)穩(wěn)定性不夠,與雇主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僅為39.7%;農(nóng)民工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wù),如觀察其參加基本社會保險的比例,工傷保險為26%,醫(yī)療保險為17.6%,養(yǎng)老保險為16.7%,失業(yè)保險僅為10.5%。因此,他們作為全部人口的中間群體,其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出來。
成長的煩惱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高速的經(jīng)濟增長和急劇的結(jié)構(gòu)變化帶動了就業(yè)的擴大和勞動者的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參與率提升。國外學(xué)者觀察到,歐美勞動力市場兩極化,高技能型崗位和低端部門非熟練崗位增長較快,中間層次崗位相對減少,美國的新增就業(yè)增長緩慢且?guī)缀鯚o一來自制造業(yè)等可貿(mào)易部門。但中國不一樣,中國的非農(nóng)就業(yè)在擴大,其分布在可貿(mào)易部門與非貿(mào)易部門比較平衡。
正是由于就業(yè)的擴大和參與率的提高,雖然經(jīng)歷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所有收入組都從收入的快速提高中獲益。然而,收入增長過程仍然有煩惱,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群體,有不盡相同的煩惱甚至焦慮。
處于較高收入組中的人群,仍然為日益高企的房價、年幼子女的入托入園、學(xué)齡孩子的高質(zhì)量教育憂心忡忡。
處于較低收入組的人群,則為看病難看病貴、就業(yè)技能跟不上崗位調(diào)整的步伐、贍養(yǎng)老人以及自己未來的養(yǎng)老煩惱不已。
更具體來說,各類群體各有各的煩心事。
農(nóng)民工為自己能否取得城市戶籍身份困擾,年輕夫婦抱怨生育二孩的負擔(dān),大學(xué)畢業(yè)生面對著就業(yè)的不確定性。當然,這些煩惱大多屬于成長中的煩惱,改善中的煩惱。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公共政策,也在積極地促進著事情的變化。然而,從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迫的時間表著眼,仍然需要實施更大力度、更廣泛意義上的再分配政策,才能在各類人口群體收入提高的同時,增進全體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迄今為止形成的龐大中等收入群體,是高速經(jīng)濟增長、勞動力供求關(guān)系變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政策的結(jié)果,已經(jīng)塑造了橄欖型社會結(jié)構(gòu)的雛形。然而,從使每個人都有參與感和獲得感來看,培育這個橄欖型社會結(jié)構(gòu)的中間人群,不僅要保持他們在當下收入意義上的中等水平地位,還應(yīng)該真正在就業(yè)、消費、生育、社會保障上,解除其后顧之憂,才能提高全體人民的社會總體福利水平,釋放消費潛力,發(fā)揮橄欖型社會結(jié)構(gòu)的功能。
用再分配政策增強經(jīng)濟發(fā)展的共享性
總體而言,隨著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疾風(fēng)暴雨式的勞動參與率擴大和收入增長階段已經(jīng)過去,提高居民生活質(zhì)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多地需要靠再分配政策,把人口意義上的中間群體轉(zhuǎn)化為經(jīng)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以增強經(jīng)濟發(fā)展的共享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wù)的均等化供給,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國際上在這方面有很多教訓(xùn)。在那些忽視再分配政策,任由勞動力市場制度退化的國家,收入分配惡化,經(jīng)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反而減少。這也正是一些國家給民粹主義政府上臺機會的原因。
無論是經(jīng)濟增長還是全球化,本身無疑都是有益的社會進步的過程,但是,這些過程同樣都不會自動產(chǎn)生涓流效應(yīng),不能自然而然保證每個人群自動均等獲益。因此,再分配政策首先應(yīng)該是一個獨立的政策取向。另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應(yīng)與時俱進,社會保護體系應(yīng)更加完善,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應(yīng)有所增強。這是一個具有規(guī)律性的政策演變趨勢,是形成和鞏固中等收入群體的關(guān)鍵。
這里所說的再分配政策,同時包括狹義和廣義的社會政策概念。首先是指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政策,諸如具有累進性質(zhì)的稅收政策等。
更重要的是廣義再分配政策,包括保護財產(chǎn)權(quán)和調(diào)動每個群體參與經(jīng)濟活動的積極性,推進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體制改革,實施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構(gòu)建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以及形成針對各個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體系。這類政策的共同特點是具有較強的外部性,看似不能從市場上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如果不是從單個的參與者或局部著眼,而是中國經(jīng)濟和社會整體來看,政策紅利則十分顯著。
第一,實施這些政策產(chǎn)生的結(jié)果,直接服務(wù)于發(fā)展的目的。正如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水平不能僅僅用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度量一樣,一個家庭的幸福感也不單純表現(xiàn)在收入水平上。以政府為主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特別是基本公共產(chǎn)品,可以同時在社會整體和個體兩個層面,增進公平公正,增強經(jīng)濟和社會安全感,拓展惠及每個家庭和個人的發(fā)展空間,是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中體現(xiàn)“全面”的關(guān)鍵。
第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如果從社會回報而非私人回報角度著眼,這類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能分別從供給側(cè)和需求側(cè)獲得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