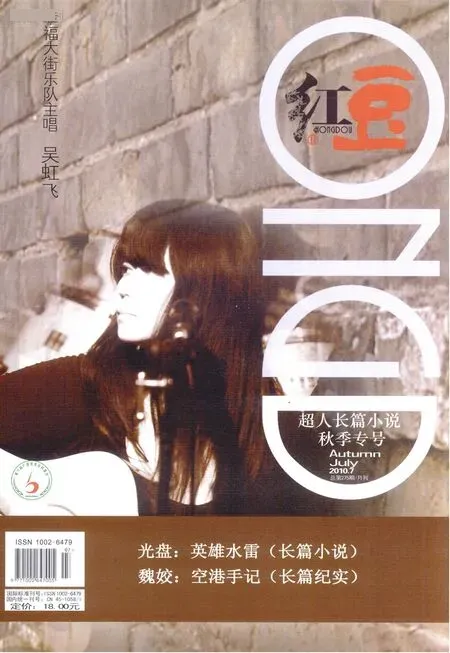先行者的眼光
馬力,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旅游報》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諸多報刊發表散文作品。著有散文集《鴻影雪痕》《南北行吟》《走遍名山》等,同時有散文理論著作《中國現代風景散文史》《山水文心》《什剎海的心靈行吟》等。
中國社會在進化的長途上跋涉了多少年代,直到近世,出洋的人忽然多了起來。這中間,有商輪上的船員,有使團里的翻譯,有傳教士的助理,有出國考察的技術人士,也有流亡海外的官吏和文人。這些乘風掛帆以觀異域者,成了首批開眼看世界的人,又都肩負著某種責任似的,將新鮮的見聞記錄成文字。故國的人受了這游錄的感染,知道了天下。昏昏的心醒覺了,驀抬頭,一面眺望天朝之外的廣域,一面審視安身立命的土地,神州的新聲便在胸腔深處隱隱蕩響。光明到來之前,在黑暗中向西方尋索真理的一派人物,抖擻精神,挺身時代潮頭。
謝清高:遠航的行記
謝清高是在大海上度著生涯的人。十幾個春夏,他隨葡萄牙商船在廓開的航路上出沒于風浪。遙遠的疆域中,風俗、民情、土產、人事和景物,那樣陌生,又那樣新異,烙刻于心底,成為抹不去的生命記憶。謝清高常常動情,卻因雙目失明無力執筆來寫,便拖著病體向梅州老鄉楊炳南逐一講敘,豐饒的見識從心里閃出光來,風逐陰云一般驅除了翳蔽在眼前的暗影。楊炳南筆之于文,一部《海錄》就這樣留給了歷史,廓開一條走向世界的路。
謝清高無意沾沾自喜于情節的傳奇性,不然,他的口述應當更為生動,保留清晰的歷史細節。即使這樣,國人仍可從他的憶敘中初識南洋的生活景況,領受歐洲的現代化氣息。所載既是海行的印象,簡略與零屑固屬難免,而在當時的中國,這部船工的遠航錄,卻如拂煦的風吹來,前路荒茫的人們定住神,眼光伸向未來。即便今天讀它,也仿佛被他的講述一路導引,揚帆朝著浩瀚的海面去。
謝清高《海錄》的出現,叫人第一次認識了中華之外的廣域。南洋群島、北印度洋、地中海諸國的形勝,破開閉塞的心界,人們的視野里,很多新的東西進來了。
記風俗。風俗最能觀察一國民眾生活之常,也最易觸著不容藏偽的實狀。有些與中國相近,有些則不同,竟至不免駭異。南洋某國的水葬之俗是這番光景:“有老死者,子孫親戚送至水旁,聚而哭之,各以手撫其尸,而反掌自舐之,以示親愛。”(《明呀喇》)夫婦之愛則以火化之儀表示:“更有伉儷敦篤者,夫死婦矢殉,親戚皆勸阻,堅不從則聽之。將殉,先積柴于野,置夫尸于上火之。婦則盡戴所有金銀珠寶玩飾,繞火行哭,親戚亦隨哭。極慟,見尸將化,婦則隨舉諸飾分贈所厚,而跳入火。眾皆嘖嘖稱羨,俟火化而后去。”(《明呀喇》)明呀喇,大體說,就是孟加拉國。此種場景為中土所罕見。彼地人民的道德觀約略可知。
記民情。民情最易體察出社會的狀況。在暹羅國(泰國),“俗尊佛教,每日早飯,寺僧被袈裟沿門托缽,滿則回寺奉佛”,且“頗知尊中國文字,聞客人有能詩文者,國王多羅致之,而供其飲食。”佛陀之外,儒風南漸,自會使人感覺親切。在新當國(印尼加里曼丹島),婚嫁自由帶來情感的爽適:“民居多板屋三層。約束子女甚嚴,七八歲即藏之高閣,令學針黹。十三四歲則贅婿。然必男女自相擇配,非其所愿,父母不能強也。”燭影搖紅之外,也演著慘烈的一幕:“合婚之夜,即以所居正室為新郎臥房。女父母兄弟俱寢于前室。女若不貞,婿嘗立行刺殺,或并殺其父母兄弟而去,無敢相仇者。”此段敘述,很為詳悉,連那亦喜亦悲的實景也能夠浮想。謹守古制的嫁娶遺風,脫不掉令人窒抑的原始空氣。讀到這里,覺得字句罩上陰影,心頭也壓了一塊石。在大西洋國(葡萄牙),“人死俱葬于廟中。有后來者,則擇其先葬者,取其骸,棄諸廟隅,而令后至者葬其處。”素持“慎終追遠”之德的中國人,不免以此為異。
記土產。土產最能表現一地的自然稟賦。本底國(柬埔寨)的象牙、翡翠、箭翎、班魚脯,暹羅國(泰國)的金、銀、鐵、錫、魚翅、鰒魚、玳瑁、白糖、落花生、檳榔、胡椒、油蔻、砂仁、木蘭、椰子、速香、降香、迦南香、象牙、犀角、翡翠,三巴郎國(印尼爪哇島三寶壟)的沉香、海參、沙藤、燕窩、蜜蠟、冰片,小呂宋(菲律賓馬尼拉)的烏木、蘇木、海參,大呂宋國(西班牙)的哆啰絨、葡萄酒、琉璃、番堿、鐘表,咩哩干國(美國)的白鐵、玻璃、洋參、鼻煙、羽紗、嗶嘰,亞咩哩隔國(巴西)的五谷、鉆石、金、銅、蔗、白糖……物之阜,仰賴于天靈的寵賜。
記人事。人事最切近民心。謝清高的行錄中,時見人物的面影,有些記敘頗類《世說新語》那樣的筆記調子。某島國,為華人淘金之所,“乾隆中,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于此。其人豪俠,善技擊,頗得眾心。是時嘗有土番竅發,商賈不安其生,方伯屢率眾平之。又鱷魚暴虐,為害居民,王不能制。方伯為壇于海旁,陳列犧牲,取韓昌黎祭文而焚之,鱷魚遁去。華夷敬畏,尊為客長。死而祀之,至今血食不衰云。”(《昆甸國》)若無這百十字略述,方伯之名不彰,其事不為后人曉也。昆甸東南有戴燕國,“乾隆末,國王暴亂,粵人吳元盛因民之不悅,刺而殺之,國人奉以為主,華人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至今猶存。”(《戴燕國》)閩粵人多出洋經商,留下的事功兼舊跡,被謝清高格外注意,成為《海錄》中的重要部分。
記景物。景物最能透出自然與人文氣象。爪哇島上,“海中有山,層巒疊巘,崒兀峻嶒,時有火焰,引風飄忽,入夏尤盛,俗呼為火焰山。”(《萬丹國》)倫敦“樓閣連綿,林木蔥郁,居人富庶。”(《英吉利國》)簡筆勾勒,亦能入妙,猶似在紙上繪出幅幅畫來。
地遼疆閡,阻隔了眼界,一部《海錄》改變了時人的觀念,始知天朝并不獨尊,更大的世界還在外面。有識者的胸襟,因之拓開。在廣州禁煙的林則徐,把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譯成《四洲志》,嗣后,魏源以此為據,“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將百卷本《海國圖志》編著出來。這部“縱三千年,圜九萬里,經之緯之,左圖右史”而成的地理志,述東南洋各國、大西洋歐羅巴、北洋俄羅斯、外大洋美利堅等。異域史地,一一能詳。
沿著水路順風航行,南海諸島里的東沙、西沙、中沙、南沙,東洋八島里的巴布亞新幾內亞、澳大利亞、斐濟、新赫布里底群島在航途上絡繹迎送,讓謝清高看到了遠方的風景。由于歷史條件和認知能力的限囿,他沒能像日后的維新派那樣,由此深慮起國家的現實和前景,然而他口述的訊息與軼聞,不是書上得來,而是附在人生履跡上的切身經歷,又為當時社會的一般人所難提供,并以其鮮見性和真實性顯示出價值,自然成為思想啟蒙的精神財富。
李圭:環游的敘錄
環游地球是可稱為壯舉的。隔著迢遙的地理空間,依當時的交通和傳播條件,十九世紀能成此行,更不可視為等閑。值美國建國百年的日子,李圭,這位寧波海關副稅務司秘書,奉朝廷指派,隨團東渡太平洋,赴費城參加世界博覽會,又乘船過大西洋,游英法,經地中海、印度洋回國。日后著成《環游地球新錄》。
李圭此行,路遠時長,“是役也,水陸行八萬二千三百余里,往返凡八閱月有奇。”(李鴻章《環游地球新錄序》)文字上的責任,他自然是擔著的:將世博會情況和途中所歷“詳細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故而,他的游述有一種筆墨的忠實,不但博聞,尤能強記,過眼之物再多,入其筆下,也便服帖地化為行行文字,將真跡固定下來。為歷史留影,這當是極要緊的。
清政府組團赴美的第一要務,全在費城世博會上。會址占地三千五百余畝,簡直就是一座新建的城池。三十七國赴會展陳,無物不有,無美不具。李圭游目其中,驚得大為感喟:“誠可謂萃萬寶之精英,極天人之能事矣!”既然做了摛章之士,李圭很是盡責。《環游地球新錄》刊行,他自為序,云:“謹將會院規制情形,善法良器,分別采擇,記錄成篇,名為《美會紀略》。”他撰述著那里的真實景狀,從“會院總略”到“各物總院”,先摹其大貌,求得概知,再朝機器院、繪畫石刻院、耕種院、花果草木院、美國公家各物院、女工院、總理會務官公署順次著筆,從會場的空間布局,到臚列的器藝造作,仔細端量,周詳記錄,不廢觀察的主動權。他斤斤于結構的完整、方位的準確,全景勾勒一筆不茍,局部描畫細致入微。在我看,他抓住了記游文章的根基,失了它,全篇就立不穩。即使今日誦讀這些字句,也能依其縷述繪制一幅圖卷,作為盛會的導覽。
李圭的記覽自有選擇,這選擇又充溢中國氣質。《凡例》中講得明白:“各物總院,首敘中國,義所當然。”足見他的落筆,繁簡詳略,其來有自。情緒跟景物的聯系一旦建立,會把心帶入閱覽體驗,物事的尋常性便被意義取代。他“行至金銀珠寶各物處,則如入寶山,萬象爭奇,兩目盡眩矣”,其中“英國地大物博,金碧爭輝”,尤為游觀者矚目,“物以瓷器為最,質白潔而工精細”。李圭一眼看出名堂:“初西國無瓷器,乃自中國訪求,回國潛心考究,始得奧妙。今則不讓華制,且有過之無不及之勢。”語多自豪感,又浸著難以道明的酸澀滋味。
意大利的石琢像,在西方國家中,其藝最精。石像、銅像和瓦像,制作水平的高超無可存疑。雕木器比起中國的卻略遜一籌。蠶絲亦多,“而其蠶桑之法,亦得自中國,仿效而成,即用以奪中國之利,可以不慮哉。”此言又帶出一段深思:“另有古銅器、古石器、牙器、鐵器,列于繪畫石刻院,皆二千年以上之物,自地內挖得者。有爐臺五事、牙桿秤、香爐、銅缽、銅鏡、銅石圖印,悉與中國式樣同。亦似有字,若鐘鼎文,剝蝕不可辨。按意大利,即往昔歐洲大一統之羅馬,漢書為大秦國,曾與中國通。今觀各器,豈當時得自中國耶?抑仿其式而自造耶?惜字跡莫辨,不能考其來歷矣。”身在異國的李圭,觸物,動了鄉思,一時心情,應當是驕傲的。
美國的機器制造業對社會生產的推動力之巨,震撼了李圭,他深感“美國地大人稀,凡一切動作,莫不恃機器以代人力。故其講求之力,制造之精,他國皆不逮焉”。他親見美國的機器造紙法:將紙料洗凈、浸透、舂碎,入鐵磨和水磨之,“計自入磨至告成,僅數時事耳。每日約成紙二千三百斤”,便想到在中國延續了兩千余年的造紙術,“今觀此法,尤覺工省事倍”。在耕種上,美國照例發揮機器的作用,觀覽之時,李圭產生了急迫感:“方今我國內地,兵燹后多有未墾之田,因是正需此器。倘日后議墾西北曠土,尤必得購用,以代人力也。況中西地土非盡殊,而農田則為中國首務。茍力省工倍,是舉國之所愿也。”西方工業化產生的能量,對農耕傳統的改變同樣深刻,尤其觸動知識精英做出意識的改觀。
李圭重視婦女的教育。女工院的“繪圖立說,指揮工匠,以及如何鋪設,如何位置,皆出女手,新巧異常”,“凡婦女所著各種書籍、繪畫、圖卷、針黹之物,并各個巧技妙法,悉萃于此”。 天文、地理、格致、算學、女紅、烹飪諸種書籍,分別排列,其旁執事的婦女,答客問詢,娓娓不倦,“舉止大方,無閨閣態,有須眉氣”,他敬之,愛之。想到國內女學的墜廢,不禁追懷歷史:“考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女之于學,往古蓋有所用之矣。”他發出醒世的心音:“倘得重興女學,使皆讀書明理,婦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輕視婦女之心由是可改,溺女之俗由是而自止。”搦管繪句,李圭詳為記敘的雖是繁博器物,然則曉天下、明事理的載道之心,并未有一刻的消歇。
世博會甫畢,李圭又游歷美國各都會,再涉大西洋,東抵英國倫敦,繼而東行出法國馬塞海口,過蘇伊士運河,歷紅海,渡印度洋,抵香港回到上海,加上數月前自上海出發,經日本越太平洋抵達美國西海岸三藩城,幾乎環行地球一周。開闊眼目后的記憶與心得,結撰而成《游覽隨筆》《東行日記》。親行之路、所歷之境中的一切政治、風俗、言論乃至科技、展會、招商,林林總總,詳略不一地收納筆端。在費城,看監獄、習正院、瘋人院、造錢局、蠟像館諸地,自謂“習正院與輕重犯監獄,皆主于化人為善也”。他追想起浙江第一循良李化楠在余姚做知縣時,“凡獲穿窬小竊,不遽加刑責。遴手藝之老成者,令教以藝。暇則親至其處,宛轉勸化,俾自悔艾。藝成,許親族鄰佑或教其藝者,具狀保出,永不為非。”本國的賢良德政,恰能與異域的所見相合,便引發深深感慨。在華盛頓,看伯理璽天德宮、養兵院、議政院、郵政局、觀天臺;在哈佛,謁見清政府駐美副公使容閎,看克爾司洋槍廠、織造廠、聾啞院;在紐約,看書館、巡捕房、稅關、育嬰堂、紳民公會、衙門、總督署、寄藏所、大雜貨店、戲館。紐約書館,尚默識,不尚誦讀,只因“蓋默識則書之精義乃能融洽于心”。他殊覺這里“歌詩、舒體,似有得中國樂舞之意”,贊嘆“教法精詳,課程簡嚴,而不事夏楚,師徒情意洽貫”。一動一息,體察入于纖微,那種感覺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
往游泰西第一大都會倫敦,圣保羅大教堂、議政院、電報局、稅關、驗茶所、驗酒房、新報館、博物院、機器會館、奧克司芬城,依次入眼。根性登博物院里的展物牽動心情,因為“有道光年間覺生寺所制銅磬,及金玉釧、釵環簪珥、景泰瓶爐、雕木器,皆得自中國者”。造型熟稔的物件,勾起了一縷鄉愁。
法國巴黎的拿破侖故宮、盧發博物院、拿波倫武功坊、生物苑、柯巴辣戲館、馬戲館,敘述較略,不知在李圭心里,留痕是否也這般淺,這般淡。
李圭把奉使出洋的耳聞目見,載錄在這部書里。廣為采擇的行記,無所畛域,無所蔑棄,意氣那么豁如,襟度那么寬博,不獨為清廷提供了“以資印證”的第一手材料,更深的意義在于讓公眾明曉同一時間出現于異邦的新奇事物,而這正是開啟認知的初始。域外文明憑借李圭的文字注入進來,使千年帝國的僵體煥出活力。充滿人文意義的游述、富于思辨色彩的論說,將別國的生存智慧跟中土習尚嫁接,向依附世傳禮法的道德禁忌與行為羈勒質以疑義,這對當時的國人具有開啟心智、拓展視野的實效,當然超出單純記錄世博會的預想。
讀過《環游地球新錄》的人,廣做轉述,一雙眼睛變作千萬雙眼睛,去看海外的天地。李圭讓更多的人隨著自己的視線向未來凝眸,無數眼界因之拓開,無數心懷因之激奮,精神的解放開始在封閉的古國醞釀。
責任編輯 練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