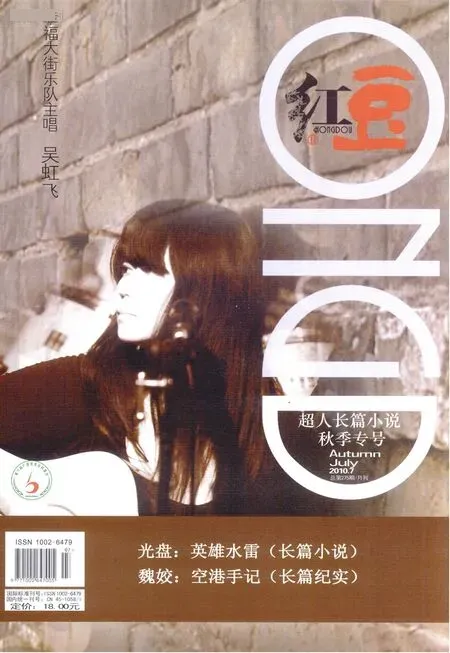從陜北到額濟(jì)納
高安俠,女,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陜西作協(xié)簽約作家,《讀者》雜志簽約作家。魯迅文學(xué)院第八屆高研班學(xué)員。在報(bào)刊發(fā)表大量文學(xué)作品,著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野百合》,散文集《弱水三千》《我們身邊的空缺》《遼闊的藍(lán)》《完美的背后》等。
在中國(guó)雄雞版圖的腰窩,一個(gè)小小的單圈,那么細(xì)小纖薄,像是一枚指環(huán),遺失在沙漠里。
那就是額濟(jì)納,一個(gè)無(wú)比荒涼的地方,除了胡楊和藍(lán)天,一無(wú)所有。
我想去額濟(jì)納,并不是因?yàn)楹鷹詈退{(lán)天,陜北的秋天甚至比那里更美,色彩也更豐富。額濟(jì)納根本的吸引力在于遙遠(yuǎn)。
當(dāng)車轉(zhuǎn)入高速路,延安越來(lái)越遠(yuǎn),生活的庸常和煩瑣也跟著漸漸遠(yuǎn)離,那么多負(fù)累遠(yuǎn)遠(yuǎn)地甩在后面。我不再是那個(gè)朝九晚五的小職員,不再按著固定的軌道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地生活。不再是今天就知道明天的生活,甚至知道幾點(diǎn)幾刻在做什么。不需要琢磨他人的臉色,不需要絞盡腦汁寫(xiě)干巴巴的材料。
那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漸漸離我而去。
水水水
在穿越了黃土高原之后,毛烏素沙漠綿延不斷的沙丘呈現(xiàn)出一種粗糲感。灰色的大地,在太陽(yáng)的照耀之下,反射著干澀的白光。少量的綠色植物一掠而過(guò),因?yàn)橄∩伲屓搜矍耙涣痢?/p>
一切全然陌生。
短暫的興奮之后,不知為什么,惶惑像一股潛流從心底暗暗滲出。公路平平展展,像一面無(wú)限延展的明鏡,倒映著車影,空氣在簌簌抖動(dòng)。遠(yuǎn)方連接著遠(yuǎn)方,究竟哪里是盡頭?
車輛高速位移,像一群鳥(niǎo)兒般輕盈地飛翔,反光鏡的光斑迅速移動(dòng),劃出一道道美麗的弧光。高緯度地區(qū)的陽(yáng)光似乎更刺眼一些。賀蘭山脈赭紅色的巖石氣勢(shì)洶洶地撞過(guò)來(lái),眼看要撞到鼻梁上,可是到底沒(méi)有,似乎是擦著額頭了,頭皮上微微地刺痛。山脊起起伏伏,快速向后逃離。速度給人以興奮感,類似酒后的微醺,一切有些不真實(shí)。
從公路標(biāo)志牌顯示的地名里,你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這一路的地名很多以“水”來(lái)命名,泉水子、海子、一眼泉、喊叫水。千萬(wàn)不要以為這里多水,正好相反,這樣的地名在告訴人們,這里是個(gè)缺水的地方。正如陜北黃河岸邊,那些一無(wú)所有的人總喜歡起名:有財(cái)、富貴。
“喊叫水”,多么焦渴的呼喚!水缺到了極度,我聽(tīng)見(jiàn)人們焦唇敝舌地喊叫著:水水水!
造物主就是這樣的不公。半月前,我曾在西湖邊久久佇立,看波光明滅,漣漪蕩漾。嫉妒地想,天下的水怎么都到了這里!隨手朝空中抓一把都可以將水汽握住。江南的植物因?yàn)樗殖渑妫L(zhǎng)得肥大粗壯,張牙舞爪。滿坑滿谷都是蓊蓊郁郁的樹(shù)木,放眼望去到處是綠,揮霍的綠,奢侈的綠。
可是在這沙漠里,水是多么稀缺,植物們都懂事,舍不得浪費(fèi)水,把葉片長(zhǎng)成了細(xì)刺,或者表面涂滿了蠟質(zhì),盡可能節(jié)約每一滴水。駱駝刺和紅柳細(xì)細(xì)弱弱,一副營(yíng)養(yǎng)不良的樣子。除此而外,滿眼白花花的石頭、沙子,反射著太陽(yáng)干巴巴的光。
霍城
多么熟悉的名字,這是霍去病的城。相傳霍去病北擊匈奴,曾經(jīng)駐扎于此,此地因而得名。多年后,當(dāng)我站在茂陵霍去病墓前,看那馬踏匈奴的石雕,回思童年的霍城,覺(jué)得這個(gè)曾經(jīng)是奴隸的將軍簡(jiǎn)直是個(gè)故人,親切而自豪,這是家鄉(xiāng)的霍去病啊!
霍去病北擊匈奴的勝利,使得這片草原成為漢武帝的皇家牧馬苑,汗血寶馬就出自這里。它們?cè)跐h帝國(guó)一次次戰(zhàn)爭(zhēng)中立下過(guò)汗馬功勞。可以說(shuō),漢帝國(guó)時(shí)期,中國(guó)版圖的確定有汗血寶馬的功勞。
昔日童年的霍城只是一片烏泱泱的低矮農(nóng)舍,同學(xué)的奶奶住在這里。那一年,一個(gè)星期六的下午,她帶我去找她的奶奶,低矮的農(nóng)舍里掛了一面墻的獎(jiǎng)狀,那是同學(xué)的舅舅們的。老奶奶很為兒子們自豪,做了一鍋白面條子隆重招待我們。我有潔癖,嫌棄她指甲的黑垢,便裝作肚子疼。老奶奶以為我是真疼,要給我吃止痛片。農(nóng)村缺醫(yī)少藥的,止痛片是萬(wàn)能的靈丹妙藥。送我們走出村口,她還一個(gè)勁地叮嚀,生怕路上著涼,哪里知道一出村子,我的肚子痛就好了。后來(lái)我想,同學(xué)是了解我的,只是不愿揭穿罷了。
還有另一個(gè)發(fā)小——琴,上初中的時(shí)候,她每次回家都要給我拿半個(gè)燒盒子 ——本地一種小吃,類似鍋盔。把面餅放在鐵鏊子里,再把生鐵鑄的蓋子旋緊,煨在燒著的馬糞里。待熟了以后,外面焦黃,里面香軟,散發(fā)著草原特有的青草清香。她那巧手的媽媽在里面摻了酥油和香豆子粉,河西走廊的小麥本身生長(zhǎng)期長(zhǎng),小麥的成熟度好,那燒盒子吃起來(lái)又香又甜。很久以來(lái),記憶中的燒盒子超過(guò)任何美味。那是家鄉(xiāng)的味道,童年的味道。
邊城
張掖,是一個(gè)古雅的地名,出自漢書(shū)“伸張國(guó)掖,以通西域”。絲綢之路上一顆美麗的結(jié)紐,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帶。從漢代開(kāi)始,張掖就成為一個(gè)重要的存在。這里的很多地名都和漢代有關(guān),比如前面提到的霍城,還有比鄰的酒泉。相傳霍去病打了一個(gè)大勝仗,漢武帝得到捷報(bào)賞賜美酒一壇,可是將士眾多不夠喝。霍去病干脆把美酒倒進(jìn)一眼甘泉中,大家大碗暢飲,有福同享,酒泉因此得名。
漢帝國(guó)時(shí)期的名城張掖,今天和內(nèi)地城市相比,繁華程度毫不遜色。
我們進(jìn)城的時(shí)候已經(jīng)夜色深濃,華燈初上,大街上很熱鬧,鬈發(fā)多髯的馬可·波羅的雕像佇立在廣場(chǎng)中央,給這個(gè)城市增添了一絲異域的風(fēng)情,想必他曾經(jīng)到過(guò)這個(gè)絲綢之路上的明珠之城。
酒吧一條街,全部是仿歐式建筑,衣著時(shí)尚的男男女女衣香鬢影,往來(lái)穿梭,讓人完全想不起來(lái)這曾經(jīng)是一個(gè)烽火連天的邊地。
如今,絲綢之路上那些漢唐時(shí)期的沙漠駝隊(duì),被高鐵、高速公路徹底改寫(xiě),一個(gè)個(gè)繁華的城市顛覆了荒漠戈壁的苦寒偏遠(yuǎn)。遙遠(yuǎn)這個(gè)詞的含義需要重新定義,一個(gè)朝發(fā)夕至的地方,能算是遙遠(yuǎn)嗎?漢武帝時(shí)期,張騫出使西域,一走13年,那才算是遙遠(yuǎn)。這么說(shuō)來(lái),遙遠(yuǎn)是個(gè)時(shí)間概念而非空間概念。
清晨,在張掖城里轉(zhuǎn)悠,甘泉公園里,很多人在跳廣場(chǎng)舞,喧囂吵鬧中透露出和平年代豐衣足食的靜好。
很多人對(duì)當(dāng)下的中國(guó)到底是窮是富,是好是壞,有各種看法。有一次和人討論,一個(gè)人拿自己家鄉(xiāng)的一些情況說(shuō)事,得出的結(jié)論是,中國(guó)社會(huì)各種矛盾一觸即發(fā),幾乎到了分崩離析的前夜。我反對(duì)他的觀點(diǎn),證據(jù)也是自己親眼所見(jiàn),結(jié)果雙方各執(zhí)一詞,幾乎吵起來(lái)。我講的是我看到的情景,他講的是他看到的現(xiàn)實(shí),誰(shuí)也說(shuō)服不了誰(shuí)。現(xiàn)在想想,有些盲人摸象的意思。
據(jù)說(shuō),大唐時(shí)期,武則天要稱帝,大臣們擔(dān)心牝雞司晨,老百姓反對(duì)。武則天就到民間調(diào)查,半路上碰見(jiàn)一個(gè)白胡子老頭兒,吃飽了飯,邊走邊拍著肚皮悠閑地哼唱,武則天便放心了。
回來(lái)以后,她對(duì)大臣說(shuō),皇帝是男人還是女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能吃飽飯,過(guò)上好日子。
中國(guó)究竟是富裕還是貧困,不能簡(jiǎn)單地一言以蔽之,驚人的富裕和驚人的貧困同時(shí)存在,誰(shuí)也掩蓋不了誰(shuí),誰(shuí)也遮蔽不了誰(shuí)。張掖城里衣履光鮮的人們和塔拉草原那些為了生存而四處奔波的人同時(shí)存在。我想,這就是中國(guó)真實(shí)的模樣。
公園一角,兩個(gè)氣質(zhì)儒雅的老人在拉小提琴。優(yōu)美的旋律響徹在開(kāi)滿菊花的秋天里。我猜想也許是20世紀(jì)中期來(lái)到張掖支邊的知識(shí)分子。現(xiàn)在,兒女都在本地成家立業(yè)了,也就等于在這邊城扎下了根,不再惦念著故鄉(xiāng)了。
在我從小生活的塔拉草原就有很多這樣的知識(shí)青年。你永遠(yuǎn)不可低估那些來(lái)自大城市的知識(shí)青年對(duì)于一群蒙昧的孩子有多么大的影響力。上海的文老師會(huì)彈琴,每天上音樂(lè)課,老師就會(huì)彈著一部腳踏風(fēng)琴教我們唱歌。她的皮膚很白,手指纖長(zhǎng)。她教我們要愛(ài)干凈,每天上學(xué)前,要把臉和手洗得干干凈凈。我怎么洗也沒(méi)法將皮膚洗得和老師一樣白凈,曾經(jīng)暗自猜測(cè),不明白她怎么就那么白,白凈的臉,白凈的手,至今在記憶里閃著耀眼的光。
三年級(jí)的時(shí)候,文老師給了我一本《張騫出使西域》。這本書(shū)打開(kāi)了一個(gè)孩子的眼界,原來(lái),世界并不是只有草原那么大,祁連山外面還有一個(gè)更為遼闊的世界。遙遠(yuǎn)的地方,遙遠(yuǎn)的人,無(wú)窮無(wú)盡的遠(yuǎn)方激發(fā)了孩子對(duì)于世界的向往。
巴丹吉林
進(jìn)入巴丹吉林沙漠,我們都有一點(diǎn)興奮,這個(gè)地方的知名度很高,是中國(guó)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地方。
我們抻著脖子四下里望,可是荒漠接天,什么都沒(méi)有。臆想中那直刺藍(lán)天的火箭發(fā)射塔根本就沒(méi)有出現(xiàn)。只有一處岔道上一個(gè)醒目的標(biāo)語(yǔ)昭示著這個(gè)地方的特殊:“竊密就被抓,抓了就殺頭。”口氣凌厲,叫人心里一抖。誰(shuí)說(shuō)做賊心虛?不做賊照樣心虛。連忙一腳油門加速離開(kāi)。
沙漠、戈壁連綿不絕,連當(dāng)初的駱駝刺也沒(méi)有了。巴丹吉林沙漠和陜北以北的毛烏素沙漠一比,完全是兩個(gè)世界,毛烏素沙漠雖然號(hào)稱沙漠,卻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固沙,一路所見(jiàn)紅柳和毛頭柳織成一個(gè)個(gè)方正的網(wǎng)格,好像手拉手的衛(wèi)士,死死看守著不肯安分下來(lái)的沙丘。各種草本植物已然將沙漠覆蓋,可以說(shuō)植物基本上把沙漠鎖定,土地沙化基本得到控制。
但是巴丹吉林沙漠卻是完全意義上的沙漠,干巴巴,白花花,就連偶爾遇見(jiàn)的芨芨草也是白花花的,讓人想起曾岑的那句“北風(fēng)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那芨芨草就是詩(shī)人筆下的白草。過(guò)了千年,白草還是昔年模樣,干枯的白,倔強(qiáng)的白。
我們的車奮力在沙漠里馳行,越走越覺(jué)得遙遠(yuǎn),那個(gè)額濟(jì)納仿佛在天邊,沙漠里除了沙子和石子,一無(wú)所有。女兒幾次問(wèn)道,這里的人們吃什么呀?沒(méi)有水怎么活下去呀?
城里的孩子以為水是從自來(lái)水管子里流出來(lái)的,糧食是從超市里買出來(lái)的。浩大世界的真相令她吃驚而無(wú)助。她們不可想象在苦寒的邊地,人們活下去要付出怎樣的艱辛。
那些曾經(jīng)從這片沙漠里走過(guò)的人一個(gè)個(gè)漸漸清晰起來(lái)。張騫、玄奘、法顯、鳩摩羅什。對(duì)了,還有王維,幾乎每一個(gè)小孩子都會(huì)念“大漠孤煙直,長(zhǎng)河落日?qǐng)A”。這是詩(shī)人王維在趕赴邊地慰問(wèn)將士的途中所作。這死亡的大漠,因?yàn)樵?shī)人的到來(lái)而成為審美意義上的存在。
不難想象一千年前,在長(zhǎng)安城里混得不怎么好的王維,一個(gè)人遠(yuǎn)赴邊地時(shí)的寂寥和失意,在朝廷里屬于溜著墻邊站的,才會(huì)派這些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我的車時(shí)速140碼仍然感到走不出巴丹吉林,王維是一個(gè)人一輛馬車,究竟是怎樣泅過(guò)沙海的呢?
也許,緩慢的馬車反而讓詩(shī)人的心靜下來(lái),官場(chǎng)失意之后,一顆清冷的心反而能捕捉到詩(shī)意。他們說(shuō)文章憎命達(dá),在得失之間,我不知道王維更愿意將天平傾向哪一頭。
額濟(jì)納
天色漸漸顯示出黃昏的意味,又大又圓的太陽(yáng)與地平線就要相切時(shí)分,公路指示牌上終于出現(xiàn)了“額濟(jì)納”三個(gè)字。
瞬間,我有一種走失多年、回到人間的感覺(jué),漫長(zhǎng)的奔突,終于可以稍停喘息。
當(dāng)額濟(jì)納旗的輪廓出現(xiàn)在天穹下,我覺(jué)得那是最好看的一個(gè)風(fēng)景,那是活色生香的人間,那里有熱騰騰的生活!
我們的房東是個(gè)和氣的本地人,當(dāng)他打開(kāi)房門時(shí),我有些小驚訝,多么漂亮的房間!一點(diǎn)兒也不遜色于內(nèi)地。
房東很健談,他告訴我們,他們一家是漢人,多年前,響應(yīng)國(guó)家政策從內(nèi)地來(lái)的,一邊說(shuō),一邊給我們交代鑰匙、水電等事宜。房東的妻子話很少,但是眼睛里透著精明勁兒,我猜家里真正的一把手應(yīng)該是她。果然,她說(shuō),本來(lái)這個(gè)房子剛裝好,舍不得出租,但是,既然女兒已經(jīng)給你們說(shuō)了,那就只好租給你們了。言語(yǔ)里意思豐富,我們趕忙表示感謝。其實(shí),房費(fèi)不低,一晚1000元抵得上內(nèi)地好酒店的房?jī)r(jià)了。他們的女兒今年剛上高中,趁著這幾天全國(guó)各地的人都來(lái)看胡楊,打算在景區(qū)里擺個(gè)攤賣哈密瓜,掙個(gè)手機(jī)錢。女孩子忸怩地一笑,躲在母親身后,一句話也不說(shuō)。
當(dāng)年,張藝謀拍了一部電影《英雄》,里面有一段兩個(gè)麗人廝殺的場(chǎng)面,背景就是額濟(jì)納的藍(lán)天和胡楊。張藝謀說(shuō),也許多年以后,人們忘記了這部電影,但是不會(huì)忘記這個(gè)畫(huà)面。
一部電影成就了額濟(jì)納。每年十月,當(dāng)胡楊的葉子黃了,大家穿越河西走廊和巴丹吉林,千里迢迢來(lái)看胡楊那一片金燦燦的美。
額濟(jì)納這幾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甚為迅速,擴(kuò)建的新城寬闊大氣,剛修好的體育館造型既大方簡(jiǎn)約又具有現(xiàn)代感,比起延安的體育館那傻笨粗拙的模樣,簡(jiǎn)直是云泥之別。雖然這幾天全國(guó)各地的車輛蜂擁而至,但是寬闊的大街毫無(wú)堵塞的可能。在這里開(kāi)車,心情燦爛如金黃的胡楊林。我放在后備箱里的大衣、棉襖以及水和食物完全沒(méi)有發(fā)揮作用,這里什么也不缺。超市里應(yīng)有盡有,就連暮色中的廣播里也放著京劇折子戲,如果不是街道上蒙文的提醒,幾乎讓人忘記這里是邊境。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同樣可以用在植物上。陜北田間道旁的楊樹(shù),身材頎長(zhǎng),站姿挺拔,像一列士兵站崗放哨。而沙漠里的胡楊,因?yàn)闃O度缺水,它們用盡了各種辦法來(lái)適應(yīng)環(huán)境,樹(shù)姿奇形怪狀,或扭曲向上,或匍匐倒地,那些死去的胡楊活似經(jīng)歷了一場(chǎng)慘烈的戰(zhàn)爭(zhēng),樣子極為猙獰可怖。
一棵合抱粗的胡楊樹(shù),渾身披掛著金箔裝飾的鎧甲,在陽(yáng)光下熠熠生輝,華貴雍容,讓人聯(lián)想起昔日居延海的匈奴王。可是,近前細(xì)看,胡楊的葉子似乎有些異樣,底部的葉子如柳葉般細(xì)長(zhǎng)而密,樹(shù)巔的葉子好似銅錢一般,疏疏落落。摸一摸,硬硬的,蠟質(zhì)的手感。
在極度缺水的額濟(jì)納,為了活下去,它不得不變化葉子,將葉面縮小,蠟質(zhì)的表面最大限度地減少水分的蒸發(fā),保證節(jié)省每一滴水。
每一棵胡楊的生命都是一段含著血淚的奮斗史。
那些千里路上來(lái)看胡楊的人,是否在領(lǐng)略美景的時(shí)刻,悟到生命的貴重?
居延海
夏天,祁連山的冰雪融水一路蜿蜒北流,匯成一條小溪。最初,它的小名叫做山丹河。別看它小,這是一條倔強(qiáng)的河流,不肯隨大流朝東投奔大海,卻一頭扎向西北的巴丹吉林。
順著河西走廊狹長(zhǎng)的地帶,一路蜿蜒迤邐流到張掖,在這里,人們稱它為黑河。黑河滋養(yǎng)了張掖,是張掖的母親河,使得它成為沙漠戈壁深處的一塊肥美綠洲。
很久以來(lái),我一直納悶它為什么叫做黑河。記得有人說(shuō),可能是因?yàn)樗嬗纳畛屎谏妹2还茉趺凑f(shuō),這是一個(gè)不動(dòng)聽(tīng)的名字。還好,流到巴丹吉林沙漠,人們終于給它起了一個(gè)詩(shī)意的名字:弱水。
其實(shí),弱水只是言說(shuō)水流的小。據(jù)《山海經(jīng)》記載,水流細(xì)弱不能載鵝毛。連一片羽毛也漂不住。可是,這細(xì)小的河流竟然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奇跡,千百年來(lái),它的水流匯聚成了居延海,一個(gè)沙漠中的內(nèi)陸湖泊。
這片海四周曾經(jīng)是綠洲,居住過(guò)柔然、匈奴、突厥等民族。
你永遠(yuǎn)都想不到,在居延海,我碰到了老子。
《道德經(jīng)》的老子。
和所有的圣賢一樣,老子一生寂寞。西過(guò)函谷關(guān)時(shí),遇見(jiàn)了尹喜,感后者禮遇而著《道德經(jīng)》。可是,過(guò)了函谷關(guān)后,騎著青牛的老子去了哪里?沒(méi)有人知道。司馬遷說(shuō)他不知所終。
很多次在閱讀《史記》的時(shí)候,都沒(méi)有在這句話上停留。我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不值得探究的問(wèn)題。反正他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樣,兒孫滿堂,壽終正寢,老死在自家炕頭。那樣的話,他也就不是老子,而是一個(gè)有福氣的尋常老頭兒。
對(duì)于一個(gè)思想家來(lái)說(shuō),他思想的存在,就等于他的存在。對(duì)于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老子是永生的。而死亡,僅僅指的是身體的不在場(chǎng)。
那天,風(fēng)很大,含著一股強(qiáng)勁的力,人站立不穩(wěn),可是,卻吹不動(dòng)居延海里的水,浩大的水面只是泛起細(xì)碎的波紋,太陽(yáng)尖銳的光在慢悠悠的波紋里一閃一閃,耀眼而不真實(shí)。我想起曾經(jīng)看到的西湖,西湖的波紋從來(lái)沒(méi)有這樣從容,太陽(yáng)光也沒(méi)有這么尖銳。
在浩大的居延海旁邊,老子騎著那頭青牛,仿佛在慢悠悠地行走。我覺(jué)得很奇怪,居延海遠(yuǎn)離中原大地,自古以來(lái),這是化外之地,而“居延”一詞本身就是匈奴語(yǔ),大致意思是“流動(dòng)的沙漠”。
那么,老子怎么會(huì)混跡于匈奴人中間?
該不會(huì)又是一處人造景觀吧?這幾年興起來(lái)一個(gè)調(diào)調(diào),叫做文化搭臺(tái)、經(jīng)濟(jì)唱戲。文化儼然一個(gè)丫鬟,要服務(wù)陪襯經(jīng)濟(jì)這個(gè)主角。為了招徠顧客,各地紛紛借著文化的名義生捏硬造,一會(huì)兒孫悟空的故居橫空出世,一會(huì)兒豬八戒的墳?zāi)贡徽业剑鳂郁[劇無(wú)非奔著一個(gè)“錢”字。
難道又是一出幽默劇?
可是《甘州府志》記載:“老子出函谷關(guān),入流沙不知所終。”流沙就是古代的居延海一帶。
對(duì)老子這樣一個(gè)充滿了探究精神的人來(lái)說(shuō),出了函谷關(guān),地平線還在遠(yuǎn)方。遠(yuǎn)方,對(duì)于他來(lái)說(shuō),同樣充滿了誘惑。于是他選擇不停地走,西出大散關(guān),溯渭河而上,翻過(guò)隴山,遠(yuǎn)方永無(wú)盡頭,遠(yuǎn)方之外還有遠(yuǎn)方,直到黑河流域,直到順著黑河進(jìn)入巴丹吉林沙漠。
至今,本地流傳著很多關(guān)于他的傳說(shuō),看來(lái)并非空穴來(lái)風(fēng)。
我為自己的偏狹感到汗顏,在我的觀念里,居延海太偏遠(yuǎn)了,遠(yuǎn)離中原大地,夷狄雜居,尚未開(kāi)化,老子不可能來(lái)到這里。
可是,什么是偏遠(yuǎn)呢?那么誰(shuí)又是中心呢?
想起一個(gè)笑話,說(shuō)兩個(gè)老頭子圪蹴在地頭聊天,一個(gè)說(shuō):北京可好啦,要甚有甚。另一個(gè)低頭嘬著煙袋說(shuō):好是好,就是太偏遠(yuǎn)了。
在上古時(shí)期的《山海經(jīng)》里就有關(guān)于弱水的傳說(shuō),說(shuō)大禹為了讓弱水流入沙漠地帶,置合黎山于東,使得居延海一帶鳥(niǎo)飛魚(yú)躍,水草豐茂,羊肥馬壯,人民安康。
可見(jiàn),沒(méi)有發(fā)達(dá)的交通工具,古人卻比我們走得更遠(yuǎn),視野更為開(kāi)闊;沒(méi)有偏狹的中心論、正統(tǒng)論,對(duì)世界的每一處都充滿了好奇心。
面對(duì)波光水色的居延海,我特意在騎著青牛的老子面前照了一張相。就像和一個(gè)老熟人見(jiàn)了面,打了一聲招呼。
責(zé)任編輯 練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