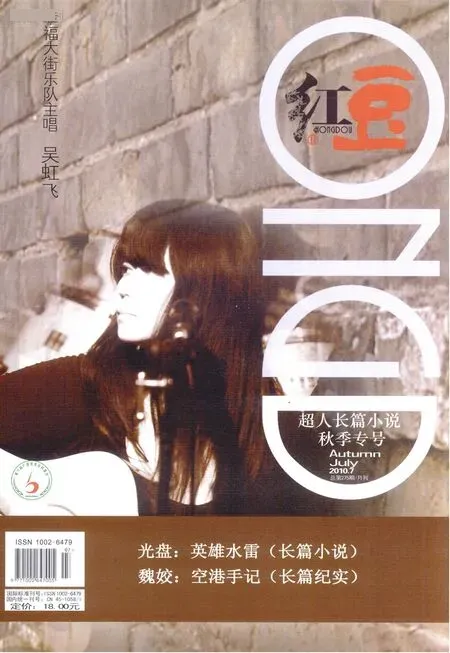祁十木的詩
祁十木,本名祁守仁,回族,1995年12月生于甘肅臨夏。現就讀于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寫作班,“相思湖詩群”成員。作品見于《詩刊》《民族文學》《詩選刊》等多種期刊,并入選多種年度選本,獲多種詩歌獎。
多層世界
我始終睜著眼。今夜,我經歷一個人的
人生,同樣經歷我。在所謂的世界終點
生造出的詞匯,稱呼一些本與之無關的物質
鐵就是鐵,水就是水,愛情就是愛情
一絲懷疑都未曾有。某一天,我戳破自己的手指
發現里面是個空殼子,藏著一座小房子
同樣一群轉圈的人,生殖、勞作、死去
我開始觀察頭頂的天空,里面的人也抬頭看我
我用力抖一抖身子,我的世界靜止
地震來到他們的世界。我記起
我曾玩弄過一群搬家的螞蟻
像如今,大我幾倍的、高等世界的孩子在逗我
存心淹沒熱愛的家園。懷疑再次涌起
家人、朋友、愛人,甚至我自己
都被我指控成一堆虛無的名詞
在我們“大世界”里數,自己是怎樣的小芝麻
一些被拉長的歲月。一并毀滅
我縫上手指,暗地里的懦弱者
閉上眼睛與接續夢境。明天的醒來、生活、下次夢
都在忘掉,又一個人的人生。我害怕
舊事
一九九五年。荒草地。父親開墾這一角
挖空祖父的墳。日夜勞作,用挖空的黃土和泥
調和以水為主要成分的黏稠狀黃泥
那時我出生不久,他把我撒在里面
彌合一些縫隙。祖父的骨頭碎渣、我這堆肉末
及父親的血絲,使得這些泥水散發藥味
這取自黃河的泥,捏出黃色的我
泥捏我,遭遇著從南到北的風。難怪我總想在風里走走
走成一株輕盈的睫毛。生根、發芽,茂密在祖國中央
睜開時,向上翹著,觸碰黃河北岸的馬鞭、蘇州河里的魚蝦
而閉合時,苦思冥想,始終無法樹立一些形狀
無,命令我從頭到腳的開裂,裂
縫,錯綜復雜,猶如父親那握著鐵鍬的手
和泥的手。裂開的口子,修成正果。我們的愿望始于此
又落于此,陣風吹來,明顯區別于父親的控制
再捏我,加之碾、磨、揉,我返照生日。一道碎渣
自此,落草為寇,圓了漂浮物的夢——
睫毛。一截一截破裂,游蕩于祖國的四周
和那些說中國話的甘肅人、河南人、廣西人、四川人一道
游蕩,從天山南北尋至長江上下
此刻垂暮的夕陽、故園,邕江多了些偏頗的味道
我想起一個叫張廼瑩的女人,她從汨羅江而來,石頭像我
可你還記得嗎?我位居北方的父親,我沉睡,
沉睡的父親,我受傷的指紋遺傳了你
離開時,你用背當門,縹緲在人群最密的車站,我躺倒在地,躺著
像延伸的、天梯模樣的軌道。天堂、地獄,鄉書何處達?
匆匆、匆匆,流亡思緒成為一種弒父情結
我體內,出發于鄉愁的世界,一層厚厚的繭。實際上
里面是最后一段睫毛。而由此產生的一座座毛孔
將生長成噴泉,蔭蔽下烈日灼燒的黑色翅膀
責任編輯 侯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