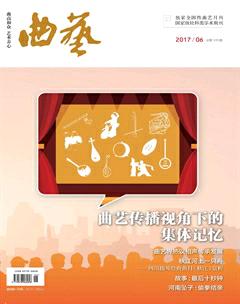一片真情弦上流
陳連升
徐麗仙是我國享有盛譽的彈詞名家,她在長期演出實踐中所創(chuàng)造的“麗調”是吸收“蔣調”的旋律、“徐調”的運腔,融化而成的。“麗調”最初以柔和委婉、清麗深沉為特點,之后結合譜唱各種歷史題材及現(xiàn)代生活的唱詞,對唱腔、曲調作了很大的革新,增加了明朗剛健以及流利歡快的一面。
自從藝以來,徐麗仙曾演出過幾十段長、中、短篇彈詞和彈詞開篇。代表作有《新木蘭辭》《情告》《陽告》《六十年代第一春》《見到了毛主席》《年輕媽媽的煩惱》《飲馬烏江河》《黛玉葬花》等不下三十篇。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有幸錄制了她的精湛作品《飲馬烏江河》。錄制過程中,她的投入、虛心和精益求精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麗仙對藝術的追求非常執(zhí)著。我聽老前輩介紹:徐麗仙不僅利用洗衣裳的時間背誦唱詞,還經常來到公園的僻靜地方模仿角色的虛擬動作。她文化水平不高,每拿到一個唱詞,總是先請作者和專家給她逐字逐句地詳細講解,弄明白了意思以后再分段哼唱定腔,對初步定腔的唱腔,邊唱邊征求意見。碰上沒有日場演出,她會花上一整天工夫,不斷揣摩唱詞意境和人物感情,一遍又一遍地哼唱,仔細修改,尋求最貼切最適合的旋律。一次她對我說:“要說我的唱有一些特色的話,該有詞作者很大功勞。平襟亞先生編的唱詞既能突破句格的常規(guī),又能調順平仄。比如中篇彈詞《王魁負桂英》中‘天昏昏,地沉沉,虎狼輩,毒蛇心,負恩義,滅人倫的唱詞在起始句中連用六個三字句,這在傳統(tǒng)彈詞中是沒有先例的。這是彈詞作者為我著意跳出老框子,尋求新唱腔而創(chuàng)造的有利條件,便于我抒發(fā)感情。徐凌云、陸澹庵先生都曾為我的唱提出過不少技術性意見,我的唱調也有劉天韻、姚蔭梅、蔣月泉、周云瑞、楊德麟等大家的指教和幫助。”從這段自謙中,也同樣可以看出她在藝術上所花費的心血。
1978年,徐麗仙不幸得了舌底癌,病魔奪去了她演出的權利,但無法奪走她對評彈事業(yè)的一片癡情和刻意求精的藝術追求。1981年6月,戚雅仙、楊飛飛、梅蘭珍相約徐麗仙在無錫市人民大會堂作一次藝術交流的公演。她們是分別從事越劇、滬劇、錫劇和評彈四個藝術品種表演的姐妹,徐麗仙不顧病痛的折磨欣喜若狂,她太想手抱琵琶重登舞臺為心愛的觀眾獻上一曲了,于是她毅然同意了。上海評彈團領導得到消息后,馬上派人來無錫進行勸阻,但這次徐麗仙謝絕了領導的好意,她說:“我要為彈詞作出自己的一點貢獻,上臺為觀眾彈唱才是真正的精神療養(yǎng)。”最終,她說服領導,堅持演出了。
這次演出我并沒有去,是無錫電臺的錢同朋同志繪聲繪色地為我介紹了相關情況。
當紫紅的帷幕輕輕拉開,光線由弱轉強,徐麗仙身穿一件鮮紅織錦旗袍,懷抱琵琶出現(xiàn)在觀眾面前時,她光彩照人,根本不像被病魔折磨了三年的病人啊。頓時,春雷般的掌聲響徹整個大會堂。徐麗仙平靜一下自己的心情,輕撥琵琶,潤了一下喉嚨,唱了一曲剛剛譜好的新曲《二泉映月》。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癡。弦聲未落,掌聲驟起,在聽眾熱情要求下她又唱了自己的保留曲目《情探》。觀眾沉浸在“麗調”藝術的美與動人中時,誰又想到徐麗仙為這場演出付的代價有多大,她是在忍著病痛服藥打針后才上臺的啊。
演出結束被扶下舞臺,徐麗仙像散了架一樣,渾身虛汗,臉色蒼白,繼續(xù)服藥。身上雖然痛苦,但心靈上卻得到很大慰藉。她就是一個只要藝術不要命的人。
徐麗仙住院期間還是不停地作曲、錄音,她說:“我就這點時間了,我要和死神賽跑,盡可能多留下作品。”
1982年3月15日至27日,文化部主辦的全國曲藝優(yōu)秀節(jié)目(南方片)觀摩演出在蘇州舉行。趙麗芳演唱的彈詞開篇《二泉映月》榮獲一等獎。為表彰譜曲者徐麗仙為評彈事業(yè)所作的貢獻,文化部專門設立了一個榮譽獎授予徐麗仙。
1981年至1982年,由于舌底癌的折磨,徐麗仙咬字有些不清,每吐一個字額頭就冒出汗水,難以想象演唱幾十句的唱詞要承受多少痛苦。但徐麗仙堅忍不拔,她認為只有撥弦、彈唱、譜曲才是最好的精神療法。這兩年中,她仍然堅持錄制了不少開篇作品。
徐麗仙有一個心愿,要為李白著名詩篇《行路難》譜曲。她覺得這首詩正是自己走過的人生和藝術道路的寫照。可惜曲譜尚在腦海里醞釀,在嘴邊哼吟,還未及寫在紙上,她就溘然仙逝,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為了緬懷這位不平凡的彈詞藝術家,1984年9月,我做了專題節(jié)目《一片真情弦上流》。至今,她的音容笑貌仍時時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