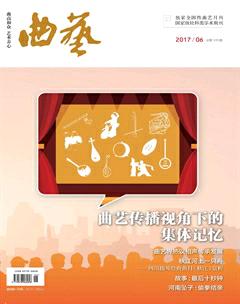傳我以藝 遺我以德
三寸醒木三寸舌三尺書臺,您有三千桃李;
數載師徒數載情數度心胸,我來數列慈恩。
曾記那年那月,那時少不更事的我被那位先生斥責:“年紀不大,脾氣不小,你這個性格就跟曲藝團的徐勍一樣!”曲藝團是干什么的?徐勍是誰?這一切跟我又有何關系?當時哪知后來,關系大了。水有源頭樹有根,且聽我娓娓道來。
隨著年齡的增長,因探尋四川揚琴與川劇的腔詞關系,從而深入了解了曲藝。因藝術崇拜而追星,知道了李月秋、李德才、王永梭、鄒忠新、程梓賢等四川曲藝界的袞袞諸公。這才曉得了徐勍是一位當年在西南三省紅得發紫、紫得發亮、亮得發燙的評書大家。惜乎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好容易才在一次宴會上目睹了您的風采,有了第一次的接觸。殊不知,由于那個時候的我內斂不足,張揚有余,沉穩不足,輕浮有余,除了嘴巴能說之外,并沒有給您留下什么好印象。我是如何得知?早在八年前,這可是您親自告訴我的。
2009年底,幾乎一事無成的我,幾番周折之后再次回到了重慶。一天,與我的文學寫作老師,著名的戲曲編劇隆學義先生久別重逢于通遠門城樓的桂香閣茶樓。隆老免去客套,直奔主題,問我今后的打算。說實話,當時的我比較消極,真不知人生的道路該何去何從。隆老對我說:“以前程梓賢先生不是教過你幾個段子嗎,干脆你就學說書。一來你自己能寫,一塊醒木一張嘴,一把扇子一杯茶,輕便靈活,簡單節約。二來,你的舞臺欲望強,又有川劇底子,只要你堅持,若干年后定有所成。”為此,隆老還專門把我引薦給了重慶評書名家曾令弟先生。因我與曾令弟先生本就是親戚關系,不便收我為徒。不幾日,無意間聽說您在住院,我與牛林先生同去醫院探望。多年不見,本以為您早已將我這無名小輩遺忘。不待我開口介紹,您拔掉氧氣管就問:“袁國虎,好多年不見,現在作何職業?”我回答:“待職青年,無業游民。”您撐起身對我說道:“這次我出院之后,你就來我這里學說書嘛。”話音剛落,我頓時受寵若驚。我正想學評書,不料您竟主動開口。求之不得,榮幸之至!繼而您說道:“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就覺得你能言會道,是塊說書的材料。只是你那個時候癡迷川劇且性格跳顫,也就沒有說下文。只要你肯學,我愿傾囊相授。”至此相處一年后,在“南山第一莊”舉行了正式的拜師儀式。如此,得師垂青,忝列門墻。拜師時的情景歷歷在目,您從主持人天池老師手中接過話筒說道:“天公已經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化用晚清詩人龔自珍《已亥雜詩》中的詩句。原詩是:“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您在自傳《口舌人生》的結束語中引用過原詩末尾兩句,由此可見您在事業上對我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機緣巧合,拜師不久,我便應“成都印象”之邀,離渝赴蓉,在錦城正式掛牌開始了職業說書的生涯。您的臨別贈言至今言猶在耳:“這下你獨自放飛,出去好好歷練。要想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說書人,不能靠老師一口一口地喂你幾個段子,道路是自己走出來的,本事是各人磨練出來的。隨時保持聯系,無論生活還是業務,我都會盡力。小子前途可造,還望好自為之。”一番言語,不禁讓我回想到了幾句戲詞:“金鉤李昌我師父,拜在門下當學徒。夜學文來朝習武,諄諄教誨當記熟。拜辭恩師下山路,從此跑灘闖江湖。……倘若日后有難處,大叫三聲洞庭湖。”
那幾年,雖說師徒不常見面,但您對我的關心亦是不少:請同行戴德云老師給我講述天府之國的民俗,托老友羅競先老師幫我搜集評書資料。后來聽說我要攥弄長篇書,還特意囑咐年近七旬身居綿竹的大師兄何成正給我“過條”,教我“清條”“撕條”“岔條”“串條”,如何勾綱剪蓋,怎樣起承轉合,……慢慢地,我才在成都立了足。立足未穩,又在悅來茶社開了另一個書場。“落地紅”當然只能靠段子,幾場書下來,籠下一批自己的觀眾,才能說長書。有一天,我開書至半,正欲“扎板”,突然觀眾席中一聲咳嗽,抬頭則見您戴了一頂白色塑料的博士帽坐在第五排中間,頓時頭腦空白而不知所云。只得急忙離位,請您登臺。這才知道,您原本在南京度假,聽說我在開長書,專程乘機悄悄前來。難以抑制的淚水是感動所致,不消說下半場的書就由您替我接過去說了。當晚回到家中,話罷別后事,敘過寒與溫,而后的話題無一不是評書。將近一周,白天您陪著我去說書,我在臺上說,您在臺下聽,聽完之后指毛病、提意見,茶館、飯館、車上、路上都在說。晚上回家又給我“過條”,《得勝圖》《金鞭記》《梨園譜》……,每每幾近東方之既白才洗漱上床。那幾天的惡補才讓我真正探尋到評書的奧秘,深深明白說書的不易。幾個月之后,我又在西門天藏閣茶樓開辟了新的書場。您為此又來成都,相比頭次的悄無聲息,這回顯得有些大張旗鼓。還未動身便廣發“英雄帖”,邀集了成都不少的曲藝大咖、社會賢達來為我助威剪彩。有一天,我說完《徐明廣測字》下來,您拍了一下我的后腦勺說道:“這段書說得不錯,成了。”師門里眾所周知,您對弟子的要求何止是嚴格,簡直就是苛刻。據說有些師兄一輩子都沒有得到過您的一次表揚,您對我的認可使我受寵若驚。當晚我們師徒睡在一張床上,我因興奮而遲遲未能入眠,好容易才睡著,不到兩小時就被您叫醒:“起來,我給你說,昨天那段書還是有些問題,比如開頭,我總覺得差點什么,想了一晚上,我覺得應該這樣,……”我開燈看鐘,天吶!這還是下半夜,四點都沒有到。看我臉上表露詫異,您臉上已然呈現不悅之色:“你以為白天我說你成了,你就忘乎其形滿足了?告訴你火候還尚早。會通精化你僅僅也就是會了、通了,逐漸在往精的方向走了,還沒有精益求精,更莫說化了。你還有賣弄的嫌疑,過于表現自我。”對我一陣狠批,接著一一舉例示范。不一樣,真不一樣!您雖然是在說書,卻有鮮明的音樂形象和濃郁的戲劇色彩,每一句言簡意賅,猶如情景再現,充滿了詩情畫意。同樣的語言,不同的表達,疾徐收放、低昂吞吐,于波譎云詭中得飄逸峻挺之致,且字韻純正,口吻親切,如珠走盤,如帆順風,其性靈風骨,洵非凡庸所有。后來我才深深地明白,您的藝術追求是著意要往一種俗文化的形式中植入雅文化的因素,最終想要達到質樸真率與精致典麗融為一體。造詣何其之深!差距何其之大!莫說回想當時,就是現在,于我而言都還是那三個字——夠得學!
三年前,重慶市曲藝團向我拋出了橄欖枝,回渝簽約,這才結束了我的跑灘生涯。回爐再造,與您接觸的時間便多起來了。剛來團里那半年,您身體尚可,幾乎每周演出您都要來聽。聽后總有意見和建議,好的、不好的、值得保留的、需要精進的,……這期間,您教的更多的是怎樣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追求和信仰,如何克服性格的弱點,根除江湖的痞氣,保持勤奮的學習,打造經典的作品。
我正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時,您已然百病纏身,垂垂老矣!近年來不斷接到您住院的消息,幾乎住院就下病危通知書。幸而每回都是有驚無險,好多次生命垂危的關頭一輩子好強的您都挺過來了。您經常告訴我說自己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感謝政府感謝黨給了您強烈的翻身感。進入耄耋之年本算高壽,可我仍然難以接受您永遠離開這一突如其來的事實。
恩師!我多想再聆聽您一次教誨啊!這已是奢望。您的風范和恩德于我如晴云松柏,春煦雨露,我難以報答,只能將慟哭于寢門之內的深沉哀傷作為永恒的紀念!連日連月,每當我在高聲講演中驚醒,總是那么悵然若失。我走上書臺高舉醒木的那一瞬間,您那嚴厲的面孔、殷殷期盼的目光總是浮現在我的面前,激起我對四川評書的無限熱愛,喚起我的創作熱情,啟迪我在藝術道路上不斷探索真諦,奮發不棄!